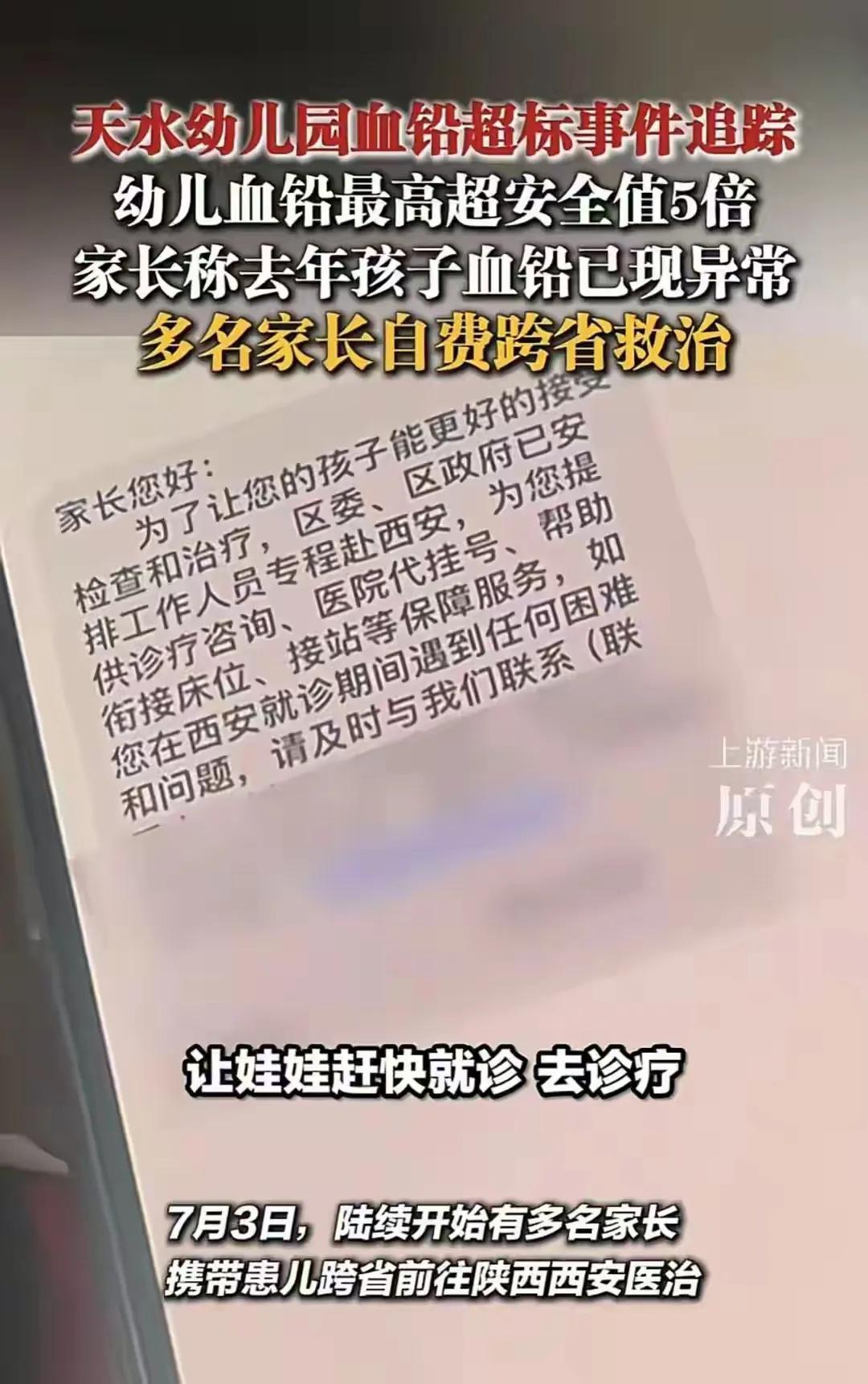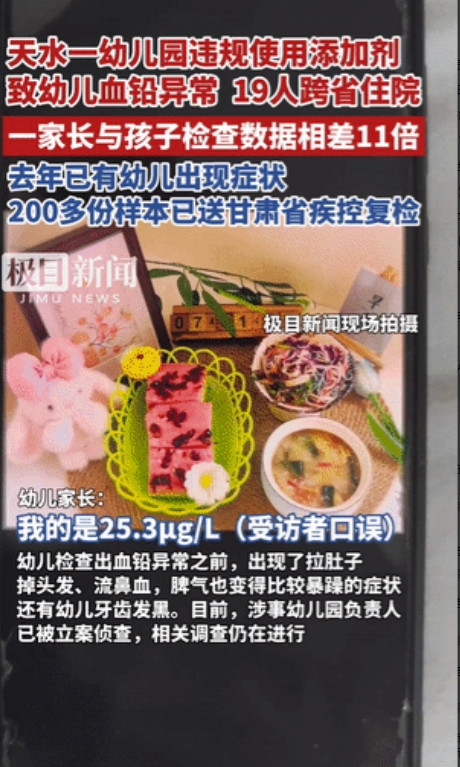袁隆平曾这样批评过自己的学生: “要研究水稻,你就必须给我下田去,电脑很重要,可它种不出水稻,书本很重要,但它也种不出水稻。”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那年月战乱四起,家里东奔西跑,湖北、湖南、重庆都待过。小时候,他亲眼见过饿肚子的人,瘦得皮包骨,这让他下定决心,长大要干点跟粮食有关的事。1949年,他考上西南农学院,学农学,专攻遗传育种。大学里,他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课余就往田里跑,盯着庄稼看,恨不得把每棵稻子都摸透。毕业后,他被分到湖南安江农校当老师,住的是土坯房,吃的粗茶淡饭,但他乐在其中,天天泡在稻田里,研究咋让水稻多打粮食。 60年代,全国闹粮荒,袁隆平坐不住了,决心搞杂交水稻。当时国外专家都说,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没戏,可他不信邪,埋头查资料,翻外文书,熬夜推算。1961年,他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穗大粒多,产量高得吓人。他带着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没日没夜地找雄性不育株,顶着太阳晒,累得几次晕倒田里。1964年,他找到6株关键样本,1973年终于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亩产一下翻了好几倍。这技术让中国从吃不饱到碗里有粮,还推广到国外,帮不少国家填饱肚子。 袁隆平生活简单得像个老农民,穿旧衬衫,骑破自行车,住老房子。他会英语、俄语,拉得一手好小提琴,闲下来还爱跳踢踏舞,逗得学生哈哈笑。他讲课风趣,爱用湖南话讲段子,但一聊到水稻,眼神就亮得像灯泡。他常说,农业科学得为老百姓服务,解决饿肚子的事比啥都重要。这股子信念,撑着他干了一辈子。 袁隆平那句“要研究水稻,你就必须给我下田去,电脑很重要,可它种不出水稻,书本很重要,但它也种不出水稻”,是90年代初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说的。当时,团队里来了批年轻人,大学刚毕业,脑子里全是新潮理论,个个捧着电脑,热衷搞数据模型,觉得下田又脏又累,没啥技术含量。袁隆平看不下去,觉得这帮小子光会纸上谈兵,压根不懂水稻的脾气。他点名批评一个叫小张的学生,嫌他整天对着屏幕算参数,却连稻田的土质变化都没摸清。 袁隆平为啥这么较真?因为他自己就是从田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知道,水稻这东西,书本和电脑只能帮一半忙,另一半得靠田里实打实的经验。土壤酸了、虫子多了、排水不好,这些问题光靠公式算不出来,得眼看手摸才行。他要求学生每天至少两小时泡在田里,量穗数、查病虫害、记生长数据,连他自己,六十多岁了还天天往田里钻,晒得脸黑得像锅底。他常举例子,说某块田前年虫害严重,去年水淹,产量波动大,电脑压根预测不了,只有下田才能找到症结。 这番话不光是批评,更是他科研理念的精髓。他常说,农业研究得“脚沾泥,手沾土”,理论再漂亮,没实践背书就是空话。他带着团队定了规矩,实验数据必须从田里来,模型得跟田里情况对得上号。这法子让团队少走了不少弯路,也培养了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干实事的科研骨干。后来,杂交水稻的每次产量突破,都跟这套“田间为本”的路子分不开。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越搞越牛,2000年,超级杂交稻亩产破700公斤,2004年冲到800公斤,2011年上900公斤,2014年直接干到1000公斤。每回验收新品种,他都亲自到田里,拿放大镜看穗粒,掰着手指算产量,乐得像个小孩。他的技术不光救中国的肚子,还推广到印度、越南、非洲好多国家,当地农民用上他的稻种,收成翻倍,日子好过不少。他去国外交流,操一口流利英语,跟专家聊育种,讲得头头是道,外国人听完都竖大拇指。 他完全可以靠杂交水稻技术申请专利,赚得盆满钵满,但他没这么干。他公开说,杂交水稻不搞专利,中国就是要让全世界不挨饿。这话一出,国际上都炸了锅,联合国粮农组织直接叫他“杂交水稻之父”。他自己呢,照旧过得糙,穿旧衣,住老房,办公室塞满书和稻种,桌上永远放着记录本和放大镜。2019年,他拿了“共和国勋章”,全国人民都觉得,这荣誉他当之无愧。 到了晚年,袁隆平还是闲不下来。2020年,90岁高龄,他还跑去海南育种基地,拄着拐杖看新品种,风吹得白发乱飘,他还哼着小调,精神头一点不输年轻人。2021年5月22日,他在长沙去世,享年91岁。那天,全国人民都红了眼眶,追悼会上,稻穗摆满灵堂,街头鲜花堆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