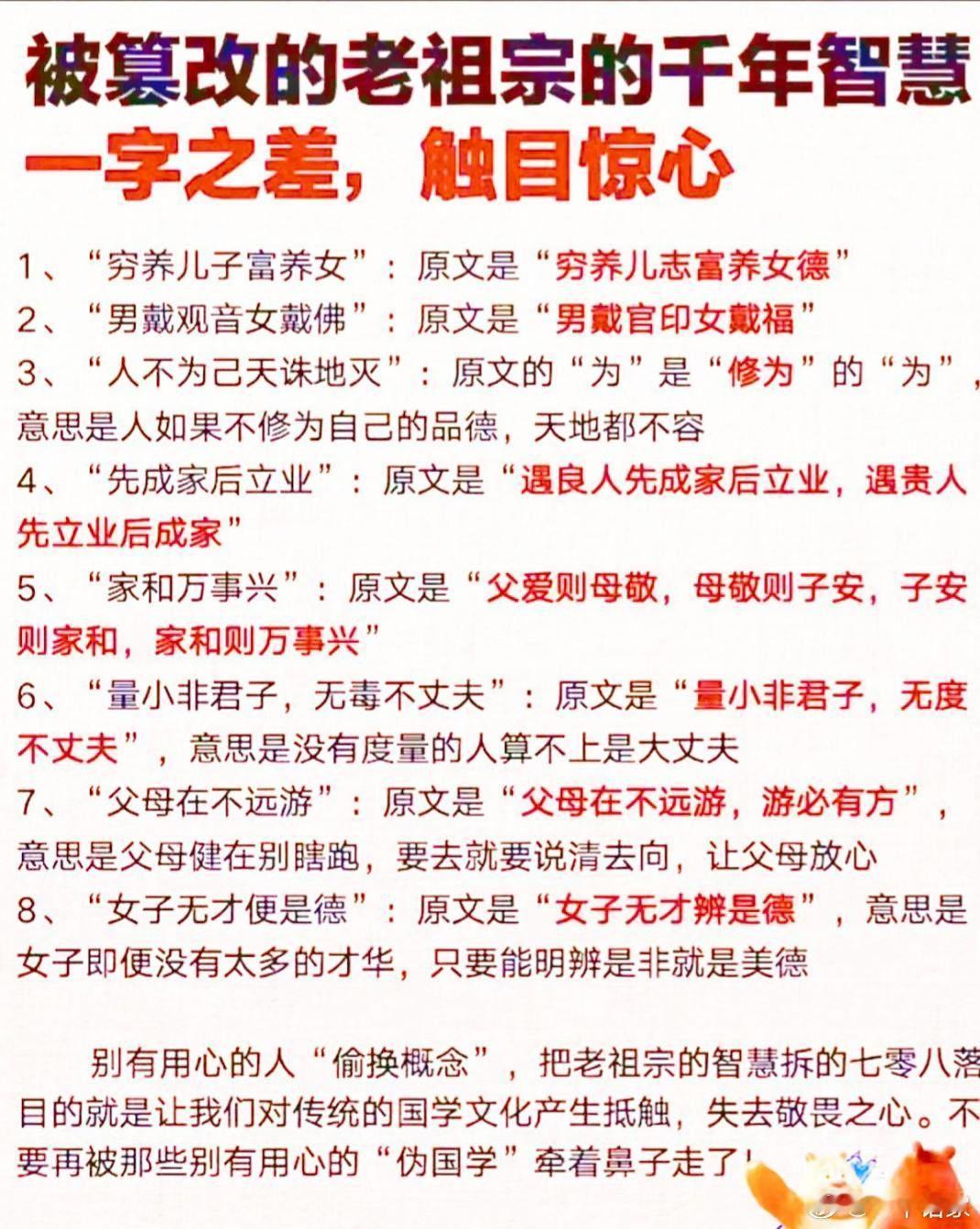作为香港教联会副会长、立法会议员、前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的邓飞先生,是一位在香港教育领域深耕多年、成就卓著的教育专家、学者。
邓飞先生曾获颁香港特别行政区荣誉勋章,现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友好协进会会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硕士课程兼任讲师等职务。

▲邓飞
邓先生年少成名。大学时代两度荣膺香港大专辩论会冠军,并夺得最佳辩论员等殊荣。
近日《香港故事》系列专访团队对邓飞先生进行了采访。围绕爱国爱港、爱国者治港、香港经济发展与香港教育展望等一系列话题,邓飞先生以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专业素养和见地,分享了精彩独到的见解。
爱国者治港:首先要遵守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
朱顺忠:邓老师,请问您怎么理解“爱国爱港”这四个字?
邓飞:爱港是没有太多争议的,香港就是香港。说到爱国,首先要明确这个国是指什么国。如果你只是说一个中国,那是不足够的,而且有点空泛。
我们说爱国爱港,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尊重“一国两制”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宪法性的原则。无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设立特别行政区,再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是一个全国性法律,不仅仅是香港适用的——也是很明确说了“一国两制”,在这个前提下来理解爱国爱港才具有更精准和更现实的意义。
这个国肯定是指“一国两制”的国,而“一国两制”的国根据我们的宪法和基本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朱顺忠:爱国者治港,这个爱国没有一个确定的度量衡。比如,经常喊口号爱国的人,可能会别有用心。真正会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甚至这些建议和批评可能很刺耳、很犀利,这样的人可能内心深处是真的爱国。您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
邓飞:我们说爱国者治港,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和政治伦理。如果你想参与到治港团队里面去,首先必须尊重“一国两制”。如果从根本上否定甚至反对“一国两制”,请问你参加干吗?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人格分裂。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那种喊口号式爱国的人,如果他不是真心爱国,就往往是规避了“一国两制”。他会规避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只是泛泛地讲爱中国,然后爱一个虚幻的或者是很遥远的一个所谓的历史文化的中国。而且他所理解的历史文化的中国还不一定真的是历史文化的中国,只是他认为是的。
而提出很尖锐的批评意见的人,如果他批评是对标着一种很具体的公共政策、社会事务,想去解决问题,希望我们的社会,希望我们的特区,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所改善、有所进步,解决一个接一个的经济、民生、社会的问题,他提出来的意见再怎么尖锐都是就事论事。但是,如果他只是假借批评某些经济、社会、民生的政策,但实际上否定整个政治体制、整个国家体制,他是谈不上爱国,谈不上对“一国两制”尊重的。
朱顺忠:我能不能画一条红线?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你可以尖锐地批评,但是法律是底线。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怎么想,我们无从判断,也不好判断,我们把法律作为底线。如果你批评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实际上去分裂国家的目的,这样就把法律作为一条红线去区分二者。
邓飞:对,可以这样理解。
香港抗战和共产党游击战一脉相承
朱顺忠: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两岸三地,对历史的教育,对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现代史的认识,可能有不同。您怎么理解?比如就抗日战争来说。
邓飞:我倒没觉得两岸三地有很根本的区别。只要你尊重中国人,尊重这段悲壮、壮烈的历史,其实在根本立场上不会存在差别。可能有些历史细节,基于大家研究的角度不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因为大家知道,14年抗战恰恰就是我们不分党派,不分南北,不分阶层,整个中华民族都携手在一起,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历史。是这场战争使得我们的民族凝成一体,真正出现了很强的一种民族的解放的情绪在里面。
当初,为什么日本叫嚷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它背后的假设就是中国人一盘散沙,中国人是没有一个很凝聚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这是日本侵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既是有一种侵略的军事的意义,也是一种文化的判断。结果他打下来才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的入侵反而激发了中国人一起去抗战,真的是撞在铁板上了。这反过来就证明中国人绝对不是日本侵略者所以为的一盘散沙。落实到以抗战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教育上,这一点是必须突出的。
朱顺忠:最近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台湾的某个领导人,就公然提出来,抗日战争是由某一个群体,比如说国民党将士主导的,对共产党的抗日行动进行了弱化,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当然我们的外交部对此也有反应。您从香港的角度,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邓飞:首先,我觉得挺搞笑。他怎么忽然代表了这个政党来说话?因为他自己都是否定这个政党的。这个政治笑话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他那种极端的政治的取巧和政治的功利主义。在他自己的所谓选举政治的考虑之下,他所推崇的这个抗战的政党,就是他的敌人。现在要跟中国内地对抗的时候,就把这个政治上的敌人又标榜出来,变成他所推崇的所谓抗战的主力。这种政治取巧和政治的极端自私务实的主义,大家笑笑算了,别太当真。
第二点,抗战的时候国共当然也有摩擦,但在整体上,大家抱持着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首先要救国。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甚至也有一批是无政党人士,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都是一起去抗战。大家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情。我也同意你说主力军、正规军,你的人数最多,你的装备最好,所有外部的支援都是给你的,你就天然承受了正面战场。作为日本侵略军,他首先打击的肯定是你的主力部队,肯定是打击你接受国际援助最多的部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到底是谁挺进到敌后?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绕到你的后面,而且我的装备是远远比你弱的,不仅是比日本侵略军弱,比我们的主力正规部队还要弱得多,但我却挺进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这个行动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不简单的胆略的体现。
香港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其实我们就充分理解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价值。英国殖民军队在香港抵抗了十几天就垮掉了。之后的香港敌后游击战,港九独立大队,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政党(共产党——编者注)领导之下,也只有在这个政党领导之下才具备这种专业的游击战的能力。我们当时的正规军不是不想打游击战,他们也有大批的游击队,但为什么在游击战争里面他们发挥不了共产党游击队的那个力量?这就是专业和外行的区别。在整个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面,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坚持的游击战就是跟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进行的游击战完全是一脉相承。无论是从政治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军事战术上,都是一脉相承。
“黑暴事件”是反对派一步步与中国割裂的结果
朱顺忠:您说得非常精彩。立法会前议员蔡素玉小姐告诉我,她在1997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去维多利亚港湾公园里边,拿着很多毛绒玩具去问一些十岁以内的小朋友,问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几个小时的时间,她的毛绒玩具没有送出一个。当然1997年以后会好多了。针对这个问题,您是不是有很深的感受?
邓飞:这其实跟当时的殖民教育是相关的。因为早在1952年左右,当时港英方面殖民统治者对香港本地教育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首先排除了用英国文化历史来同化香港本地的可能性。第二条就是,在必须推动跟中国语文、中国历史相关的教育时,怎么拿捏分寸?就是不能激发起香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讲中国古代史,讲它再怎么辉煌都可以,但不能提近现代,不能有近现代民族独立或者解放运动的历史和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问中国首都在哪,小朋友都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殖民主义教育就这样把它抽空了。
在主权回归之后,其实我很早就提出,中国历史教育必须要古今并重,不能延续殖民统治时代厚古薄今的做法。那样会变相地造成为反对派那种只推崇文化历史的中国,讨厌当代中国的论调培养群众基础,培养社会思想基础。现在香港的历史教育就相对比较平衡,近现代历史、当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都是比较平衡的。
朱顺忠:97年以后,再加上中央政府和香港的交流的增多,政治上的互融,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发展趋势,但是很不幸,前些年发生了黑暴事件。大家都在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偏差?还是确确实实是有一些极少数人鼓动的?您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邓飞:教育只是反映了这种不足,不一定是根本原因。其实,刚回归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我们爱国爱港的阵营觉得,既然保持50年不变,香港就自动繁荣稳定,我们就讲发展,甚至发展都不用怎么讲,反正香港的经济本身就很不错,对于意识形态也好,政治理念也好,或者是一些价值观,能不提就尽量不提,能回避就回避。但是另一种趋势就是,反对派刚好跟我们相反——我不跟你谈经济,我就跟你谈政治,他也呈现出阶段性。
第一个阶段,反对派的做法就是叫爱传统历史文化的中国,不爱当代中国。再具体一点,再敏感一点,就是我是爱国,但我不爱党和政府,这也是很有迷惑性的提法。这是第一个阶段,大约一直到2012年,反国教风潮出现,开始呈现出另一种局面。
之后反对派再往前走一步,我不仅是不爱党和政府,我也不爱国。这就是所谓的解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思潮开始出现。为什么有所谓的香港民族论呢?这已经不是在跟你讲一个党和国家或者政治体制,而是说我就是所谓的民族论,就是民族身份认同也好,本地的文化习俗也罢,就是跟整个中国开始要割裂,然后到黑暴,走得更加极端,走到尽头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不可能再听之任之了。无论是国家通过的《国家安全法》,还是特区终于完成了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必须从法律方面去拨乱反正。但其实法律永远只是一个最低标准,我们要求的更高层次的政治伦理、政治价值观的标准,这就要靠教育了。
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惠及民生经济
朱顺忠:应该承认,不管是什么原因,目前今天包括内地,包括香港,我们的经济确实较之前些年有了下行的压力。很多人都在寻找香港重新振作起来的方式,近些年香港也在慢慢恢复,甚至在某些领域恢复的幅度还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想让香港的经济,甚至也包括全国的经济能够尽快地回归。我想问问您对香港将来的经济是怎么看待的?
邓飞:香港始终有个很重要的很好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跟国际的准则无缝对接。同时,它又有整个国家作为它的福地。坦白讲,如果我们不算澳门,只讲海外,我们再找不出哪个城市有这种政治经济地缘上的优势,只不过要看我们怎么发挥。我觉得这方面是乐观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有一些经济现象,不是香港独有,甚至不是整个中国独有,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以人工智能为首的创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之下,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经济,都会呈现出一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而且新兴的富庶阶层大多不是(处于)传统经济(领域),传统经济就是勤勤恳恳、白手兴家,经过几十年的累积,终于成为一个富豪、上市公司等。
但是现在的所有新生的富豪几乎都来自创新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地球科学这一类(产业),有几个特点是与传统经济白手起家的人完全不同的。第一他特别年轻,以前可能要积累几十年才能够成为富豪,现在他可能是“90后”的人就成为了富豪。全球都是这样。第二,这些新兴富豪的生活价值观或者是三观跟传统经济白手兴家的富豪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通常他的学术水平或者他的知识含量特别高。他都是大学里面,我们香港叫神级的学科、神级的专业,最热门的专业的学生,就是知识门槛的要求特别高。而传统经济的富豪,可能连大学都不需要去念。挖了个矿或者有一块地皮,就累积起来了。但现在不同了,新兴富豪往往是高端学霸。
第三种情况是,这一类的科创企业家,以及他们的科创企业,跟传统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有个根本区别:他们不怎么去消费。而且科创企业也不需要大量的员工,他可能就这么几个码农,连接待处都不需要请人去。
这三种情况加起来就意味着:第一,科创经济时代下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你不容易迈过这个门槛,因为他的学历要求特别高,知识含量特别高。第二,它对于周边的民生经济的牵引作用,就是涟漪效用不强。他不需要招很多人,这些科创企业家对于声色犬马也完全没有兴趣,他就想怎么改造人类、改造世界、改造地球。
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这种科创企业的发展,是世界的大潮。科创是第一生产力,科创是第一战略竞争能力,不可能逆转的。但同时我们要小心,这一类的企业多,不等于它能够带动起整个民生经济。一些传统的民生经济,一些传统的中小企业还是需要存在的。
我们要同时顾及两方面,一个是科创经济要保持一个高的、高标准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尽量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惠及民生经济。我举个例子,跟我这行相关——教育,现在香港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我现在提出的从留学香港开始,要再进一步变成留学经济。什么叫留学经济?不是说帮大学和中小学去赚钱,不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教育经济是通过吸收来自世界各地和来自内地的学生、家长、人才等等,他们来到香港就带动着香港经济民生的转变,第一可以补充我们的人口老化,为我们提供一些年轻的人口。第二,人口有了,他们需要吃住,需要购买日用品,整个市面就会被带旺起来,而且这一点在欧美成熟的国家和社会也是已经完全成体系了。比如说,我以前留学的地方英国约克,约克大学对于约克郡的经济贡献是很重要的,包括GDP,也包括它聘用的各种人,除了大学教授,还有各种后勤人员,都是为当地经济做了很大贡献的。
朱顺忠:我注意到您在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态度非常鲜明,我非常欣赏这一点。现在有一种论调,比方说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享受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许多特殊的政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海南,为什么不在上海等等树立另外一个金融中心?您对这种论调是怎么看待的?
邓飞: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彼此取舍的零和游戏的关系。你塑造海南、上海,都可以,就良性竞争,各自去发展,自己觉得自己最有优势的,就去发展好了。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把它对立起来,这种论调本身起码不会产生一种良善的后果。其中包含有很多虚的或者是伪命题。我们经常发现有很多的论调都是把一些本来根本就不是零和游戏的事情故意对立起来。我认为这完全不是相互排斥的观点,可以各自发挥优势的。
反对偏激的教育理念,也要突破语言局限
朱顺忠:还有一种论调,比如在内地,很多地铁站,原来是中英文标注,后来就有人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为什么要用英文来标注呢?我们就用汉语拼音,标注完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中国人不需要看中文拼音,因为都认识汉字,外国人看中文拼音又看不明白,而且这种趋势还有曾经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再比如说,有专家主张取消大学的四六级英语考试,不让孩子们平时学英语等等。您作为一个教育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邓飞:这些对于香港来说暂时影响不是很大。我觉得香港面对的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种局限性,它跟内地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
我先说香港的最大局限性,是把世界性、国际性等同于英语。谁跟你说世界只有英语?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不用英语,一带一路国家可能是俄语,可能是阿拉伯语,可能是土耳其语。对香港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盲点。这个盲点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就是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还真的傻乎乎地以为全世界都是说英语;第二点是我们的教育课程上,哪个大学有小语种的课程?没有。大学只有英语,其实很危险,危险的就是我们除了英联邦再加美国之外,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英语世界之外的庞大的世界,无论是欧洲大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一无所知。
很多香港人根本分不清印巴跟阿拉伯,跟土耳其有什么区别,也搞不懂德国与法国有什么区别。除了旅游胜地,除了喝啤酒和吃法国大餐勉强知道之外,其他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是香港必须要跟上的。否则,你这个所谓的国际超级联系人,这个“国际”是被砍掉了至少一半。
严格来说,这只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来的一种惯性,而我们突破不了这个惯性,甚至连要突破这种局限性的主观意识都还没有建立,这才是最危险的。
我们在说,我们要增加对中东国家的联系,帮国家担任超级联系人,结果我们的议员、我们的官员到了当地才发现,中国内地的企业早已在那里落地生根,而且有大量的商会已经成立了。我们香港在当地不但没有什么投资,即使有的话,连商会的规模都成立不了。
到底我们是为国家开拓,还是我们落在国家后面了?这就有点尴尬了。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某些中东国家,非英语系的国家都出现过很多这种尴尬场面。但英语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普通法制度对于金融商业来说弹性比较大。在这方面,香港有比较大的优势。
国家也感觉到了这个巨大的优势。把国际调解院设在香港,就是充分利用普通法这个国际商务上的优势,真的做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我们要扩大生意面,扩大联系不同的国家、地区,第一就要突破语言障碍,明白世界比英语世界大得多。要突破这个认识,同时从我们的课程体系,尤其大学课程体系也必须研究,是不是要引入一些英语以外的课程和英语以外的一些国别的研究?这些都必须要补上。
可能内地未必留意到这种情况,在香港我在这方面感觉比较强烈。至于你说内地,好像是有些比较极端,比如说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甚至高考都取消英语考试。我们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这样想,这很重要。提出这些观点的专家,如果他是纯粹只是一种很狭隘的民族情绪,我们当然不能支持。
朱顺忠:绝大多数是这种,您说的这种。
邓飞:这我们不能支持。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来提出,就是从扩大我们的学术体系的自主性和对国际联系的无缝对接的角度,也不一定反对。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上是有两次大翻译运动,很重要。
欧洲的中世纪是黑暗时代,整个古希腊罗马的先进文化完全集体失忆了,历史性失忆了。直到阿拉伯人通过智慧宫把整个希腊罗马的文化用阿拉伯语和突厥语保存下来,然后阿拉伯帝国去征服西班牙半岛的时候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西班牙的学者以那里为主,但不限于西班牙,陆陆续续从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主要是阿拉伯语,重新发现了原来自己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化是如此地灿烂。陆陆续续把阿拉伯语的记录翻译成欧洲的拉丁语,重新翻译成欧洲的语言,这是第一次,所以就出现了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没必要整个欧洲为了保存我的灿烂文化,就只学阿拉伯语,没有我自己的自主性,不需要这样做。
第二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明治维新一直到今天有个很强的大翻译运动,他把大量来自英语和其他欧美国家的语言的科学、人文,大量的知识迅速几乎无缝对接地翻译成日语。日语本身没有那么多词汇,它就借助汉语,所以有大量的我们当代的汉语(词汇)其实是来自日语。我们很多政治词,比如政府、政党、派出所,其实来自日语。日本就借用我们汉语去重新翻译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人文和自然科学都很发达,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日本人不太需要去学外语。
日本的普及教育里面几乎是到了中学甚至高中阶段才学外语,有大量的日本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英语也不怎么样。日本发的许多期刊尽管是英语的,可能跟作者本人也未必有很大关系,所以就日本这一方面的经验,是不是将来也过渡到我们整个中国的发展,而不是一直依赖着学习外语?不是每个人的语言天分都那么强,有些人可能是人文,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天分很强,就是语文能力不强,一个英语就把一个英雄好汉拖死了,也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如果出于这个考虑,我们继续发展整个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大目标?就像当年日本的大翻译运动一样,必须建立起我们自主的学术体系,同时又能够用我们的当代汉语,一直进步的当代汉语无缝对接世界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果终极目标是做到这一点,提出我们不要过度强调英语的考核,英语的应试,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是支持的。
朱顺忠:您说得非常好。其实不管是中华文明、欧美的文明,还有两伊文明,文明在顶端都是融合的。强行用某种语言来撕裂文明,也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共同希望中华文明能够在语言层次也有一个大翻译运动。
邓飞:肯定的。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
加快输入高端人才,拓展职业教育
朱顺忠:我最近关注到香港的就业和VTC(香港职业训练局的简称——编者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香港在全国推行的VPAS(职专毕业生留港) 计划。但是有一个剪刀差,就是一方面香港本地的失业率在攀升,我看最新的数据已经达到3.7%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专上人才奇缺。在这种状态下,似乎是香港的人才又缺,失业率又高,我们怎么来理解?
邓飞:其实,几乎所有大城市都面临这种情况。在大城市,一方面会用很多的政策去吸引高端人才进来,另一方面越是大规模的城市,越是呈现出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干(的现象),一些低技术、低知识含量的、低学历的工作,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干。
包括内地的一线城市都面临这种局面。我认为要解决的第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一些中基层的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干,而且我不干,我也不想别人来干,不想输入外地劳工来干,这就是一个很激烈的矛盾。
朱顺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有没有提出的某些建议呢?
邓飞:我认为目前香港的政策还是靠谱的,现在输入劳工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在香港请不到,你才可以去聘用其他地方来的劳工。这个前提还是有保障的,同时也会保障他的最低工资。一旦无底线地压低工资,就把整个市场拖累了,同时也是在盘剥外地劳工。这两方面的原则香港政府都还是比较明确的。
有时候人们可能会嫌香港做得慢,但是香港是相对比较人性化的,不会走极端。输入劳工和平衡本地就业这方面,其实特区政府一直都做得不错,在政策上是经过很精巧的设计的。
至于说打击黑工,那是执法的问题,不是政策出了问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输入高端人才,这个竞争很大。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以前一些没有特别去参与这类竞争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已经开始参与了。
比如说,英国拿5000万英镑出来,实行搬家计划。为的是吸引全球各地的科学家或者科创企业家,不是一个人移民,而是把整个实验室的团队都搬过来,这是比较罕见的。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都提出要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这在美国简直是破天荒的,美国是一个极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于国家政府,尤其联邦政府的政策,直接地去调控,或者用内地的说法,就是从指导性计划变成了指令性计划,现在在美国都出现这个苗头了。
既然大家都这样做了,香港在这方面更要加快步伐去做。
第三条,关于职业教育,目前香港有应用科学大学等学校,其实就是职业培训大学,它做职业培训,但是它是有本科、有硕士、有博士的。
朱顺忠:职业培训,还有博士学位?
邓飞:是的,有。实际上就是应用研究和应用教育,它不仅是培育人才,它的毕业生可以马上持证上岗。不仅仅是这样,同时它的学生到了硕士、博士层面以后,他的应用技术的研究能力必须要上得去,不是培养学生有一套技术,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你教会了我,然后我去做,我不会思考,没有开拓性的,不是这样。香港这种应用科技大学在茁壮发展。
最后一点,我觉得可以向内地学习。内地现在都在开拓一些职业培训的本科课程,跟企业一起合作。内地的“学企合作”是从课程的设计一直到企业的实践实习教育,是一条龙融合在一起的。学生上课不一定是完全在大学的教室里面,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合作的企业里面去培训。
香港开办课程跟企业界合作,就是我要开这个课程,你们企业在这个岗位有没有这个培训需求?有,那我们就开。但只止于这一步,还没有到企业去实践这一步。同时,对于学位,尤其是高端学位,就是研究生以上的学位,跟企业合作就更加谈不上了。
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走得再往前走一点,因为这方面香港不仅仅是向内地的经验学习,我们知道德国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是学术综合类的大学,一个是职业培训。其实,这两块全世界现在都在逐渐模糊它们的区别,有一个融合的趋势。去年的《经济学人》有个报告,就是讲德国的这种磨合。
朱顺忠:我看了那篇文章。

▲邓飞(右)与红船融媒总编辑朱顺忠
提高香港软实力,打造国际教育枢纽
邓飞:最近有报导说,美国传统的名校长春藤学校退学率越来越高。退学率居然占到三成!退了去哪里呢?他宁可去职业类的大学。
他也是进入本科的学校,但是是一种职业培训的学习。这当然跟美国大学的学制也有一定关系。我觉得还是要跟上世界的大趋势,没有必要去严格区分两类大学,可以把这两类的界限模糊一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学习内地和德国的这些经验,加大和大企业的合作。
朱顺忠:怎么合作呢?
邓飞:香港缺乏大企业,我们要引入高端企业到香港的时候,不妨把这一条加进来,就是同时也要拓展到境外。如果在香港本地有一个大企业,它可能只是个总部经济。所有的厂房,实验室或者是实验车间,根本都不在香港。它可能是在大湾区,可能在东南亚。我们的职业培训的大学跟大企业去合作,可以这样做——我们的学生不仅仅是在香港的校园上学,还可以到大湾区,可以到东南亚的厂房或者是实验室去实习。这样我们的思路可以拓宽一点。
最后一点是,我们现在要打造一个国际教育中心、国际枢纽。
现在整个东南亚国家的青年人口的比例非常高,印尼、越南、菲律宾等都非常高。他们做这种青年职业培训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是极高的。我前年去东南亚几个国家考察的时候,人家很实事求是地跟我们说:我们的人口中,青年比例很高,但是没有一技之长。一旦失业就易导致社会危机,社会危机会转变成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职业教育,无论是中学类、大专类,还是大学类的职业教育,在拓展国际教育枢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同时把应用科技大学这一块拓展到东南亚国家。
朱顺忠:您这个思路比较超脱。
邓飞:要拓展到帮他们去培养他们的青年人,让他们用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去培养他们,这样就有几个好处,第一,我们的友好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他们的职业培训学院是不能招外国学生的,我们的香港的任何一所大学和 VTC 都可以招海外学生,这是一个政策制度上的优势,它不做我们可以做。第二,我们用我们的职业标准去培训他们,就等于输出中国香港的标准到东南亚。
朱顺忠:意义就更重大了。
邓飞:真正的软实力除了潮流文化的软实力之外,就是教育的软实力。比如英国无可否认它是一个文化软实力很强的国家。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教育标准。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标准。我们用我们的职业培训标准去培训东南亚国家的学生,以至“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就等于输出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打造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真正的难度在第三点,因为通常来参加学习职业培训的家庭,都不是经济非常宽裕的家庭,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公共财政去补助本地的同学,但是如果说东南亚的同学留学来香港,但是没钱、没学费,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我们香港的教育部门能不能跟他们这些国家设在香港的商会、银行合作,去做一些学生贷款计划?我们不用香港特区政府的钱,能不能跟东南亚国家的商会、金融界对接起来,让他们去设立他们自己国本的,信贷计划或者是资助计划,然后让他们的孩子来我们这里学习。
朱顺忠:逻辑上非常顺。您的思路比较超脱,也很有建设性。我估计您这个思路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港府。
邓飞:如果做得到的话,我们才真的从教育的角度去跟至少东南亚国家和中亚的国家做到一个民心的相通。我们的民心相通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我们是从教育的角度和金融的角度把它对接起来。
采访:朱顺忠
编辑:刘静
摄影:张玲梅
视频: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