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宦官童贯出使辽国,遭到辽国天祚帝的耻笑“南朝乏才如此!”当晚在宴射场上,童贯对一个随行文官说了几句,此人竟一举震惊辽国——只见这个叫张叔夜的瘦弱文官一支雕翎箭破空而出,百步外鎏金箭靶正中红心。 张叔夜那会儿刚过三十,脸上还带着书卷气,谁也想不到他能拉开一石半的硬弓。他出身开封官宦世家,父亲张耆曾在西北军中任职,临终前把祖传的角弓交给儿子,只说“文能安邦,武可护民,少了哪样都站不稳”。 所以张叔夜读的是《论语》《孙子》,练的是骑射剑法,十五岁时就能在家族靶场连续射中三十步外的铜钱孔,母亲总骂他“放着好好的文章不做,偏学那些厮杀本事”,他却笑说“万一哪天用得上呢”。 这次随童贯出使,张叔夜本是负责记录外交辞令的文官。童贯虽掌兵权,却因是宦官常被外邦轻视,辽国天祚帝在朝堂上的嘲讽,让随行的宋臣都攥紧了拳头,偏童贯忍着气没发作。到了宴射场,辽国武将轮番炫技,有个叫萧十三的宗室,一箭射穿了悬挂的银壶,引得辽国君臣哄笑,笑声里满是对宋使的轻慢。 童贯这时拽了拽张叔夜的衣袖,声音压得极低:“叔夜,能不能……给南朝争口气?”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宦官的身份本就容易被诟病,此刻被辽国当猴看,脊梁骨都快被戳穿了。张叔夜抬头看了眼童贯,又扫过辽国君臣那副得意模样,忽然起身,对着天祚帝拱手:“臣愿献丑。” 辽国臣子们先笑了。这文官穿的锦袍宽宽大大,握着弓的手指白皙,倒像是捏笔的,哪像能射箭的样子?连天祚帝都端着酒杯打趣:“南朝文官射箭,莫不是要把箭射到酒坛里?”张叔夜没接话,只从随从手里接过自己的角弓——这弓还是父亲留下的,弓梢刻着“守土”二字,他每次出使都带着,藏在行囊最深处。 他站定,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子微微侧过,左手稳稳托住弓身,右手三指搭箭。动作不快,却透着一股沉稳,仿佛不是在宴射场,而是在自家靶场。辽国的喧哗声渐渐小了,连风都似停了一瞬。 “嗡”的一声,弓弦震颤,箭杆在夕阳下泛着冷光,几乎是眨眼间,百步外的鎏金靶心“噗”地溅起木屑,那支雕翎箭正插在靶心最中间,箭尾还在嗡嗡作响。 全场静了足足三息。天祚帝手里的酒杯晃了晃,酒洒在龙袍上都没察觉。萧十三的脸涨成了紫茄子,刚才他射穿的银壶,离靶心还有寸许。童贯猛地拍了下大腿,差点站起来,又赶紧稳住身形,只是嘴角的笑藏不住了。 张叔夜放下弓,对着天祚帝再次拱手:“南朝人才,不在弓马,而在民心。只是若需护国安邦,文臣亦能挽弓。”这话不软不硬,既没炫耀,也没示弱,把辽国的嘲讽轻轻顶了回去。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就不怕射偏了,反而更丢人?张叔夜正对着父亲的牌位擦拭那把角弓,闻言笑了:“怕过。可想起父亲说的‘守土’二字,想起辽国君臣那眼神,手就稳了。咱是大宋的官,出去了,就不是个人的脸面了。” 这事儿过后,张叔夜在朝中仍做他的文官,编修史书,处理民政,仿佛宴射场上的惊鸿一箭只是偶然。可熟知他的人知道,他书房的墙上,始终挂着那把角弓,每逢朔望,必擦拭一遍。二十多年后,金兵南下,时年五十多岁的张叔夜披甲上阵,在汴京城外率孤军死战,城破后拒不降金,最终自刎明志。 你说,那支射穿鎏金靶心的箭,射中的仅仅是靶心吗?或许从那时起,它就射进了张叔夜心里,成了他一生“守土”的誓言。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样的臣子,不正是一个王朝最该珍视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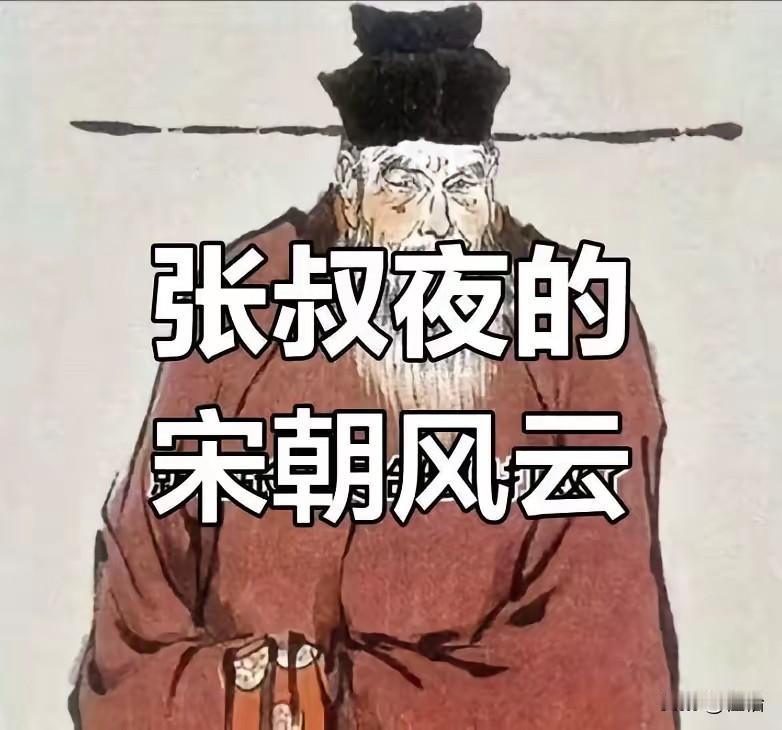










独唱团
打败水泊梁山大军的牛人,张叔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