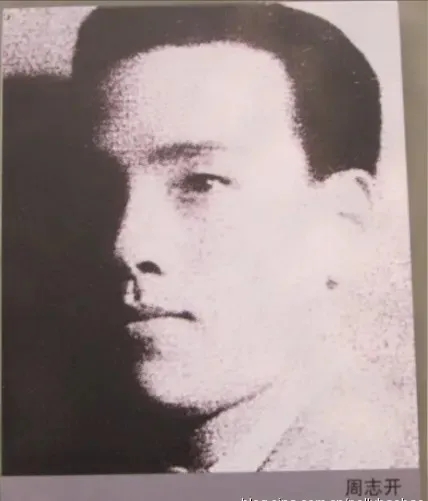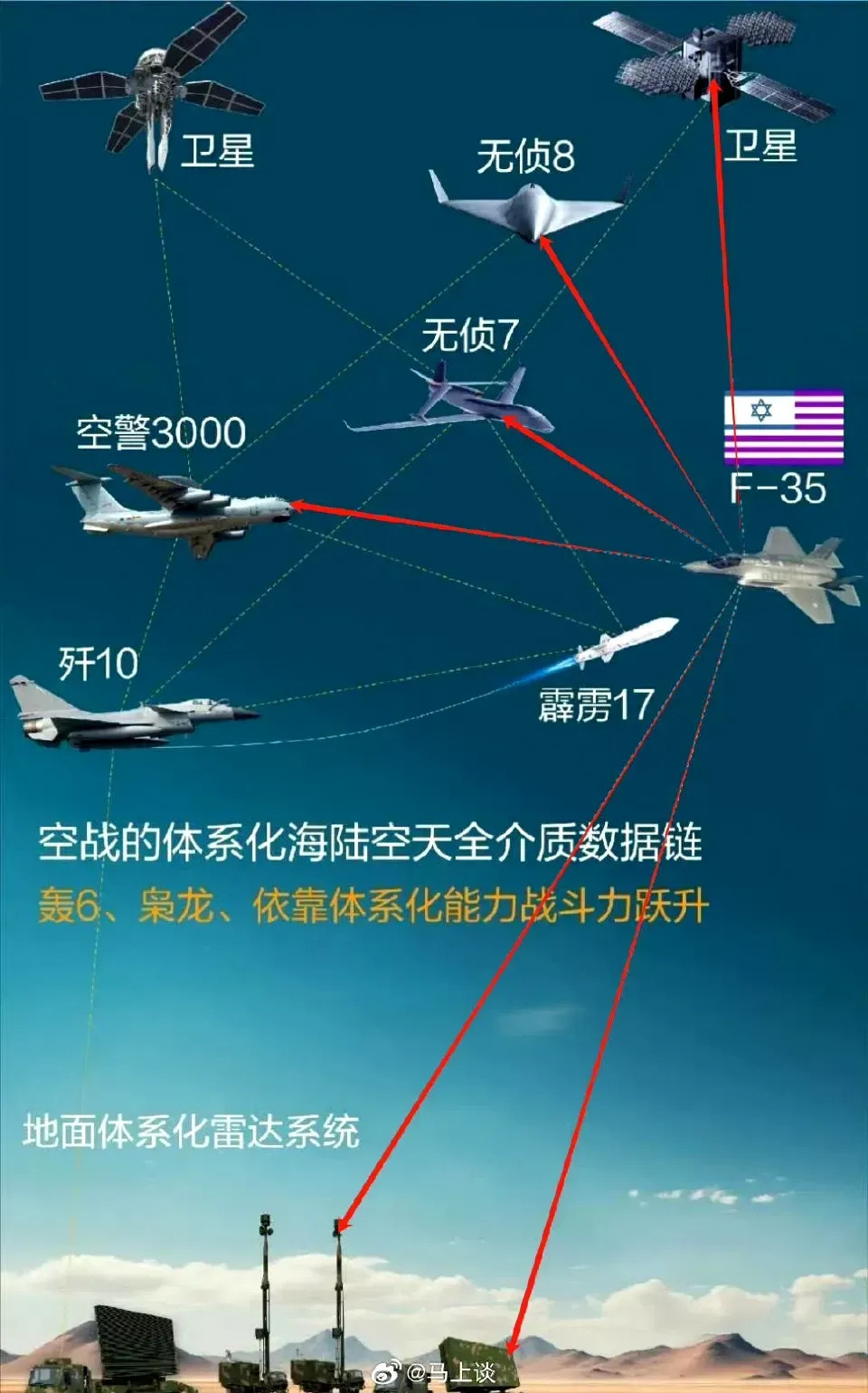1943年,梁山机场响起轰炸声:22架日军战机,发动偷袭,地面飞行员纷纷躲避,此时,却有一个身影,噌的一下,跳进机舱,离地只有60米,就拉动操纵杆急速上升,迎着敌机而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3年6月6日的梁山机场,阳光刺破晨雾,地面还散落着前夜任务的机油痕迹。
突然,防空警报撕裂寂静,22架日军战机像一群黑鸦压顶而来,中岛一式“隼”战斗机的引擎声震得机库铁皮嗡嗡作响。
炸弹在跑道炸开火花的瞬间,一个身影从掩体后箭步冲出,军靴踏着弹坑边缘的碎石,噌地跃入最近的P-40战斗机座舱。
周志开甚至没系保险带,舱盖还敞着,发动机的咆哮声中,机轮离地仅60米便强行拉起。
塔台无线电里传来急促的警告,他却迎着14架敌机俯冲而下,机炮的火线在云层划出猩红的轨迹。
那天,分水岭的山民看见三架日机拖着浓烟栽进长江,而那个单机杀入敌阵的年轻人,正是刚满23岁的空军第四大队中队长。
时间倒回1939年寒冬的柳州,周志开第一次参战的场景更显悲壮。
日军9架轰炸机编队逼近时,他驾驶的伊-15还是苏联援助的老旧机型,机枪射程比日机短200米,仪表盘上的油量表永远在警戒线徘徊。
发现敌机后,这个航校毕业刚满一年的见习官紧张得手心渗汗,120米距离开火时竟忘了计算提前量。
子弹擦着敌机翅膀掠过的刹那,油箱却意外爆炸,后来机械师检查弹孔才发现,那颗偏离的子弹鬼使神差打穿了输油管。
这场戏剧性胜利没让他兴奋,反而在日记里写下:“今日之胜实属侥幸,若技术精湛,何须老天赏脸?”
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自省,让这个出身名门的公子蜕变成令日军闻风丧胆的“空中死神”。
翻开周家泛黄的族谱,滦州周氏“诗书传家”的祖训赫然在列。
祖父周馥曾是清末力主洋务的封疆大吏,临终前将全部田产变卖兴学;父亲周学辉执掌直隶高等法院时,书房悬挂的自书条幅“国强方能民安”成了幼年周志开的启蒙读物。
1935年他偷偷报考笕桥航校那天,母亲在旗袍内衬缝进一枚玉观音,而父亲只递过剃刀说:“既以身许国,何须蓄发明志?”
航校同期的孙承宏回忆,这位总考第一的优等生训练时总多飞半小时,哪怕寒冬腊月也坚持用冷水擦飞机蒙皮,他说要熟悉战机的每道焊缝,就像剑客了解佩剑的每寸锋芒。
1940年重庆大轰炸最惨烈的阶段,周志开的座舱成了移动的伤疤博物馆。
5月29日空战后,地勤数出机身上99个弹孔和碗口大的炮弹窟窿,而他竟驾着这架残破的霍克Ⅲ击落两架日机。
战友们发现他有个致命习惯:总想活捉日军飞行员,有次追击受伤的零式战机,他冒险贴近到能看清对方飞行员惊恐表情的距离,用手势比划降落命令,直到敌机突然开火才忍痛击毁。
事后他说:“那飞行员看着不到二十岁,或许也是被迫参战……”
这种近乎天真的慈悲,在1943年6月6日梁山空战后彻底消失。
当目睹日军轰炸机向跳伞的中国飞行员扫射时,他红着眼眶打光所有弹药,三架敌机的残骸在长江溅起巨浪。
长阳县龙潭坪的老人们至今记得1943年那场反常的大雪,12月14日周志开执行侦察任务时,4架日军“钟馗”战机从云层俯冲偷袭,他的P-40N左翼断裂的瞬间,仍坚持向地面指挥部发完最后一份敌情电报。
残骸散落的山崖上,猎户发现他破碎的飞行表停在10点17分,而紧握的操纵杆上缠着那枚母亲给的玉观音。
整理遗物时,战友在日记本里发现未寄出的家书:“儿若殉国,勿葬衣冠冢,请将抚恤金全数捐建学堂,父亲常言,教育才是最好的航空母舰。”
如今重庆南山烈士陵园的青石墓碑上,24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43年冬天,而河北滦州的志开中学里,孩子们朗读课文的声音正穿透湛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