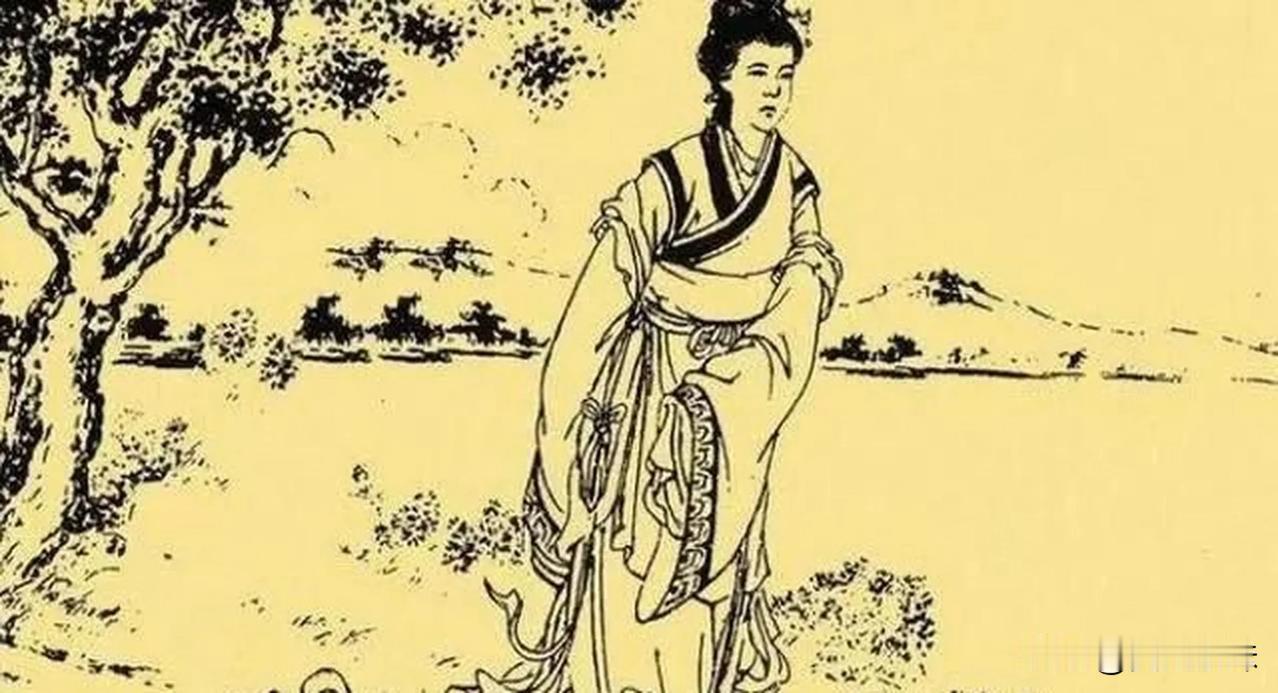古时,有个翰林编休修在老家娶了个女子为妻。隔日,两新人正拜见母亲,一个仆人突然跑进来,大声报喜:“老爷,您被升为翰林学士了。”可翰林却急得使劲给仆人使眼色,让他闭嘴。岳母和妻子听了,脸上顿无喜色。 古时候,有个翰林编修叫权某,回老家后又娶了个徐家的姑娘当老婆。新婚第二天,小两口去给老妈请安,这时候仆人权孝跟火烧屁股似的跑进来喊:“老爷,您升官啦,成了翰林学士!”权翰林一听,急得直眨巴眼。 堂屋里的铜香炉正冒着细烟,把“喜”字剪纸熏得微微发颤。 权某的老娘刚端起茶碗,手一抖,茶汤溅在青布帕子上,洇出个深褐色的圆。 “孝儿,”权某的声音压得低,带着点咬牙的劲,“谁让你在这时候说这个?” 权孝挠挠头,一脸懵。升官是天大的好事啊,昨儿驿站的人快马送文书,他还特意买了串鞭炮,就等老爷高兴了点呢。 徐家岳母干咳了两声,把刚要起身道贺的女儿按回椅子上。徐姑娘的帕子在手里绞成了麻花,新绣的并蒂莲被揉得变了形。 没人比权某更清楚这“喜”里藏着的祸。 他这翰林编修,说起来是京官,其实没实权,俸禄刚够养家。更要紧的是,他三年前在京城已经娶了正妻张氏,老家这门亲事,压根没敢报官备案——说白了,算瞒着上头纳的妾。 翰林学士可不一样。那是要给皇子们讲课的,得查祖宗八代的清白,家里有几房妻室、娶的是谁,都得写得明明白白报给吏部。 他在老家娶徐家姑娘,本是想着老娘病重,身边缺个知冷知热的人,等老娘好点就送她回乡下,自己还回京城跟张氏过日子。哪承想,官运偏偏这时候来了。 “娘,岳母,”权某搓着手,额角冒了层细汗,“这事儿……还没定呢,文书许是传错了。” 徐姑娘抬头看他,眼里的光暗了暗。她嫁过来前就知道权某有正妻,可媒人说“只是搭个伴伺候老太太”,她想着权家是书香门第,总不会亏待自己,没成想头一天就撞上个坎。 徐家岳母是镇上出了名的精明人,她捏着烟袋杆敲了敲桌角:“权老爷,咱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这官要是真升了,我家姑娘……算什么?” 这话戳在了权某的痛处。 按律例,官员重婚是要丢官的,严重了还得蹲大牢。他要是认了徐姑娘,前程就没了;不认,徐家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岂能容女儿无名无分? 权孝这才咂摸过味来,脸“唰”地白了,缩在门口跟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 “岳母放心,”权某咬了咬牙,“我不会让她受委屈。” 可这话在律法面前,轻得像片羽毛。 当天下午,权某就把驿站的文书藏了起来,对外只说“升迁的事黄了”。他给徐姑娘买了支赤金簪子,插在她发间时,手却在抖。 徐姑娘摸着冰凉的簪子,没笑。她夜里听见权某跟婆婆叹气,说“要么丢官,要么对不住徐家”,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没过半月,吏部的人真来了。 不是来道贺的,是来查“翰林院编修权某是否有隐瞒家室”的。原来有人眼红他升官,暗地里递了帖子,说他“在乡私纳民女,罔顾礼法”。 权某把心一横,当着吏部差役的面,只认了京城的张氏是正妻,说徐姑娘是“母亲认的义女,留在家中伺候”。 徐姑娘躲在里屋,听见这话,手里的针线“噗嗤”扎进了手指。血珠滴在绣了一半的枕套上,像朵没开就谢了的花。 徐家岳母气得差点晕过去,跑到权家大闹了一场,最后拿了权某赔的五十两银子,骂骂咧咧回了家。 后来权某还是当了翰林学士,给太子讲《论语》时,总在“其身正,不令而行”那句上卡壳。 徐姑娘没走,依旧在权家伺候老太太。只是再没人叫她“少奶奶”,下人都改称“徐姑娘”。她头上那支赤金簪子,被收进了妆匣最底层,蒙了层厚厚的灰。 有回老太太病重,拉着她的手叹:“委屈你了。” 她笑了笑,给老太太掖了掖被角:“日子总要过的。” 只是没人知道,每个落雪的夜里,她都会对着窗纸上京城的方向发呆。那里有她没见过的正妻张氏,有她男人用一个谎言换来的前程,还有她自己,被揉碎在礼法里的青春。 这世上的喜,从来都分三六九等。有的喜能敲锣打鼓地喊,有的喜,得捂着、藏着,一不小心露了缝,就成了剜心的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