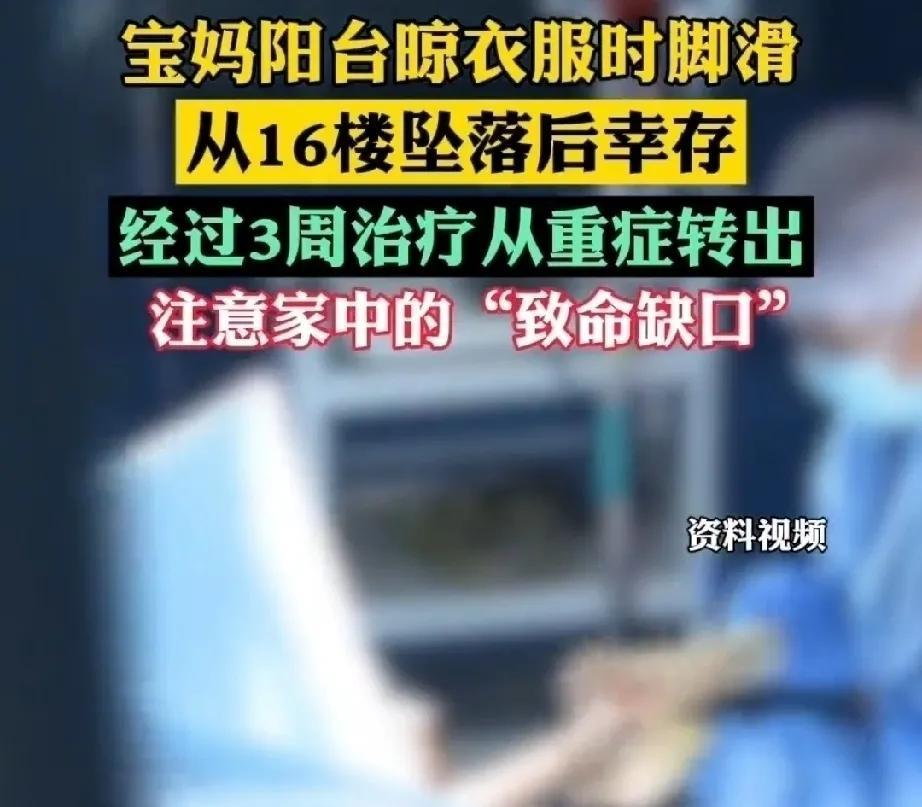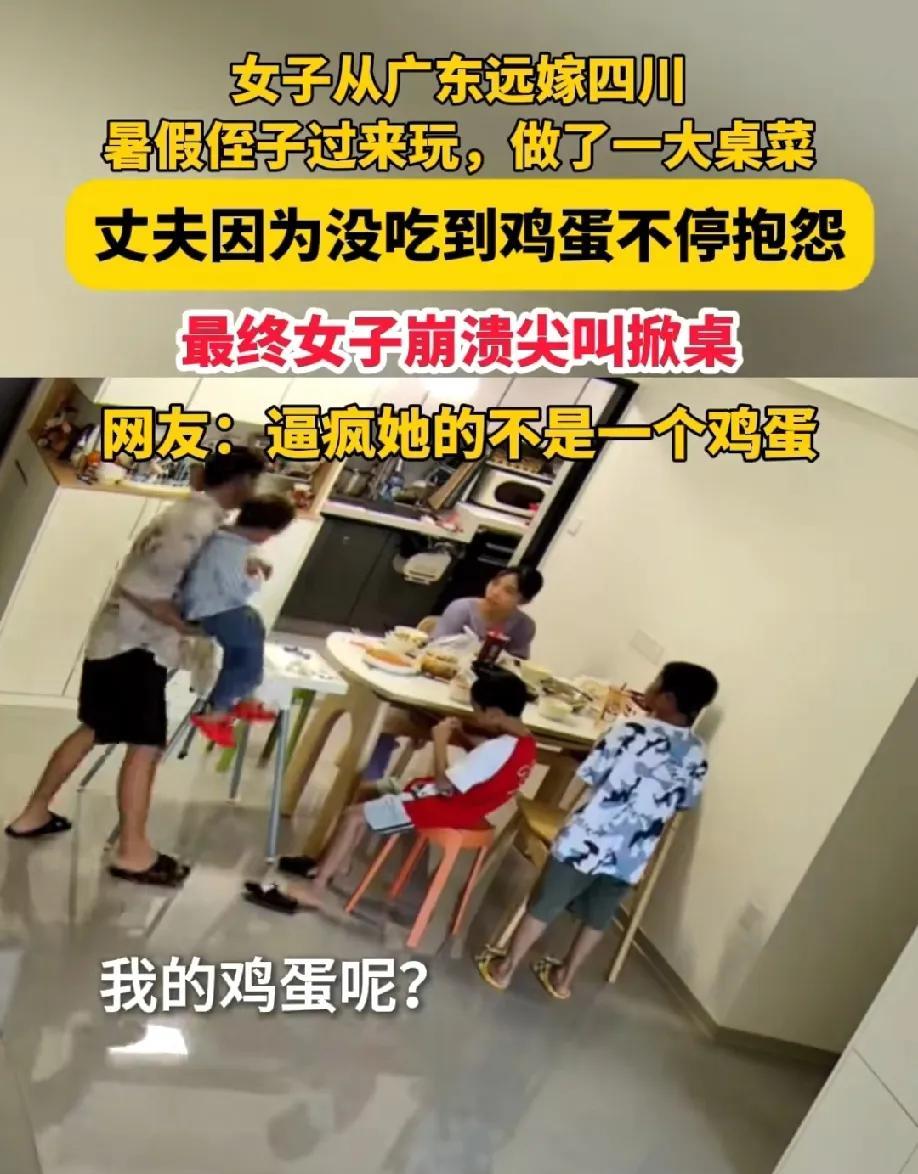清嘉庆年间,山西女子顾月波女扮男装,奉父命到江南采购茶叶。当乘船渡过长江时,突然遇到了劫匪。 顾月波年方十八岁,父亲是个茶叶商人,在太原经营店铺。嘉庆年间,世道并不太平,匪患滋生。顾掌柜的为什么让妙龄女儿远下江南去采购,难道不知路途危险?这其中有个缘故。 顾掌柜夫妇膝下无子,就顾月波这一个女儿。两口子从一开始就拿女儿当儿子养,衣着打扮举止言行无不仿照男孩。顾月波偏又喜欢舞枪弄棒,和男孩子打架从没输过,顾掌柜索性请武术教师教她武功。顾月波天性聪慧,几年下来,刀功剑术精湛绝伦,健壮男儿都不如她。尤其使得一手好弹弓,仰射空中飞鸟,无不应声而落。 江风裹着水汽,拍在船板上噼啪响。 顾月波缩在船尾,青布短褂沾了些潮气,手里摩挲着个油布包——里面是父亲给的采买清单,还有她藏了多年的牛角弹弓。船行到江心,两岸的芦苇荡忽然“哗啦”一阵响,三只小划子像箭似的窜出来,船头的汉子举着明晃晃的刀,喊得比浪头还凶:“要命的把钱帛扔过来!” 船上的客商顿时哭爹喊娘,有个穿绸衫的胖子直往舱底钻,差点把货箱撞翻。顾月波眯了眯眼,瞅见为首那劫匪的腰带松松垮垮,刀鞘上还挂着块褪色的玉佩——倒像是去年在太原庙会见过的劣质货。 “小郎君,你愣着干啥?”旁边的老茶农拽了她一把,“快把钱藏起来啊!” 顾月波没动。她的弹丸藏在袖管里,是用五台山的青石打磨的,又圆又硬。小时候师父说,打人要打七寸,对付这些毛贼,不用真刀真枪,卸了他们的力气就行。 划子“砰”地撞上船帮,那带头的劫匪一脚跨上来,刀尖子差点戳到顾月波鼻尖。“臭小子,钱呢?”他唾沫星子喷了顾月波一脸,眼神在她身上溜来溜去,“瞧你细皮嫩肉的,莫不是哪家跑出来的小少爷?” 顾月波突然笑了,左手猛地攥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右手从袖管滑出弹弓,“啪”地架在他脖子上。动作快得像江里的游鱼,谁都没看清她是怎么出手的。 “爷的钱,在你背后。”她压低了嗓子,声音故意粗嘎些。 劫匪一愣,刚要回头,就觉手腕一阵剧痛,刀“哐当”掉在地上。顾月波的弹弓已经换了方向,对准他身后的两个同伙——那俩人正伸手去抢客商的包袱,她手指一松,两颗青石弹丸“嗖嗖”飞出去,一颗打在左边那家伙的肘关节,一颗正中右边那人的膝盖。 “嗷!”两声惨叫几乎同时响起。 带头的劫匪这才慌了,想挣扎,却被顾月波反剪了胳膊,疼得直哆嗦。“你……你是练家子?” “谈不上。”顾月波瞥了眼舱里吓得发抖的众人,“就是见不得有人欺负老实人。” 这时船老大哆哆嗦嗦地喊:“官船!前面有官船过来了!” 劫匪们一听,魂都飞了。那两个受伤的互相搀扶着往划子上爬,带头的也急得蹬腿:“小爷饶命!小爷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 顾月波松了手,抬脚把他踹回划子。“滚。”她捡起地上的刀,往水里一扔,溅起的水花正好打在劫匪脸上。 划子狼狈地划远了,江面上还飘着那劫匪掉的玉佩。顾月波弯腰捡起,掂量了两下,扔给旁边的老茶农:“大叔,给娃当个玩意儿。” 老茶农这才缓过神,摸着玉佩直咋舌:“小郎君好本事!看你年纪轻轻,这身手……” 顾月波挠了挠头,赶紧岔开话:“我爹教的,乡下野路子,不值当说。”她低头整理短褂,忽然发现领口的布松了些,露出里面半抹水红的衬里——那是临行前娘偷偷给她缝的,说女儿家总得有点念想。 她慌忙把领口系紧,耳尖有点发烫。 船过了江心,风平浪静。有客商凑过来要请她喝酒,她摆摆手躲回船尾,摸出弹弓对着天上的水鸟比划。阳光透过水汽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淡淡的光影,倒比舱里那些惊慌失措的男人,多了几分沉静的英气。 老茶农远远看着,忽然跟身边人嘀咕:“这小郎君眉眼倒是俊,就是性子太烈,将来哪家姑娘敢嫁……” 顾月波没听见。她正望着江南的方向,心里盘算着到了苏州,要先去山塘街看看新茶,再找父亲说的那个老茶商。至于刚才的惊险,像江里的泡沫,破了就散了——她是来办正事的,可不能因为这点小麻烦,误了父亲的托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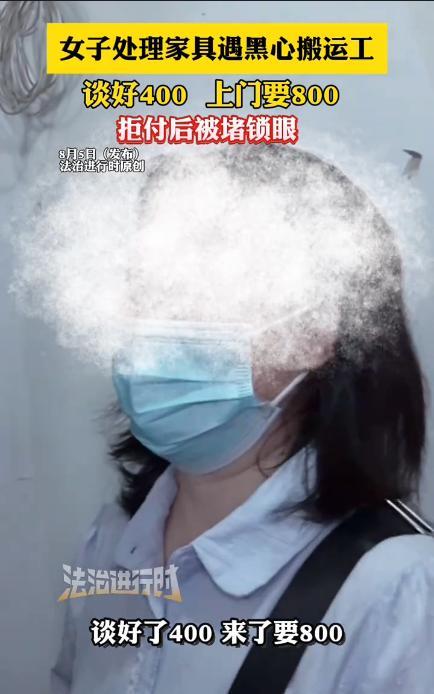
![果然大家都畏畏缩缩闯了很多祸[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1316604192503546129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