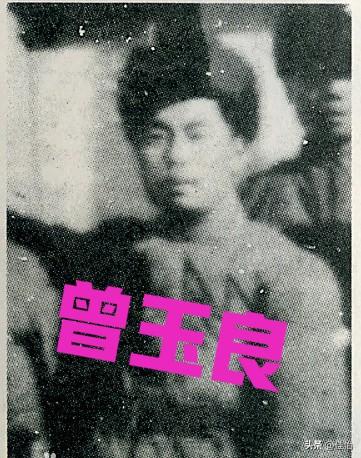1942年4月的冀南平原,冻土被疾驰的马蹄踏成黑泥,日军骑兵中队500骑兵对战129师骑兵团300骑兵,日军骑兵中队追着骑兵团打,嚣张的表示要灭了骑兵团。让人意外的是回来时,只剩30名残兵被骑兵团追着打。 话说在这黄沙深处,策马飞驰的八路军团长曾玉良在颠簸中勒紧缰绳。他左臂缠着浸血的绷带,右手却牢牢按住怀里的轻机枪。 没人知道,这道绷带下的伤口,是今早突围时被日军马刀划开的。当时他正指挥后卫部队掩护村民转移,日军骑兵像疯狗似的扑过来,马刀劈向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娘,他抬手用枪托格挡,刀刃就从胳膊上带了过去。血顺着袖口淌进枪套,他愣是没吭一声,反手一梭子撂倒两个日军,吼着“跟我冲”,硬生生把村民护进了地道。 曾玉良打骑兵那会儿,冀南还没这么多黄沙。1938年他刚从步兵转骑兵,第一次摸马镫都摔了个跟头。老团长骂他“笨得像头驴”,却还是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练。“骑兵不是骑着马的步兵,”老团长教他,“马是腿,刀是胆,脑子是魂。” 他记着这话,别人练骑术时他练劈刀,别人睡了他还在沙盘上摆地形,把冀南的沙丘、河沟、枣树林子全刻在了脑子里。 日军这次来的骑兵中队,是号称“常胜部队”的坂田支队,装备比骑兵团好得多——战马高大,马枪射程远,连马刀都比八路军的长半尺。开战前,日军小队长在马上叫嚣“一小时踏平骑兵团”,确实,起初骑兵团只能且战且退,不少战士的战马被流弹打中,摔在地上还没爬起来就被日军围住。 曾玉良在马上看着战友倒下去,牙咬得咯吱响。他知道硬碰硬不行,坂田的骑兵擅长远距离射击,可一旦近身,他们那套刻板的劈刺动作就不灵了。“往青纱帐钻!”他突然扯着嗓子喊,调转马头冲向一片刚冒芽的高粱地。 日军果然追了进来。高梁秆子刮得马脖子直甩头,他们的队形一下子散了。曾玉良瞅准机会,抬手一枪打穿最前面那个日军的头盔,同时大喊“下马!近战!”300骑兵“唰”地跳下马背,借着高粱秆掩护,端着马枪、挥着大刀贴了上去。日军在马上转不开身,成了活靶子,惨叫声混着马蹄惊惶的乱响,在青纱帐里炸开。 打到正午,曾玉良左臂的血把绷带浸成了紫黑色,他却越打越猛。看见一个日军想策马逃,他几步追上去,左手按住那日军的后腰,右手抽出腰间的鬼头刀,一刀就劈断了马缰绳。那日军摔在地上,他踩着对方的胸口,吼道“你不是要灭我们吗?” 最后剩下的30个日军,早没了起初的嚣张。他们丢了马,背着枪往据点跑,曾玉良带着战士们骑马追,子弹在他们脚边溅起泥花。有个日军跪地求饶,曾玉良却没停,他知道,对这些烧杀抢掠的-生心软,就是对冀南百姓犯罪。 战后清点,骑兵团也折损了不少弟兄。曾玉良蹲在沙丘上,给牺牲的战士整理衣襟,发现有个十八九岁的新兵,兜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窝头。他想起这孩子昨天还说,等打跑了日军,要回家娶邻村的姑娘。 有人说,这次胜仗是运气好,钻进了青纱帐。曾玉良却摸着胳膊上的伤口摇头。他打骑兵这些年,见过太多以少胜多的仗——不是靠运气,是靠敢把命豁出去的狠劲,更是靠对这片土地的熟稔。日军骑着高头大马,却分不清哪片洼地能陷马,哪片枣树林能藏人;他们拿着好武器,却不懂老百姓会悄悄给八路军报信,会把地道挖得像蜘蛛网。 你说,在装备悬殊的战场上,真正让弱者变强的,是地形的掩护,还是藏在身后的民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