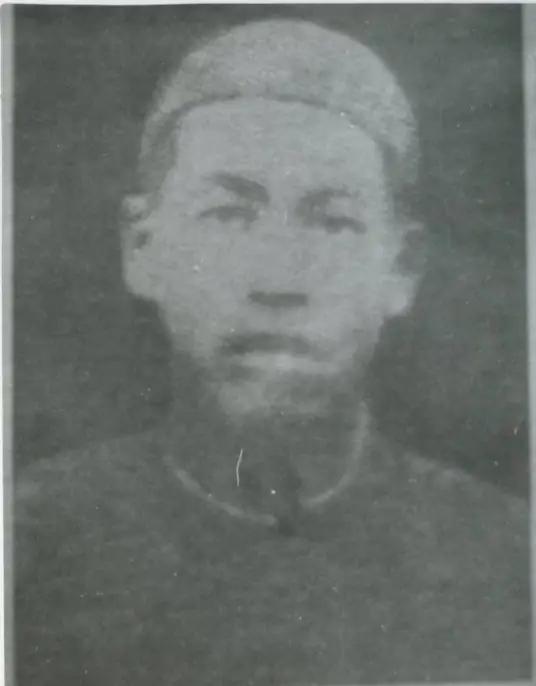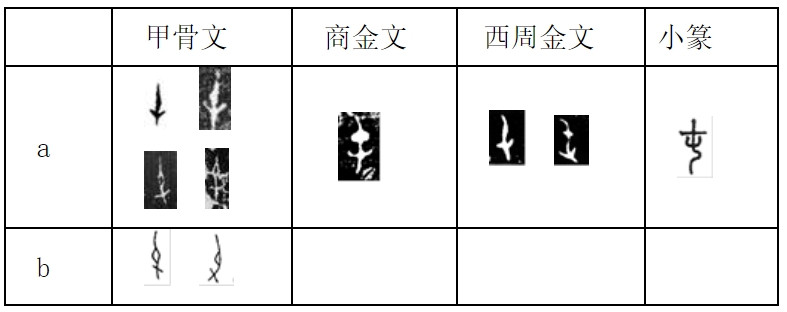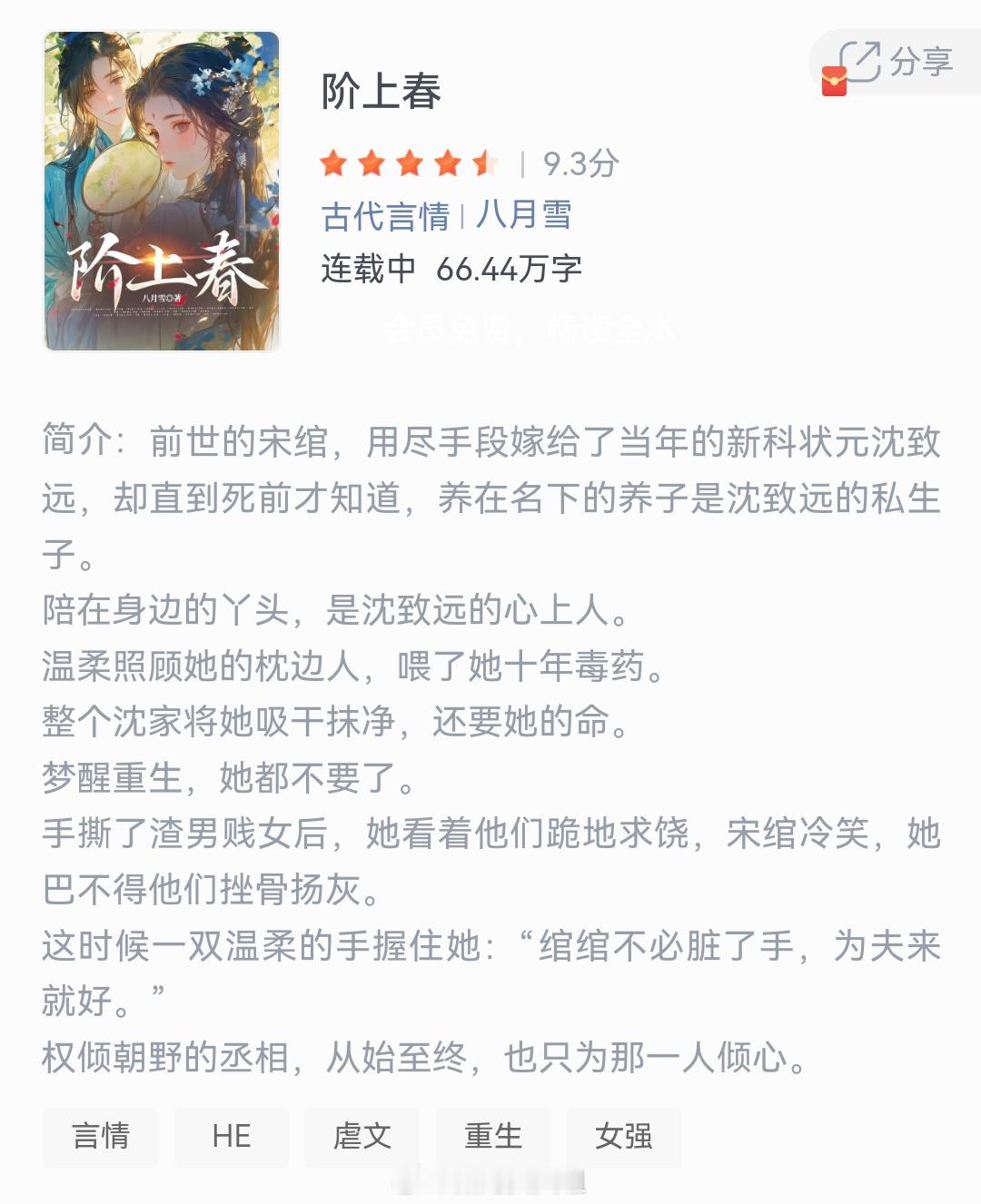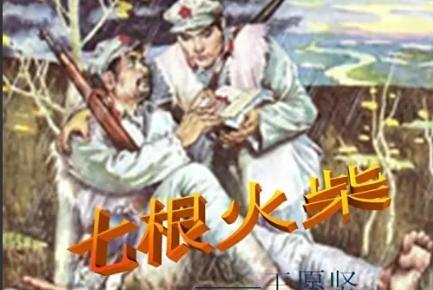1922年,王国维的发妻死于难产,扔下了三个孩子。产房外,王国维坐在板凳上,两眼无光地看着前方,原本是想着等妻子生了孩子后,在家里好好陪陪她的,毕竟出去好长时间了,终于回来了。 1907年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在上海的寓所里,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为难产,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扔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产房外,王国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条板凳上,两眼无光地看着前方。 他心里原本的盘算,全碎了。 他想着,等妻子这次平安生下孩子,自己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好好陪着她。毕竟为了求学、为了生计,夫妻俩聚少离多,他亏欠她太多了。可他等来的,却是天人永隔。 那一刻,这位日后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只是一个失去了挚爱的、手足无措的普通丈夫。 他和发妻莫氏的婚姻,是顶顶老派的包办婚姻。没什么风花雪月,就是过日子。但日子这东西,就像文火炖肉,时间长了,味道自然就出来了。王国维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他对妻子很体贴;莫氏呢,也是个传统的贤惠女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日子平淡,但安稳。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安稳,可能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可王国维心里有团火,他不甘心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甲午一战,把整个国家的读书人都打蒙了,他想出去看看,学点能真正“救亡图存”的本事。1900年,在朋友的资助下,他终于去了日本。 这一走,就把整个家的重担,都甩给了莫氏一个人。 一个弱女子,拉扯着几个孩子,还要日夜操劳家务。那种辛苦,咱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更磨人的,是思念。丈夫远在异国,音信难通,那种牵肠挂肚,是会刻在脸上的。 几年后,王国维从日本回来,一进门看到妻子,竟有些恍惚。他记忆里的莫氏,虽不惊艳,却也温婉清秀。可眼前的妻子,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却憔悴得像一朵快要败了的花。 他心里五味杂陈,愧疚、心疼、无奈,全都涌了上来。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化成了一首词——《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很多人都爱最后这两句,说它道尽了时光无情。可我觉得,这首词最痛的,是那句“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我走的时候你好好的,怎么回来你就变成这样了?这种重逢时的心碎,比离别本身更扎人。 他看懂了妻子为这个家的付出,看懂了岁月在她身上刻下的痕迹。他本想用余生去补偿,可老天爷却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1907年,莫氏的生命,就定格在了那个闷热的夏天。 妻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国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家里乱成一锅粥,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几岁,小的尚在襁褓。一个男人,既要治学,又要当爹当妈,那种崩溃,可想而知。 日子总得过下去。在亲友的劝说下,续弦的事被提上了日程。 在当时,这是一个男人对家庭和孩子最实际的责任。王国维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莫氏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怕后妈对孩子不好,思来想去,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的决定:他娶了莫氏的外甥女,潘丽正。 潘丽正比王国维小十几岁,是个温和本分的姑娘。她嫁过来,与其说是做了妻子,不如说是接过了表姑留下的重担。她对莫氏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后来自己又生了五个,把一个偌大的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可以说,没有潘丽正的操劳,王国维根本不可能安下心来,成就他后来的学术巅峰。潘丽正就像一块压舱石,稳住了王国维那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家船。 但生活这剧本,总是不按常理出牌。王国维的内心世界,远比外人看到的要复杂和痛苦。他一生都有一种难以排解的悲观情绪,他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越研究,似乎对人世的苦看得越透。 1926年,他最疼爱的长子王潜明病逝,年仅28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年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尽。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个在丈夫的光环下显得有些模糊的女人,从此开始了她长达三十多年的守寡生涯。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单身母亲拉扯七个孩子,其中的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她没有再嫁,靠着变卖丈夫的藏书和亲友的接济,硬是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培养成人。 她不像莫氏,能激起丈夫写下“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哀叹;她也不像丈夫,能用一场决绝的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她的人生,就是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是琐碎而漫长的坚守。 潘丽正女士,她不懂那些高深的学问。她只知道,丈夫没了,天塌了,但孩子们还得吃饭,还得长大。她选择了最笨拙、也最伟大的方式——“活着”。 她用自己漫长的、辛劳的一生,替丈夫偿还了对这个家、对孩子们未尽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