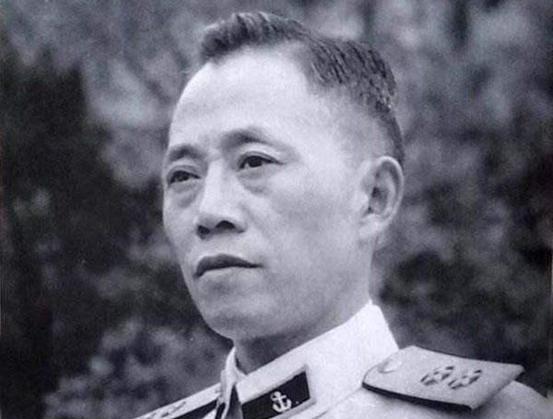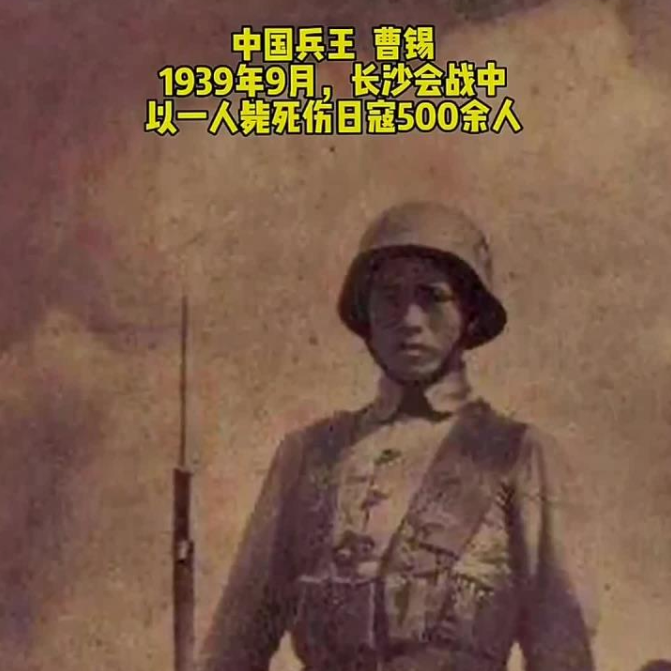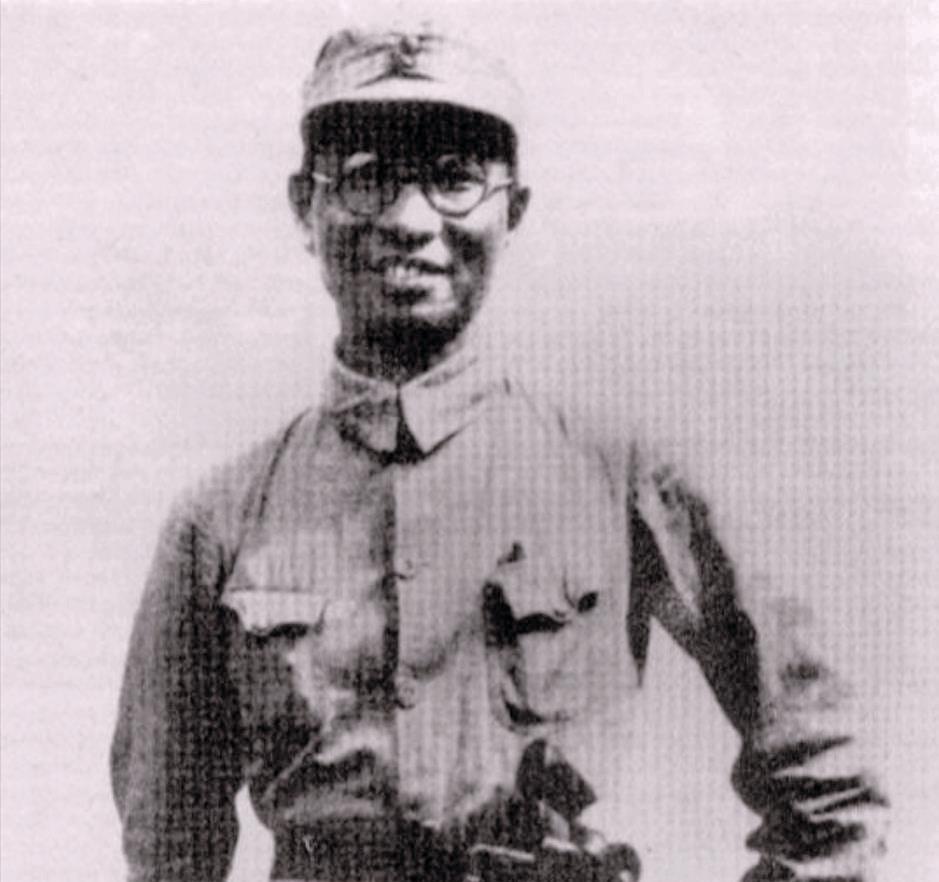抗战时,陈赓说:"山梁狭窄,部队不便于展开,可敌人在我们的突然打击下,更无法展开队形进行还击。请问,在独木桥上遇敌,怎么打?” 1938年的晋东南,春天来得慢,山梁上的风像刀子,吹得人眼睛生疼。 潞城和黎城之间的那条邯长大道,远看不过是一条灰白色的线,却成了当时最紧要的地方。 日军的辎重车一趟趟从这儿走,马蹄声压着车轮,碾出长长的辙痕。 对他们,这是补给;对八路军,那就是命脉。 刘伯承那时愁得不轻,地图摊开在桌上,指头一点,就是长生口。 那场伏击打得凶狠,敌人死了一百多,可自己的伤亡也差不多。那些都是跟着长征走过来的老兵,掉下去一个就少一个。 刘伯承说不出口的痛,憋在心里。 他想换个打法,不是去正面拼,而是像鹰盯着兔子一样,找准时机一下扑下去。 就这么定了,769团去敲打黎城,制造动静,把潞城的鬼子引出来;386旅埋在半路上,等敌人中计。计划听起来不错,可真到神头岭那一带,大家却傻了眼。 地图上画着沟谷,结果走到现场才发现,是一条光秃秃的山梁,宽不过一百米,两边光板板,没树,没草,什么遮蔽都没有。 放眼望去,就像把人摆到案板上。 有人低声嘀咕:这地儿能打?一旦暴露,部队没地方展开,敌人的炮火一盖,谁也跑不了。 干部们挤在一起,面面相觑。 陈赓没有说话,蹲下身子,揪了一把旧工事的土,又捻了捻压倒的草。他心里有点明白了。地形对己方不好,可对敌人更是要命。 纵队拖得老长,在梁上走,就像蛇盘在棍子上,只要先下手,就能一刀切成几段。 他转身对政委王新亭笑了一下:“独木桥上遇敌,谁先动手,谁就占尽便宜。”这句话传开,谁也不再犹豫。 布置紧锣密鼓,771团守在正面,准备一刀拦腰;772团埋在申家山,等着从高处扑下;补充团挤在东边,随时夹击。 最要紧的是赵店桥——潞城与黎城的唯一通道。 特务连摸黑过去,点火烧桥,木头劈啪炸响,火光映得河面通红。 桥塌下去,援军的路也断了。 伏击的工夫都下在细节里,陈赓一遍遍叮嘱:旧土别乱动,草穗踩倒了要扶起来,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顺。 士兵趴在工事里,连呼吸都压得轻。 新兵们手里握着梭镖,手心全是汗,紧张得直咽口水。 老兵拍拍他们的肩,自己心里也没底,可脸上还是一副轻松样。 黎城那边的769团,夜里就摸了过去。 破庙里亮着一盏手电,陈锡联指着地图布置任务。 凌晨四点,一营翻上城墙,轻机枪架好,火力压住,手榴弹接二连三扔下去。 日军守军被打懵,不到半个小时,街道上尸体横陈。 可769团并没有死攻,打出动静就收了手,边打边撤,把火留在外围。 黎城的骚动,就像扔下去的一块石子,波纹直传到潞城。 第二天早晨,潞城出动的不是援兵,而是辎重队。 近千人,车马长队,马匹驮着粮食弹药,大部分是辎重兵,身上不过短剑。几百号人,拉成长龙,在神头岭的山梁上晃晃悠悠走着。 十点钟,队伍正好钻进埋伏圈。 前头的骑兵擦着工事走过,离埋伏的战士不到二十米,还以为是废弃的土堆。 就在他们放松的那一瞬间,信号枪响,整条山梁像炸开了。 机枪同时开火,子弹雨点一样砸下去,手榴弹齐声炸响,火光、硝烟、尘土全卷到一块儿。 敌队立刻乱了。 前面的车冲不过去,后面的兵挤上来,整个队伍像被卡住的蛇。 八路军战士们从工事里、草丛间蹿出,刺刀、大刀、梭镖全上。 一个炊事员抡起扁担,把敌人脑袋劈开,司号员抱着石头往下砸,血溅在脸上也顾不上擦。有人身上中了几枪,用毛巾勒紧伤口,硬是扑上去再刺倒几个鬼子。 申家山上的772团二营,这时候像猛虎下山,从高地一泻而下,把敌人彻底割断。 日军缩在神头村,借着房屋固守,死死扛着。 陈赓急了,冲着部队下令:“哪怕拼光,也要夺下村子!”炮火轰过去,排长蒲大义带人硬闯,血肉横飞,把敌人赶出屋子,自己也伤亡过半。 叶成焕带队冲进村里,里外夹击,把敌人打得魂飞魄散。 等到下午,潞城终于派来救援,可赵店桥早成焦土,河对岸只能干瞪眼。 386旅打了一整天,弹药快打光,趁着天色暗下来,收部撤到申家山。 夕阳照着,梁上满是尸体,灰土都被血浸得发黑。 风吹过,腥气弥漫,战士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下去,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畅快。 战报后来传开,说歼敌上千。 日军的旬报只认三百余。档案对比下来,史学家推算大约五六百。 数字有落差,可不重要。 重要的是,108师团的辎重线被切断,报告里不得不写下“从未有过的损失”。 那一仗震动极大。 晋东南的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说八路军在神头岭把鬼子堵死在山梁上。 战士们把缴获的三八大盖举在手里,穿上敌人的棉大衣照相,笑容里有疲惫,有血,也有满足。 夜幕落下,神头岭上的风吹过旧工事,吹过断桥的焦黑木梁,吹过还在冒烟的房屋。 公路安静下来,只有马匹的尸体横在路中间,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还没看懂,怎么会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