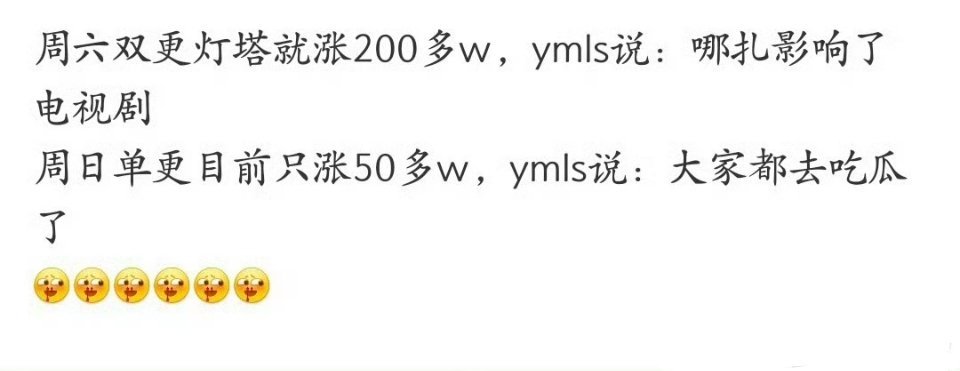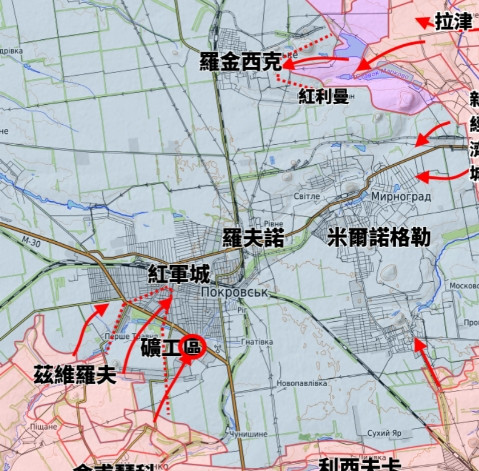打耳光的叛徒叫张锡蔚,曾是赵尚志一手带出来的兵。当年在珠河游击区,赵尚志把自己的棉裤撕了块布给他包扎冻裂的脚,还笑着说:“咱抗联的兵,腿不能软,心更不能软。”他那时跟着赵尚志打了三年仗,端过鬼子的炮楼,抢过敌人的粮车,手上沾过血,也流过泪,谁都没料到他会在1941年冬天带着队伍投了敌。 验尸的汉奸是伪警察署的小队长,平日里在鬼子面前点头哈腰,见了抗联的尸体却格外嚣张。他踹赵尚志脑袋时,嘴里还骂骂咧咧:“赵尚志啊赵尚志,你也有今天!”张锡蔚的巴掌甩得又快又响,打得那汉奸捂着脸愣在原地。周围的鬼子端起枪对准他,他却梗着脖子没躲,眼睛盯着雪地里赵尚志圆睁的双眼——那双眼,曾在深夜的篝火旁跟他讲过“赶走鬼子回家种地”的念想,曾在突围时吼着“跟我冲”带头杀向敌群。 没人知道张锡蔚那一刻在想啥。或许是想起1938年冬天,赵尚志背着受伤的他在雪地里走了三十里,自己冻掉了两个脚趾头也没松手;或许是看见赵尚志胸前那枚磨得发亮的铜制党徽——那是当年入党时,老书记亲手别在他胸前的,后来他叛变时偷偷摘了,此刻却觉得那点光亮刺得人眼睛疼。他吼出那句“你是没有手吗”,更像在骂自己:当年跟着赵尚志学的“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 赵尚志的尸体被鬼子抬去示众时,张锡蔚跟在后面,头埋得很低。街边上,有老百姓偷偷抹眼泪,有人认出赵尚志那件打满补丁的羊皮袄,那是去年冬天一个大娘硬塞给他的,他总说“留给伤员穿”,自己却裹着单衣在山岗上放哨。张锡蔚听见有个老头叹着气说:“赵司令打鬼子不含糊,是条汉子啊……”他的手攥成了拳,指甲掐进肉里,渗出血珠也没知觉。 后来有人说,张锡蔚那一巴掌,是怕鬼子糟践赵尚志的尸体,也算留点念想。可他终究是叛徒,三个月后被鬼子当成“没用的棋子”枪毙在江边。临死前,他突然朝着赵尚志牺牲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里嘟囔着“我对不起你”,声音轻得被江风卷走,没几个人听见。 赵尚志的故事,早刻在了东北的黑土地里。他19岁入党,27岁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带着队伍在白山黑水间跟鬼子周旋了十年,打了大小百余场仗,鬼子悬赏一万元买他的人头,却连他的影子都难摸到。战士们说他“身经百战,枪不离手”,老百姓说他“走到哪,哪就有盼头”。就连伪满的档案里,提到他都得写“赵尚志部作战勇猛,难以剿灭”。 那汉奸踹向赵尚志脑袋的一脚,踢不灭英雄的骨头;张锡蔚那记带着悔意的耳光,也洗不掉叛变的污点。可历史记着清楚:谁为这片土地拼过命,谁在背后捅刀子,雪会埋住血,却埋不住人心的秤。就像赵尚志生前常说的:“鬼子再横,也挡不住咱中国人要过好日子的心。” 如今鹤立县的山岗上,立着赵尚志的纪念碑,碑前的雪每年都有人扫,碑后的松树长得笔直。路过的人总会停下脚,听老人讲那个冬天的故事,讲那个打向汉奸的耳光,讲那个永远活在东北人心里的抗联司令。有些精神,就像黑土地里的种子,不管风雪多大,总能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