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年,武则天赐儿子李贤白绫,李贤痛心疾首道:“我已被废为庶人,母后何苦还要赶尽杀绝,把我流放到巴州再杀我?汉朝的吕后也不及她狠毒!”说完,大臣丘神勣把白绫摆在他面前。 巴州的秋风裹着湿气,吹得窗纸簌簌作响。李贤盯着那卷雪一样的白绫,指节攥得发白。他想起被流放那天,长安的朱雀大街上落着细雨,母亲站在城楼上,凤袍的衣角被风掀起,像只展开羽翼的鹰。那时他还抱着一丝念想——毕竟是亲生骨肉,流放到这偏远之地,或许只是母亲敲打他的手段。 “殿下,时辰到了。”丘神勣的声音没什么起伏,眼神却瞟向门外。李贤知道,门外的甲士正按着刀柄,这位“钦差”不过是来见证一场早已写好的结局。 他忽然笑了,笑声撞在简陋的土墙上,碎成一片凄凉。“丘大人可知,我十岁那年,母后教我读《汉书》。读到吕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我吓得攥紧她的衣袖。她说‘妇人掌权,不狠便成刀下鬼’,那时我只当是戏言。” 丘神勣垂着眼,没接话。他是武将出身,却也听过当年的传闻——李贤曾是朝野公认的贤太子,监国时把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连老臣们都赞他“有太宗遗风”。可自从那本《少阳正范》送到武则天案头,一切就变了。那是李贤亲手编的书,字里行间都是对“嫡长继承”的强调,像根刺,扎在了想称帝的母亲心上。 李贤走到案前,拿起桌上半首没写完的诗。墨迹已经干了,是他昨夜写的:“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他本想写完这最后一句,如今看来,不必了。 “你说母后会想起洛阳的枇杷树吗?”他忽然问丘神勣,“那年我染了风寒,她亲自在宫院里种了棵枇杷,说等结果了,给我熬枇杷膏。后来树结果了,我却成了她眼里的‘逆子’。” 窗外的风更紧了,带着巴州特有的潮湿气息。李贤脱下身上的旧袍,那是他做太子时穿的,料子早就磨薄了,却还留着母亲亲手绣的云纹。他把袍子铺在桌上,又将那半首诗压在下面,像是在整理一件体面的遗物。 “告诉她,我不恨她了。”他拿起白绫,指尖触到冰凉的布料,“只是可惜,她终究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为了权力,连骨肉都能当棋子。” 丘神勣看着他把白绫绕上房梁,忽然别过脸。他想起出发前,武则天召见他时的模样。太后没说太多话,只递给他一枚玉佩,说是李贤小时候戴过的。“告诉他,黄泉路上,别冻着。”那时太后的声音很轻,指甲却掐进了掌心。 白绫绷紧的声音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李贤闭上眼的瞬间,好像又回到了长安的东宫。母亲坐在窗前,给他梳发,金簪穿过发丝时,她说:“贤儿要记住,皇家的孩子,要么成为九五之尊,要么成为铺路的石子。”那时他不懂,只觉得母亲的手指有些凉。 丘神勣带着李贤的遗物回洛阳复命。武则天正在批阅奏折,看见那半首诗和旧袍,半天没说话。案上的枇杷膏还冒着热气,是御厨按当年的方子熬的,可那个等着喝膏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把他葬在雍州。”她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碑上别刻名字,就写‘唐故王子’。” 后来有人说,武则天夜里常独自去偏殿,对着一幅少年画像发呆。画里的少年穿着太子冠服,眉眼清朗,像极了年轻时的李贤。画像旁总摆着一盘枇杷,常常放得烂了才换掉。 权力这条路,从来都是用血泪铺就的。武则天踩着儿子的尸骨登上了帝位,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可巴州那卷白绫,终究成了她一生都解不开的结——她赢了天下,却永远失去了那个曾攥着她衣袖、怕她变成“吕后”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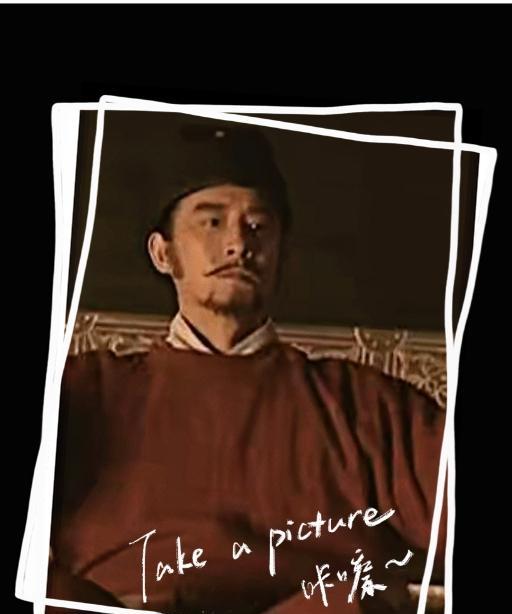




知了
她可杀了不止一个亲生儿子,把一个杀子的毒母写得如此清新脱俗,真服了你
游戏人间
武则天是菩萨,菩萨是不害众生的,她是达摩祖师投胎的,后来又投胎为虚云大师。再往前还投胎为过至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