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前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并把它们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危害的重要任务。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2年,中国刚刚走出战火与贫瘠的泥淖,百废待兴之际,一项关乎全国亿万人健康的特殊任务悄然展开,一份来自苏联的珍贵包裹,在层层防护与专人押送下抵达北京。 包裹里不是外交礼品,也非战略器械,而是一小包重不过20克的植物种子,它们表面平凡如尘土,实则关系着对抗蛔虫病的国家希望。 这批名为“蛔蒿”的种子,被平均分为四份,分送至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的国营农场,各地技术员未接到具体解释,只被反复叮嘱任务的重要性。 那时的中国,蛔虫病流行程度触目惊心,农村饮水条件落后,孩子吃了带虫卵的生菜或泥土便难逃感染,肚子鼓胀、面黄肌瘦几乎成了普遍景象。 传统民间方子效果甚微,进口驱虫药价格昂贵,寻常百姓家望药兴叹,政府急需一种可控、廉价、适合大面积推广的解决方案。 这批源自苏联极寒地带的植物种子正好蕴含α-山道年,一种能麻痹蛔虫神经的有效成分,苏联早在战前便已成功提取其药效,中国的科学家得知其原理后,深知这是改变现状的关键。 试种计划在极度保密的背景下展开,种子被藏于特制容器,途中有公安随行,最终悄无声息地进入各地农场的隔离试验田,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播入土壤,甚至夜里也不敢离开地头一步。 然而北方的春天并不温柔,呼和浩特的温棚在风雪中摇摇欲坠,大同的试验田刚刚发芽便遭遇沙尘,西安农技员望着干蔫的苗子神情黯然,潍坊成为唯一的例外。 沙质土壤疏松,地势略高,加之临时挖设的排水沟渠在关键时刻救了苗根,看守蛔蒿的职工将其称为“一号除虫菊”,无数个夜晚守在田边,只为一茬能成活。 潍坊的蛔蒿长势稳定后,科学家终于开始尝试提取其有效成分,彼时国内尚无精密设备,多靠蒸馏与粗萃技术,过程复杂、提取率低。 苏联提供的少量烘干设备成了宝贵的命脉,保证植物在采收后迅速干燥,不被热浪腐烂,提取出的山道年混入麦芽糖,制成了颜色鲜艳、塔状的小糖块。 这便是后来的宝塔糖,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迅速赢得孩子们的青睐,尽管隐隐带苦,却因其形状可爱、入口甜润,成了众多家庭记忆的一部分。 1958年,潍坊蛔蒿种植面积扩至近九千亩,全国多个省份开始引进提炼工艺,一场旨在根除蛔虫病的公共卫生工程悄然成型,可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并不稳固。 两年后,一场连续40天的阴雨袭击潍坊,大量苗田被水浸透,仓库堆积的成草也因潮湿变质,保管员从自家地窖中挖出三瓶紧急留种,其中两瓶尚有活性,成为蛔蒿种系延续的唯一希望。 随后的几年更加艰难,自然灾害使得蛔蒿田被迫腾让给口粮作物,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撤离,连烘干机的图纸也一并带走,潍坊制药厂只能靠土法复制设备,效率锐减,但勉强维持了宝塔糖的供给。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国产提取系统终于搭建完成,蛔蒿一度恢复种植,只是此时,卫生条件显著提升,儿童蛔虫感染率逐年降低,新型驱虫药逐渐上市并取代老药品,宝塔糖开始走下坡路。 市场对蛔蒿原料的需求不断缩减,仓库开始堆积未提取的草料,更糟的是,种质保存体系尚不健全,未能有效建立蛔蒿的长期保存机制。 1980年代初,又一场大雨淹没潍坊农田,留下的种子失活严重,卫生部门随后发布文件,建议淘汰以山道年为基础的传统驱虫产品,蛔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几十年后,有人想再度复育蛔蒿,却发现全国范围内无一可用种源,这株曾被视作国家秘密的北地草本,最终没有进入植物资源库,也未被完整记录于药典。 它只是悄然在若干人的记忆中闪现过一段,便沉入尘埃,如今城市药房陈列着各种现代驱虫药,无需配糖、无需等待,可在很多人心里,那颗甜中带苦的宝塔糖,仍像一盏孤灯,在记忆深处微微发光。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方志四川《消失的“宝塔糖”:几代人的甜蜜记忆》 四川省情网《蛔蒿引种与宝塔糖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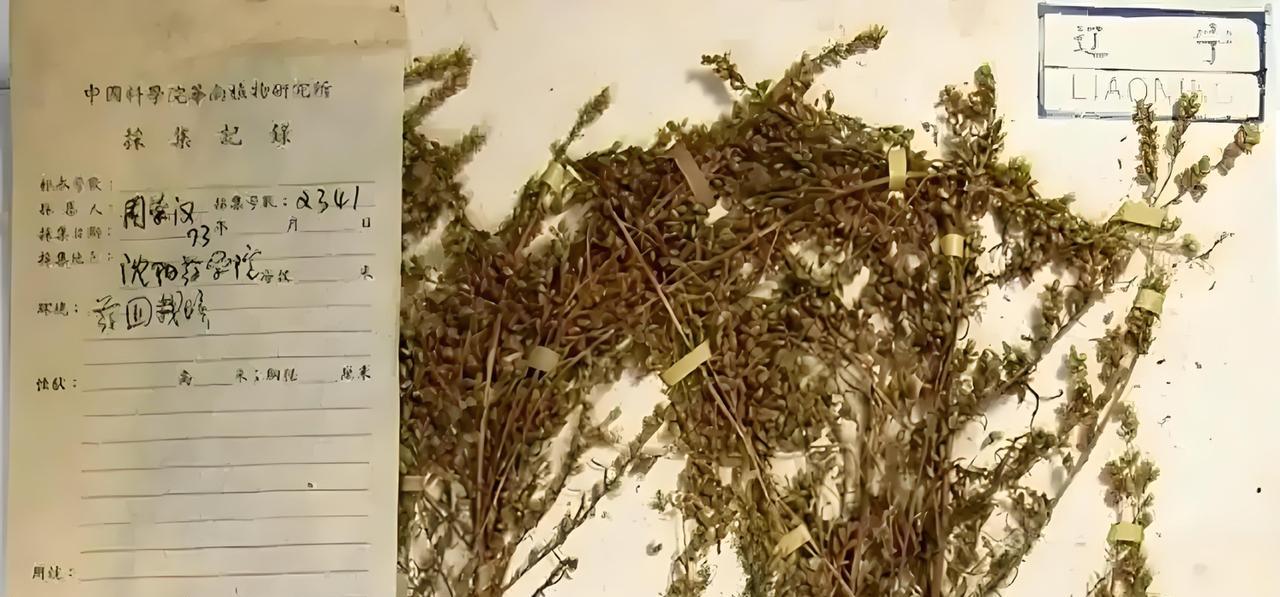

魔鬼的佣人
积积糖,治蛔虫大部分人吃过特效药
用户10xxx69
我们村有个老中医配的驱虫汤比他好多了,除了蛔虫连涤虫都能杀死
刘毅
我小时候吃过
小鸡炖但丁
我爱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