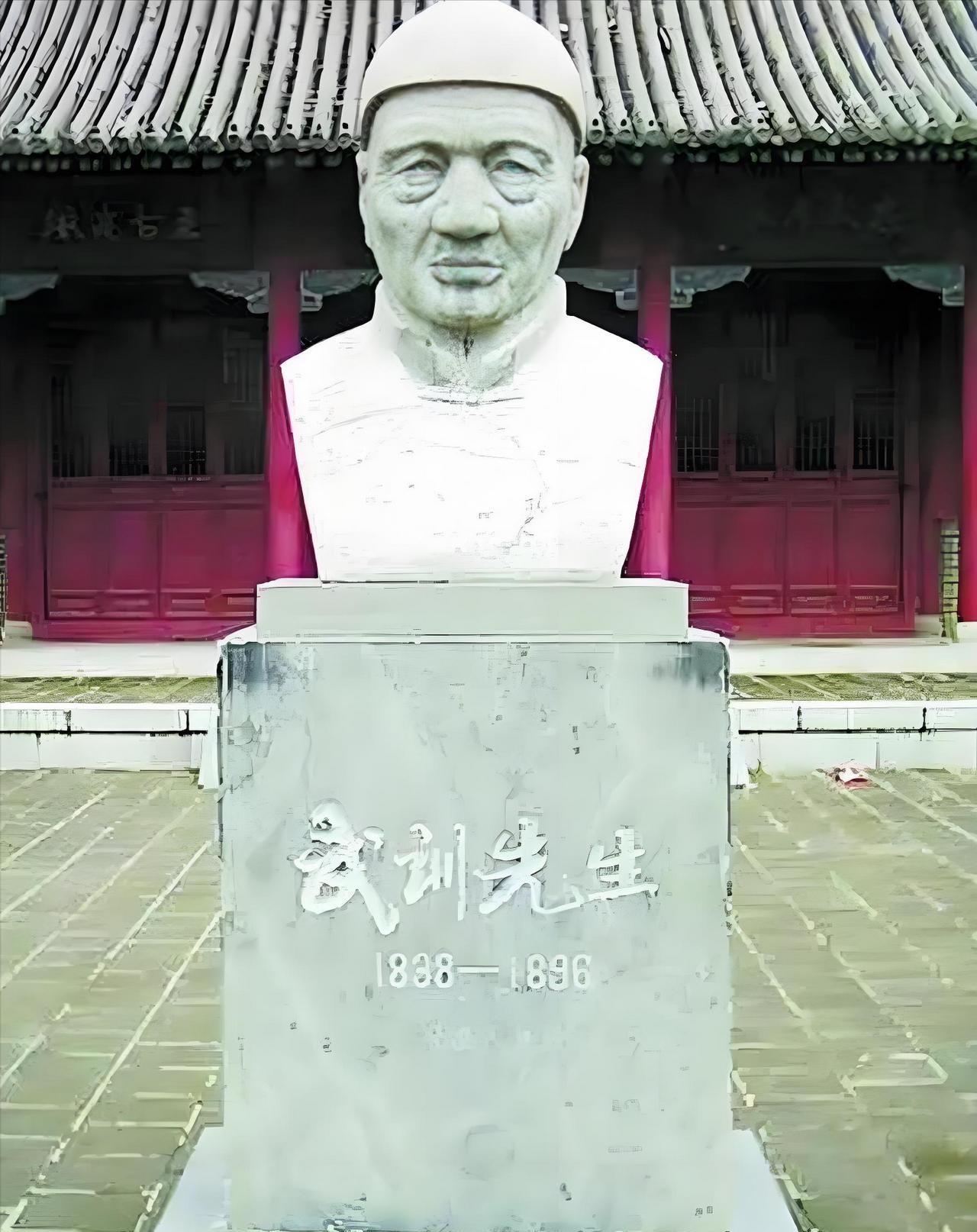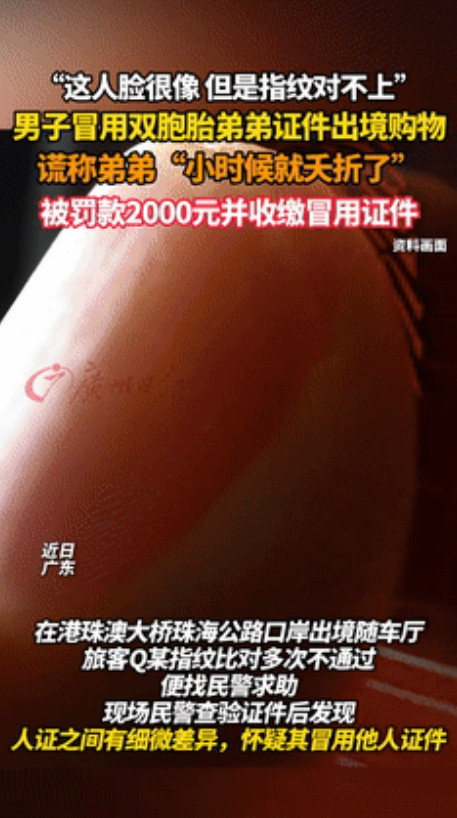1942年,著名女作家沉樱正怀3胎时,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了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1942年的一个夜晚,重庆郊外,一位女子在昏暗灯光下写完一张字条,轻轻放在桌上,字条上的字迹并不潦草,却写得极快,写完,她收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细雨中推门而出,脚步坚定而沉默,这位女子名叫沉樱,此刻她已怀着第三胎,却毫无犹豫地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家,她留给丈夫梁宗岱的,除了那张字条,还有一个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家庭的空屋。 沉樱和梁宗岱的结合,曾是一段被文坛赞誉的才子佳人之恋,沉樱出身书香之家,自小爱读鲁迅、茅盾的作品,年轻时便以犀利敏锐的文字在文坛崭露头角,她擅长描写女性的心理与情感,被称为“新时代的才女”,而梁宗岱则是诗人、翻译家,曾留学法国,思想前卫,文笔优雅,他早年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德国哲人歌德的作品,受到学界高度赞赏。 在那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他们的相识仿佛是命运安排,两人因文学结缘,因思想共鸣而走到一起,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却也充满理想主义的光亮,他们在一起讨论诗歌、翻译作品,也一起为生活打拼,沉樱暂时搁置了写作,把心力放在家庭和两个女儿身上,而梁宗岱则继续在学术和创作的道路上前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裂痕悄然生长,沉樱逐渐发现,丈夫对家庭的关心越来越少,他心中始终存有一段未竟的故事,那是他年轻时在法国的恋情,那位法国女子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替代的位置,而沉樱,尽管才情并茂,却始终被放在了现实角色的位置上,被要求做一个“好妻子”,而非一个独立的作家。 抗战爆发后,生活的重担陡然加剧,他们辗转搬迁,最终落脚重庆,沉樱变卖首饰、精打细算维持家用,心中却仍怀着为这个家庭奋斗的信念,梁宗岱却在这个时期,做出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那一年,他因父亲去世回广西奔丧,途中路过桂林,在那里,他观看了一场粤剧演出,台上的花旦甘少苏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得知她曾被一位军官强行占有,生活悲惨,便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之心,几乎没有太多犹豫,梁宗岱便用家中全部积蓄三万元,将甘少苏赎了出来,这笔钱,是他们一家多年的积蓄,是沉樱为两个孩子未来所作的全部准备。 梁宗岱不仅没有为此事感到愧疚,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救赎”,一种道德上的“义举”,他甚至打算将这位刚刚赎回的女子安置在自家中长期居住,对沉樱而言,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是情感上的巨大背叛,她曾试图冷静地沟通,想要挽回即将崩塌的家庭,但梁宗岱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主义中,听不进任何现实的声音。 当她意识到已经无法说服丈夫,甚至无法让他正视家庭的处境和孩子的未来时,她做出了那个晚上的决定,她没有争吵,没有哀求,只是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直到走出门,她才真正清楚自己其实还怀着一个未出生的孩子。 1943年,沉樱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生下了儿子,她为他取名梁思明,寓意“思而明之”,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微薄的稿费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她拒绝一切来自前夫的帮助,也不愿再与他有任何联系。 几年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年迈的母亲辗转前往台湾,在那里,她靠教书和翻译作品逐渐站稳了脚跟,她的翻译文字优雅清晰,尤其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成为台湾文学界公认的经典版本,沉樱用自己的才华和坚持,一点一滴地重建了人生的尊严。 而梁宗岱,继续留在大陆,从事文学研究,他与甘少苏短暂成婚,但这段婚姻并未带来他想象中的温情与理解,甘少苏文化水平有限,无法理解梁宗岱的精神世界,两人始终未能真正契合,晚年的梁宗岱开始尝试修复与子女的关系,尤其是他从未见过的小儿子梁思明,他辗转通过朋友试图联系沉樱,请求能见上一面。 1972年,沉樱在美国收到了这封请求的信,她没有拒绝回信,但信中语气坚定冷静,她坦言,梁宗岱在文学上曾给予她启发,但在情感上,他们是“怨偶”,她不愿再见,也不希望再回忆,信的结尾,她写下:“往事已成灰烬,何必再掀风波,” 1983年,梁宗岱在广州去世,终年80岁,次年,沉樱得知消息,只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又回到翻译工作中,她没有公开表示哀悼,也没有安排孩子们前去吊唁,她只是继续生活,继续创作。 1988年,沉樱在美国病逝,临终前,她将一本雪莱诗集交给女儿,那是梁宗岱早年送她的礼物,她轻声说,这是孩子们父亲唯一值得纪念的东西,没有怨恨,也没有宽恕,只有一份超越情感的冷静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