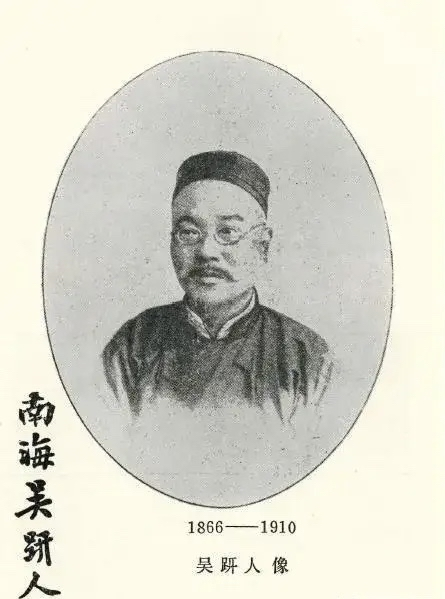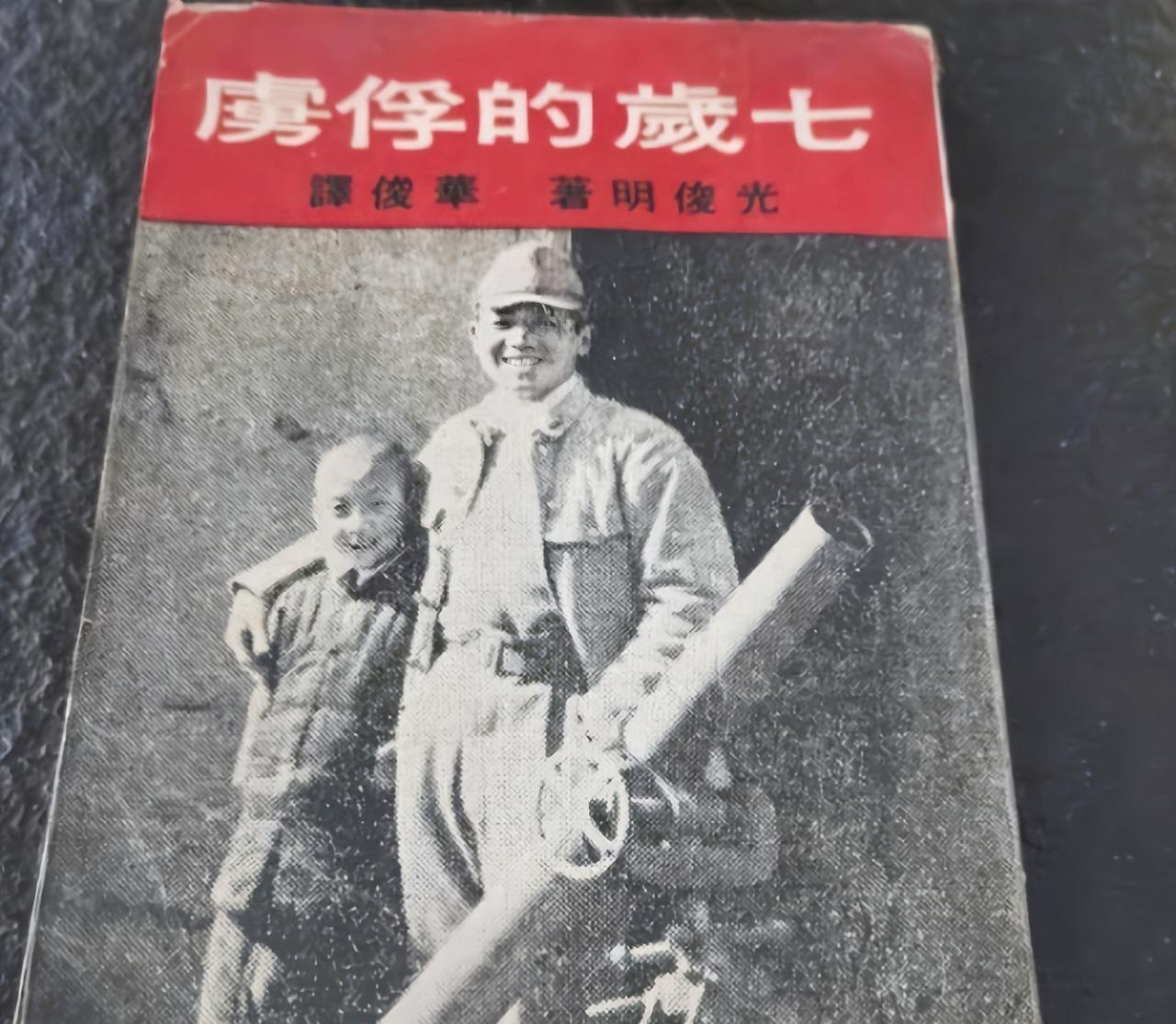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的一个小渔村里,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排行老七。父亲是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收入微薄,仅够糊口。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妇,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尽管生活清贫,但黄旭华从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常常借来哥哥们用过的书本,废寝忘食地阅读。然而,村里穷,没有像样的学校。为了上学,他不得不步行数里,到邻村去读私塾。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波及到汕尾。为了躲避炮火,黄旭华随家人逃难,辗转于揭西、梅县、桂林等地。那时,他们有时躲在防空洞里,有时躲在山洞里,有时甚至在田间露宿。 尽管如此,黄旭华的求学之心从未泯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会想方设法去上学。有一次,日军的轰炸机突然出现,同学们四散逃命。而黄旭华却趁乱抢救了几本来不及带走的课本。 战争的残酷,让黄旭华幼小的心灵饱受创伤。他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也亲身经历颠沛流离的苦难。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渐渐萌发:我长大了,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再受苦了。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20岁的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交通大学,学习造船。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造船业更是几乎空白。 但是,黄旭华却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要真正独立自主,必须发展海上力量。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制海权。而海军的核心装备,莫过于潜艇。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建造潜艇。 在大学期间,黄旭华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业余时间,他还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黄旭华被分配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工作。在那里,他参与了中国第一艘国产潜艇的设计和建造。虽然那只是常规动力潜艇,但黄旭华却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身核潜艇事业的决心。 1958年,一纸调令,把黄旭华从上海召到北京。召见他的领导神秘兮兮,语焉不详。 “我明白。”黄旭华打断领导的话,“保密工作,我义不容辞。”就这样,年仅34岁的黄旭华,走进了中国核潜艇研究的大门。从此,他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亲友也无法得知他的下落。直到30年后,他的事迹才首次披露。 刚开始研制核潜艇时,中国基本上是一穷二白。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一切只能从零开始。黄旭华和战友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海岛上,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岛上连淡水都没有,只能用海水洗澡。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从基础理论学起,夜以继日地工作。黄旭华常常通宵达旦,靠着两包烟和一壶浓茶,计算到天亮。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甚至想方设法搞到了美国核潜艇的儿童模型,小心翼翼地拆开,揣摩里面的构造。 就在黄旭华埋头苦干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1962年,他的父亲病逝。然而,由于事关国家机密,黄旭华既不能回家奔丧,也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 望着大海的方向,黄旭华泪如雨下。他知道,自己成了“逆子”,愧对父母。但是,他更清楚,肩上的重任不容有失。唯有将悲痛化作力量,才对得起父亲的养育之恩。 就这样,整整12年过去了。1970年12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终于建成下水。当五星红旗在潜艇塔顶升起的那一刻,黄旭华热泪盈眶。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打击,都在这一刻化为欣慰与自豪。 “总设计师,我们成功了!”同事们抱头痛哭。是啊,他们用青春和汗水铸就了共和国的新盾,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新篇章。那一刻,没有军功章,没有鲜花掌声。但黄旭华心里明白,此生无悔入华夏。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止步。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次次刷新核潜艇的航速、深度和航程纪录。也只有在偶尔路过家乡时,黄旭华才能匆匆去看望年迈的母亲。 直到1988年,64岁的黄旭华才有机会长时间回家。当他出现在阔别30年的家门口时,老母亲一度难以相认。摸着儿子布满皱纹的脸,老人家喜极而泣:“儿啊,你总算回来了。妈妈好想你啊。” 从一线退下来后,黄旭华并没有闲着。他成立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培养新一代核潜艇人才。闲暇时,他还去学校和社区做科普讲座,给孩子们讲核潜艇的故事,点燃他们热爱科学、报效祖国的梦想。 采访中,一位记者问黄旭华:“您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值吗?”黄旭华想了想,为了国家,他牺牲了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可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光荣而艰难的道路。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深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