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80岁的张先生一把将18岁的小妾搂入怀中,说了几句柔情蜜语的肉麻话,接着便迫不及待的洞房花烛夜,几年后18岁小妾生下4个孩子。
八十岁的张老爷从人牙子手里接过玉儿的卖身契时,日光正照着姑娘后颈的绒毛。
玉儿才刚满十八岁,眼角那颗泪痣让张老爷攥紧了手里的紫檀拐杖。
街坊们都伸长脖子看稀奇,这年岁能当人太爷爷的老爷子,偏要买个水葱似的姑娘回家当丫鬟。
张宅后院晾着十几房姨太太的绸缎衣裳,风吹过都带着脂粉香。
老管家捧着账本直叹气,老爷年轻时走南闯北挣下的家业,满院女人却连个摔盆的儿郎都没有。
张老爷常对着祠堂叹气,早年被棒打鸳鸯的初恋也有颗同样的泪痣,二十岁私奔被抓回去的姑娘,早化作城外乱葬岗的白骨了。
玉儿在厨房帮着剥豆子的时候,老爷总拄着拐棍在月洞门外晃悠。
厨娘们发现这丫头总能吃上桂花糖蒸栗粉糕,水缸永远轮不到她挑。
有次灶上烫了玉儿的手背,第二天药房里最好的獾油膏就搁在了窗台上。
那年重阳节的老黄历写着忌出行,醉醺醺的张老爷撞翻了描金食盒。
醒酒汤的白气蒙了玉儿的眉眼,老寿星的手指刚要碰着那颗泪痣,突然像被火燎似的缩回去。
三天后媒婆抱着锦缎进偏房时,丫头们看见玉儿绞烂了条绣着鸳鸯的帕子。
迎亲唢呐吹得震天响的时候,棺材铺老板都挤在席面上啃蹄髈。
洞房里的龙凤烛爆了灯花,新娘子攥着衣角往床里缩,老头儿捏了捏她冰凉的手指头。
"嫌我老棺材瓤子?"红盖头下传出声蚊子哼:"横竖都是熬日子。"
谁都没料想这枯树逢了春,玉儿过门四年竟添了三个小子一个闺女。
抓周礼把传家玉佩都抓裂了,八十九岁的老爷子笑得假牙直打颤。
咽气前还攥着小儿子的虎头鞋念叨:"到底没白活......"
灵堂里穿孝服的儿女排成串,披麻戴孝的玉儿脸上挂着泪珠子。
守夜的老嬷嬷看见她把供桌上的白面馒头掰成两半,塞给躲在影壁后头的小乞丐。
七七过后张宅换了匾额,门房里多了十几个学打算盘的毛头小子。
当年笑老牛啃嫩草的人家,如今常被主母派管家送去春耕的粮种。
灶房每天蒸八大笼杂粮馍,专收留被插草标的半大孩子。
有赶考的秀才讨水喝,看见门廊下挂的对联写着"但行善举莫问前程"。
这出戏文里的苦命女子后来当了祖母,去年清明有后生拍下她的近况。
九十五岁的老太太坐藤椅上择豆角,玄孙辈的娃娃滚了满院琉璃弹珠。
张家老宅现在是县里民俗展示馆,账房先生当年用过的算盘锁在玻璃柜里。
有记者拍过正屋板壁上挂的旧年画,发黄的杨柳青年画旁钉着张扶贫基金会的奖状。
抖音上疯传过小孙女直播带货的短视频,背景里总晃着老太太纳鞋底的背影。
祖谱上新添了铅笔写的注脚——"五代孙张念慈某年考入师范学院"。
老话说枯木底下好乘凉,张家廊檐如今晾着福利院新浆洗的棉被。
灶膛天天烧着大锅饭,过路的总能闻见蒸馍的甜香气。

![同事问:“你带饭是为了省钱吗?”怎么回?[汗]](http://image.uczzd.cn/396130961342391513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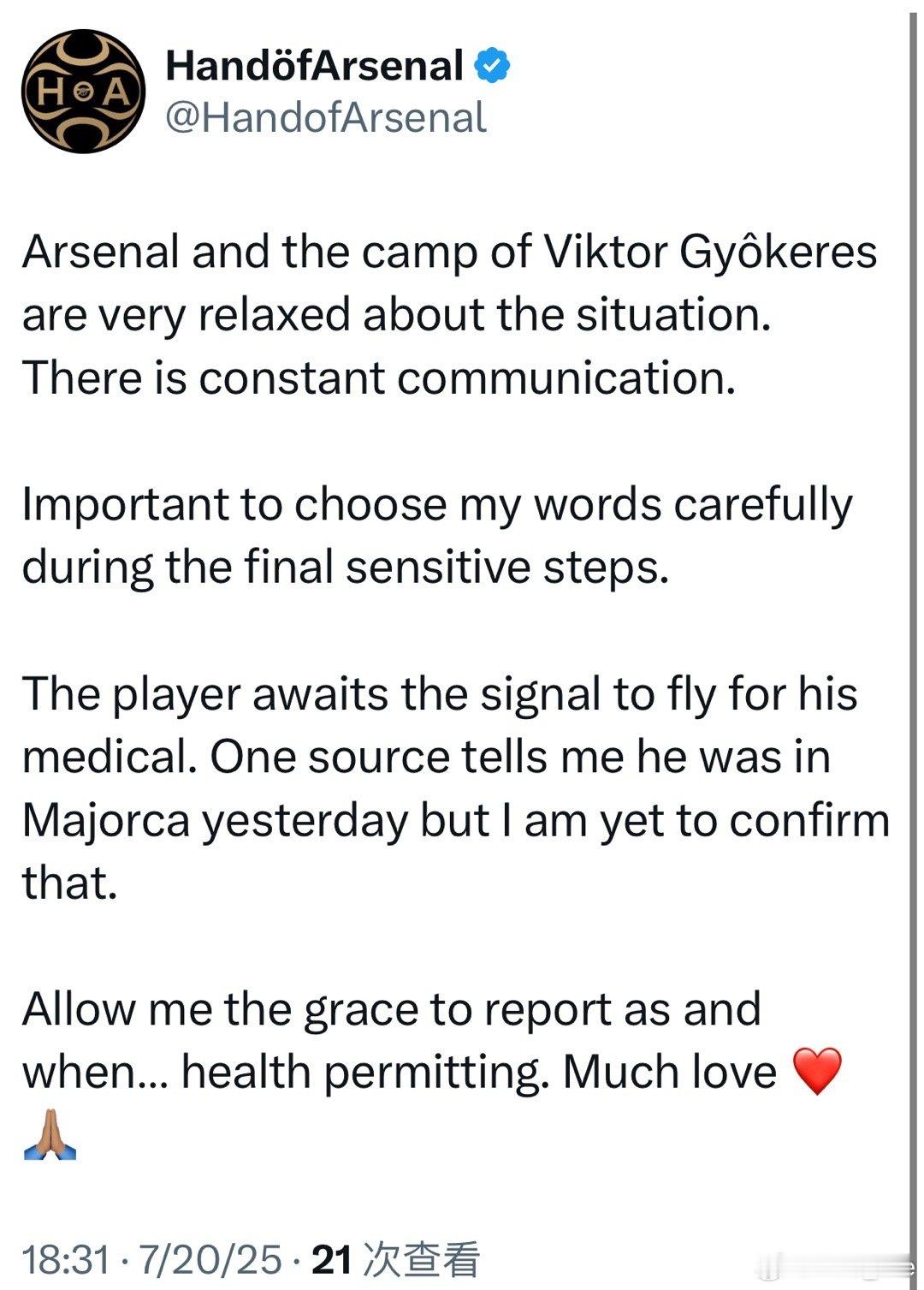


![F35也起飞后就掉零件了[捂脸哭]美国军工制造越来越拉了[doge]图源网络烽火问](http://image.uczzd.cn/122371691025049520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