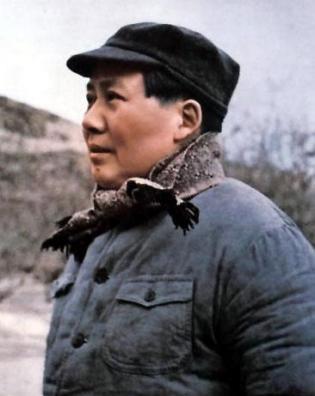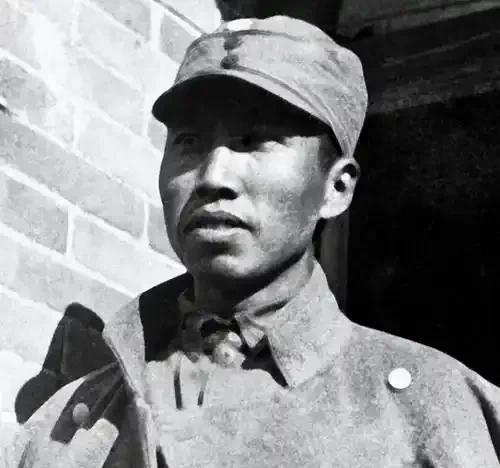1948年深秋,沈阳城迎来解放之际,郑洞国之子匆匆赶到解放军指挥部,声称要为父亲操办后事。在场官兵闻言不禁莞尔,随手递过一份报纸道:"郑将军早就在哈尔滨了,还是肖劲光司令亲自接的风,你们蒋总统这谎话编得可不太高明啊!" 【消息源自:《长春围城:1948年郑洞国的生死抉择》2023-08-15 历史研究月刊】 郑洞国把家书折了三折塞进胸前的口袋,纸角硌得肋骨生疼。长春十月的寒风从指挥部漏风的窗户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作战地图吹得哗啦作响。勤务兵刚端来的高粱粥已经结了一层冰碴子,他盯着粥碗里自己扭曲的倒影,突然想起三个月前妻子陈碧莲在上海国际饭店给他庆生时,水晶吊灯在香槟杯里折射出的碎光。 "司令,六十军又闹饷了。"参谋长踩着满地烟头进来,军靴上还沾着前天饿死在街头的难民血迹,"兄弟们说...说再不发粮,明天就开始吃皮带。"郑洞国没接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家书的火漆印。那上面还留着陈碧莲的香水味,混合着长春城里腐烂的尸臭钻进鼻腔,熏得他眼眶发酸。 城外解放军的广播车正在循环播放肖劲光的劝降信,女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音混着炒豆般的机枪声飘进来:"...长春父老正在易子而食,郑将军当真要做千古罪人?"作战参谋突然冲进来,差点撞翻桌上的沙盘:"不好了!暂编五十三师把中央银行粮库抢了!"郑洞国猛地站起来,钢盔撞歪了电灯,晃动的光影里他看见自己颤抖的右手正按在配枪上。 "老郑,别硬撑了。"新七军军长李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这个黄埔三期生摘了领章扔在沙盘上,"今早东门哨兵报告...有人在煮婴儿。"他说最后两个字时突然破了音,像把钝刀子划在玻璃上。郑洞国摸出怀表看了眼,表盖内侧嵌着的全家福上,穿着洋装的陈碧莲正抱着留声机朝他笑。 10月21日凌晨三点,郑洞国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签完投诚书时,钢笔突然漏墨,一大团蓝黑色污渍在纸上洇开,像长春上空终年不散的阴云。他摘下中正剑递给解放军联络员时,突然听见楼上传来《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声——某个军官正用最后的柴油发电,在末日来临前跳最后一支舞。 三个月后,郑安腾在四平街的解放军指挥部里攥着哈尔滨日报浑身发抖。报纸头版登着他父亲和肖劲光的合影,标题赫然写着《郑洞国将军参加革命工作》。而此刻他西装内袋里还装着国民政府颁发的"荣字第九号"烈士证明书,烫金国徽硌得心口生疼。"这...这不可能!"年轻人把报纸拍在桌上,"蒋委员长明明说..."对面的解放军干部推来一碟花生米:"尝尝吧,你父亲现在顿顿能吃上这个。" 1952年春天,当郑洞国在北京收到陈碧莲的离婚协议书时,正坐在政务院分配的苏联式公寓里听广播。播音员欢快的声音在念"成渝铁路通车"的喜讯,窗外的白杨树抽出新芽。他盯着协议书上"因政治立场不合"那行字看了很久,突然发现墨迹有些化开——原来是房顶的积雪融化了,水珠正滴滴答答落在信纸上。 1983年那个雪夜,七十八岁的郑洞国打开门时,看见陈碧莲穿着四十年前那件貂皮大衣站在楼道里。老人驼背的身影被声控灯拉得老长,像一截烧焦的树桩。"碧...碧莲?"郑洞国手里的降压药撒了一地。老太太从手提包里摸出张发黄的唱片,封套上《夜来香》三个字已经褪了色:"当年从长春逃出来就带了这张片子...现在放给你听好不好?"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的追悼会上没有播放哀乐。殡仪馆的老式留声机吱呀转动,周璇甜美的嗓音穿透花圈上的挽带:"那南风吹来清凉..."陈碧莲坐在轮椅上数着吊唁人群里的将星——有当年长春围城的解放军,也有起义的国军旧部。她颤巍巍地从轮椅下摸出瓶上海牌雪花膏,轻轻抹在遗像的相框上:"洞国啊,现在总算...不挨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