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娶续弦,岳父同情他:“我三女儿14岁,酷似她姐,你娶她吧?”马一浮拒绝:“亡妻地位无人能替,无心再娶。” “仪儿,说好要白头偕老的啊!”看着即将下葬的棺椁,马一浮突然抱着妻子的绣花鞋大哭起来。马一浮一代国学大师,19岁丧妻,他用了八十年诠释“曾经沧海难为水”,对妻子的独一份深情。 1898年,16岁的马一浮以县试榜首的身份,被浙江巨绅汤寿潜“榜下捉婿”。新婚夜,当盖头掀起的刹那,他被汤仪国色风华的容貌所惊艳,后来折服在这个大家闺秀的才华下。 两人谈诗论道直到天蒙蒙亮,汤仪指着窗外的明月:“浮郎日后必成大器,只是要记得...”话未说完,马一浮已经将她的手按在胸口上:“我马一浮此生,唯愿与仪儿琴瑟和鸣”。 这段“榜下捉婿”的佳话,很快传遍杭州城。汤仪虽出身望族,却甘愿陪丈夫住在陋巷。马一浮游学日本时,她独自操持家务,每月初七必去楼外楼点一道龙井虾仁,那是丈夫最爱吃的菜。 只可惜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1901年,汤仪生下孩子后感染风寒。临终前,她攥着丈夫的手:“浮郎,替我去看...”话音未落,绣着青竹的袖口垂落。“夫人早咳血半月了,死活不让说”,贴身侍女抽噎道。 马一浮疯了般冲到西湖边,将妻子的绣鞋浸入冰水中。从此他再不穿丝履,只着粗麻布鞋。西泠印社的吴昌硕得知噩耗,刻刀一抖,“仁”字刻成“二”,长叹一声:“马老弟这是要学尾生抱柱啊!” 岳父汤寿潜不忍见女婿消沉,提议将14岁的三女儿许配给他:“这孩子生得最像仪儿。”马一浮扑通跪地:“泰山之恩,浮铭记于心。但仪儿在我心中,无人能替”。 消息传开,杭州文人圈炸了锅。有人赞他守节如苏武,有人讥他迂腐如冬烘。马一浮却将妻子的妆奁改成书箱,刻下“不须更觅封侯印,一箧珠玑是嫁时”,从此闭门谢客,潜心治学。 之后三十年,马一浮独自一人住在陋巷,案机上永远摆着亡妻的画像。每月初七,他必去楼外楼独坐,对着空碗筷自斟自饮。 清明时节,他抱着酒壶在孤山脚下坐到天明,对着湖水呢喃:“仪儿,雷峰塔倒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 1939年,蒋介石邀他出山办学,他提出“三不原则”:不涉政、不领俸禄、不收权贵子弟。在复性书院,他写下“主敬、穷理、博文、笃行”八字学规,却在讲学时屡屡哽咽:“学问之道,贵在有个‘情’字。” 学生们发现,先生书房的青瓷瓶里,始终插着一支玉簪。瓶底刻着“永以为好”,那是汤仪出嫁前亲手刻的。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会照见簪头的并蒂莲,折射出七彩光晕。 1967年,86岁的马一浮病重垂危。他颤巍巍摸出一块褪色的绣帕,那是汤仪十六岁时练手的“杰作”,歪歪扭扭绣着“浮”字。临终前,他叮嘱学生将诗稿与绣帕一同焚烧:“留得一分寒骨在,不妨持赠素心人。” 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金刚经》扉页上密密麻麻写满小字:“仪儿,西湖水暖了,我这就来寻你。”书桌抽屉里,整齐码放着67年的日记,每一页都有泪痕,篇篇写着“仪儿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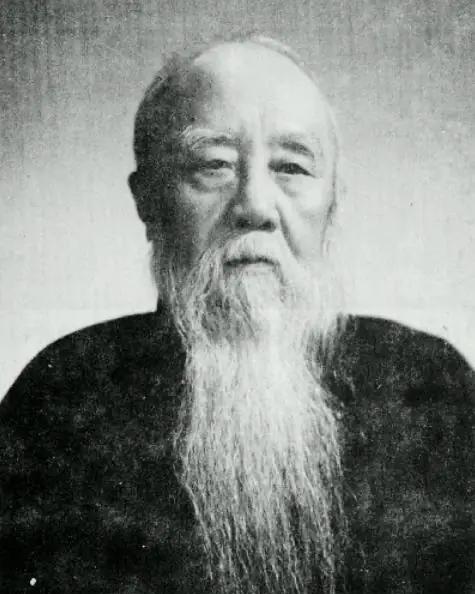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