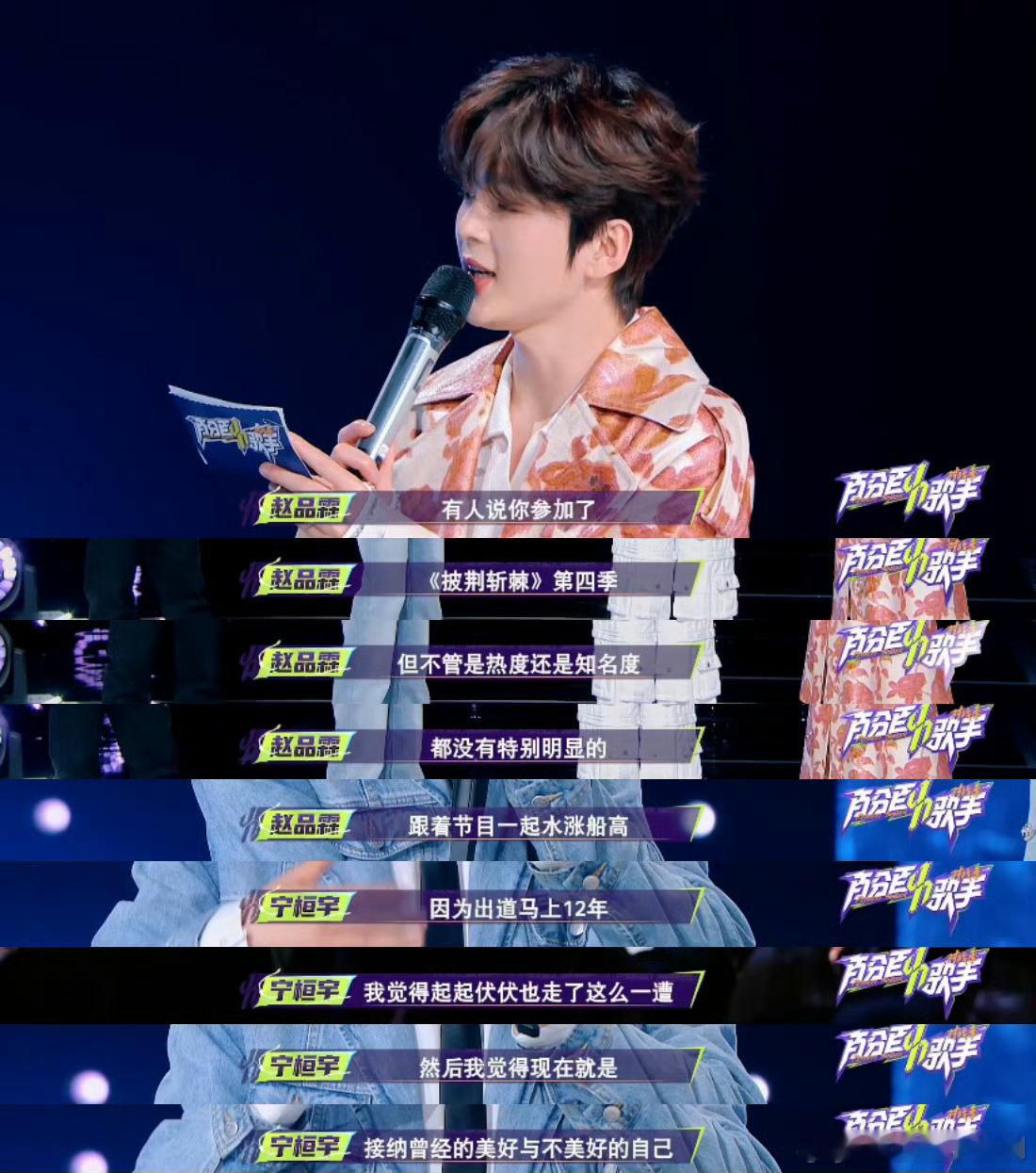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1942年五月末的江津县城,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草药苦涩的味道,五十出头的潘兰珍守在病榻前,看着丈夫蜡黄的面孔。 这位曾经在历史洪流中掀起惊涛骇浪的人物,如今连翻身都要人搀扶。外头蝉鸣声透过窗纸传进来,混着中药罐子咕嘟咕嘟的响动,让屋里显得愈发寂静。 陈独秀躺在竹席上,手指微微动了动,潘兰珍赶忙俯身过去,听见丈夫用气声断断续续交代后事。 教育部每月寄来的钱款得原封不动退回去,这是老头子最后的倔强。 潘兰珍抹了把眼泪,想起十年前在上海弄堂初遇时的情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自称王先生的教书匠,就是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的通缉犯。 时间倒回1930年的上海闸北,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潘兰珍拎着竹篮去老虎灶打热水。她租住的亭子间隔壁新搬来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总爱在弄堂口买粢饭团当早饭。 有次她晾的衣裳被风吹落,还是这位王先生帮忙捡起来的,街坊们都说新邻居是个落魄文人,靠给人代写书信糊口。 谁也没想到这个成天泡在茶馆看报纸的老头,竟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新青年》创办人。 潘兰珍记得特别清楚,那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她端着自家包的荠菜饺子去隔壁,正撞见两个便衣在翻箱倒柜。 王先生被反绑在藤椅上,看见她进来急得直瞪眼,后来报纸上登出"共党要犯陈独秀落网"的消息,她才恍然大悟。这个平时教她识字念诗的先生,竟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的"匪首"。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探视日,潘兰珍总是天不亮就起身,她背着小包袱挤上闷罐车,怀里揣着新抄的《楚辞》。 看守们起初当她是普通家属,后来发现这女人风雨无阻地送书送药,连典狱长都记住了这个操着南通口音的小媳妇。 陈独秀在牢里反而胖了些,他把囚室当书房,写起文章来能熬通宵。潘兰珍不识字,但知道丈夫在写要紧东西,总把省下的菜钱换成稿纸。 1937年夏天,外头传来卢沟桥打仗的消息,陈独秀出狱时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杖。两口子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最后在江津城外石墙院安顿下来。 三儿子陈松年拖家带口来投奔,老屋里挤得转不开身,潘兰珍既要照顾瞎眼的婆婆,又要给全家人缝补浆洗。 最难的时候,她偷偷去码头扛过麻包,肩膀磨出血也不敢让丈夫知道。 蒋介石那边始终没死心,教育部的汇款单每月准时寄到,附信里总说"仲甫先生学界泰斗"。陈独秀把这些信封原样退回,转头却要喝掺了糠皮的稀粥。 有回老部下带着整箱现大洋上门,被他举着扫帚赶出院子。 潘兰珍躲在灶间抹眼泪,她明白丈夫宁肯饿死也不吃"官家饭"——两个儿子都死在国民党手里,这是扎在他心头的刺。 最后那半年,陈独秀的血压高得吓人,听说蚕豆能降血压,他拖着病体去后山摘野蚕豆。哪晓得前夜下过雨,半筐蚕豆捂在竹篓里发了霉。 吃完上吐下泻,本就虚弱的身子彻底垮了,临终前那天清晨,他忽然精神起来,非要潘兰珍搀着到院子里晒太阳。 五月的阳光暖烘烘的,照在褪色的蓝布长衫上。他眯着眼看屋檐下的蜘蛛网,嘴里念叨着老家安庆的油煎毛豆腐。 江津县卫生院的大夫来打强心针时,陈独秀已经说不出话,潘兰珍攥着他枯瘦的手,感觉那点体温渐渐凉下去。 按照生前嘱咐,她没要政府给的抚恤金,把教育部寄的钱全退了回去。街坊们都说潘兰珍傻,守着几箱子书稿能顶什么用。 可他们不知道,那些年探监时藏在饭盒底的诗稿,早被陈独秀改成了《小学识字课本》。这是老头子留给她的念想,比金山银山都金贵。 后来潘兰珍给人当过保姆,在纱厂干过零活,有年冬天特别冷,她把丈夫的旧棉袍拆了改小袄。 从夹层里掉出张发黄的纸片,上头是陈独秀的笔迹:"兰珍伴我于患难,此生无以为报"。 她对着油灯看了半宿,第二天照常去江边洗衣服,搓衣板在青石上磨得发亮,就像这些年被生活磋磨的心气。 直到1953年病逝,她始终守着石墙院的老屋,还有那几箱从不示人的手稿。 如今江津档案馆里还存着当年的汇款单存根,褪色的蓝墨水写着"陈仲甫先生亲启"。 潘兰珍按的手印清晰可辨,旁边备注栏工工整整写着"拒收"二字。这些泛黄的纸片和石墙院里疯长的野蚕豆,成了那段往事最沉默的见证。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风雨相伴十二年——陈独秀与潘兰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