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光”。
秦朝之光是“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虽二世而亡,但开启了封建文明之光。
汉朝之光是在秦制基础上,进一步深耕细作,把汉人群体推向了“民族”的高度。
唐朝之光当然是高度开放和兼容,唐太宗提出“华夷一家”理念,缔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四海同风”超级帝国。
宋朝更像是一个阉割版的唐朝,“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刑不上大夫”,武功弱了一点,但把文治推向了封建时代之巅。
那么,明朝之光是什么?
一旦说到这个话题,想必有些人就会“颅内嗨”了,进入了“明吹”擅长的赛道。什么“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及永乐大典、明大诰等等。
这些算“光”吗?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过一句话: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诚如此言。像明朝这种皇权专制达到顶尖的王朝,真正的王朝之光,是那些敢于对抗皇权专制的猛人。
这些猛人,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从道不从君”。
(1385年)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举,一位来自陕西同州府的进士脱颖而出,此人叫王朴。考中进士后,就被安排进都察院当了一名御史。
按照科举惯例,考中进士要么去翰林院深造,要么直接分配上岗,但都有三年考核期,相当于现在的试用期。
用官场思维来看待这件事,刚考上编制,进了新单位,做人得圆滑小白一些,安排你干啥就干啥,多干活,少表态。
可王朴天生一个愣头青儿。刚入职就对朝议各种表态,而且全是奔着朱元璋去的。
一开始,朱元璋还觉得青年勇气可嘉。不到三个月,朱元璋就烦了,直接把他御史一职给撸了。
撸了王朴后,朱元璋觉得有点不太体面,又让吏部给他官复原职。
做人耿直是一个好事儿,可得看对谁耿直,如何耿直。王朴的耿直,有点一根筋。
对一般人来说,从哪里跌倒就得从哪里站起来。王朴不同,他属于从哪里跌倒,就得把这块地给刨平了。
面对朱元璋的第一次“敲打”,王朴非但没有任何警觉性,并从中吸取教训,依旧拿命进谏。
朱元璋是市井出身,玩心眼绝对是祖师爷,但你若拿“之乎者也”跟他硬刚,他铁定原形毕露。
有一天朝会上,君臣二人又杠上了。这一回,是真杠爆了。朱元璋很生气,喊来锦衣卫,扬言将王朴拖到菜市口一刀砍了。
王朴被当场扒了官服,五花大绑带走。群臣一看,青年没错,御史本来就是抬杠的。于是,集体给王朴说情,朱元璋借坡下驴,让人把王朴从菜市口拖了回来。
带回王朴就一个目的,让他认错,承认自己“目无君上”,犯了欺君之罪,如果从此改了这个毛病,还会继续留用他。
王朴一听,直接当众撂下一句话“愿速死”。三个字如同一口千年老痰,啐到了朱元璋脸上。
没有意外。下一秒,王朴下线。
从朝堂往菜市口拖的时候,刚好路过翰林史馆,当时的翰林院一哥是“刘三吾”。王朴高声喊道:大学士刘三吾在哪,我给你提供素材来了,一定要记下今天这一笔,洪武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

王朴虽是一个无名小官,但创造了从入职到被杀的纪录。试用期内,因耿直而被砍的大臣,王朴算是二十四史独一份了。
历史没有王朴的过多记载。像他这种小卡拉米在当时被砍,不值一提。比他官大被砍的,大有人在,正史根本记不过来。
砍了就砍了。可朱元璋耍了一个小聪明,在编写明典时,专门把王朴给写上了,还给王朴定了一个“诽谤”罪名。
朱元璋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件事就被后人给扒了出来。
王朴性格上可能存在言语过激,你朱元璋想杀就杀了呗,怎么还给人扣上一顶“诽谤”的帽子。
“诽谤”绝对是对一个耿直御史的政治和人格侮辱。
王朴绝不是洪武历史上因耿直被杀的大臣。早在王朴被杀前九年,就有一位前辈因同样的事儿罹难。
这个人,叫叶伯巨,是山西平遥县训导,相当于县教体局副局长。此人学富五车,研究天文星象造诣极高。
(1376年)洪武九年闰九月初九,钦天监观察到星象异常。消息一出,举国轰动。古人认为,出现这种事儿,要么是皇帝失德,要么是天有大乱。
朱元璋也慌了,诏告天下寻找高人指点。
叶伯巨自告奋勇给朱元璋写了一份《奉召陈言疏》,主题就三点:分封太侈 ,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朱元璋接到奏疏后,当场炸毛。让平遥县赶紧把叶伯巨绑来,这厮离间老朱家骨肉,我要拿弓箭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就这样领了盒饭。

两则明初小人物的故事,折射出那个时代士大夫的艰难与不幸。试问,什么样的脊梁骨能够经得起皇权的爆锤?
但我从中,似乎读到了明代文人无风骨的原因。
人创造环境,环境同样创造人。
对居于食物链上层的群体来说,他们的无耻不是最大的恶,滋生塑造他们无耻的土壤才是。任何朝代都无法完全灭绝无耻的存在,但当一个朝代“无耻”成为主流价值的时候,就应该被重视,被审视。
人心肉长,混成这副德行了,甲申事变又如何要求他们为明殉国呢?
一定程度上讲,明朝各种无解困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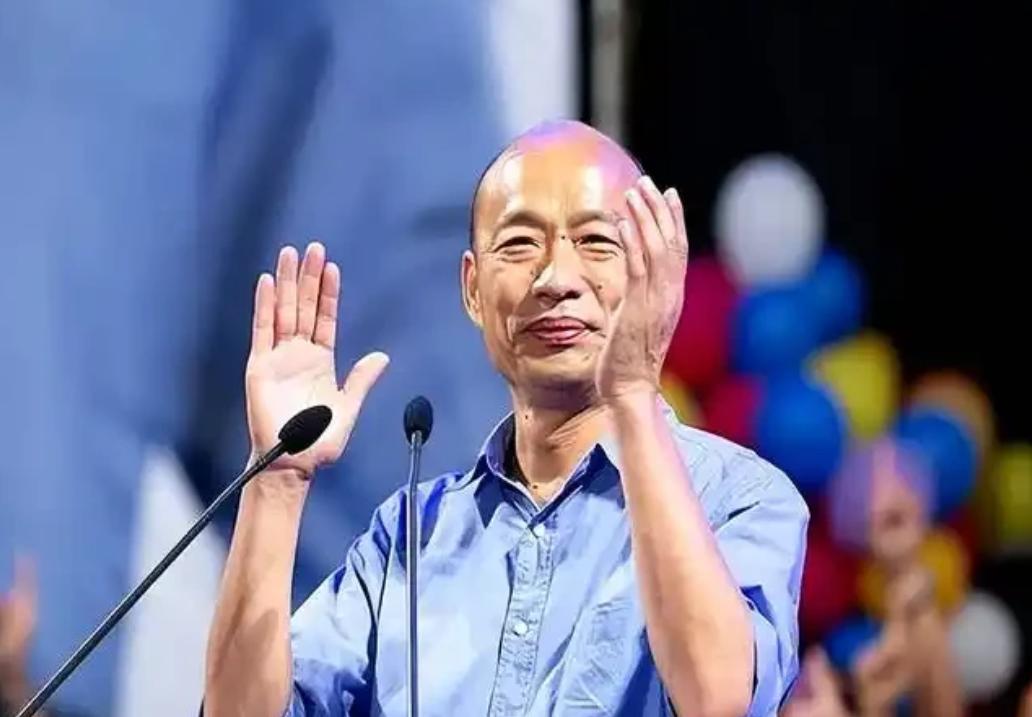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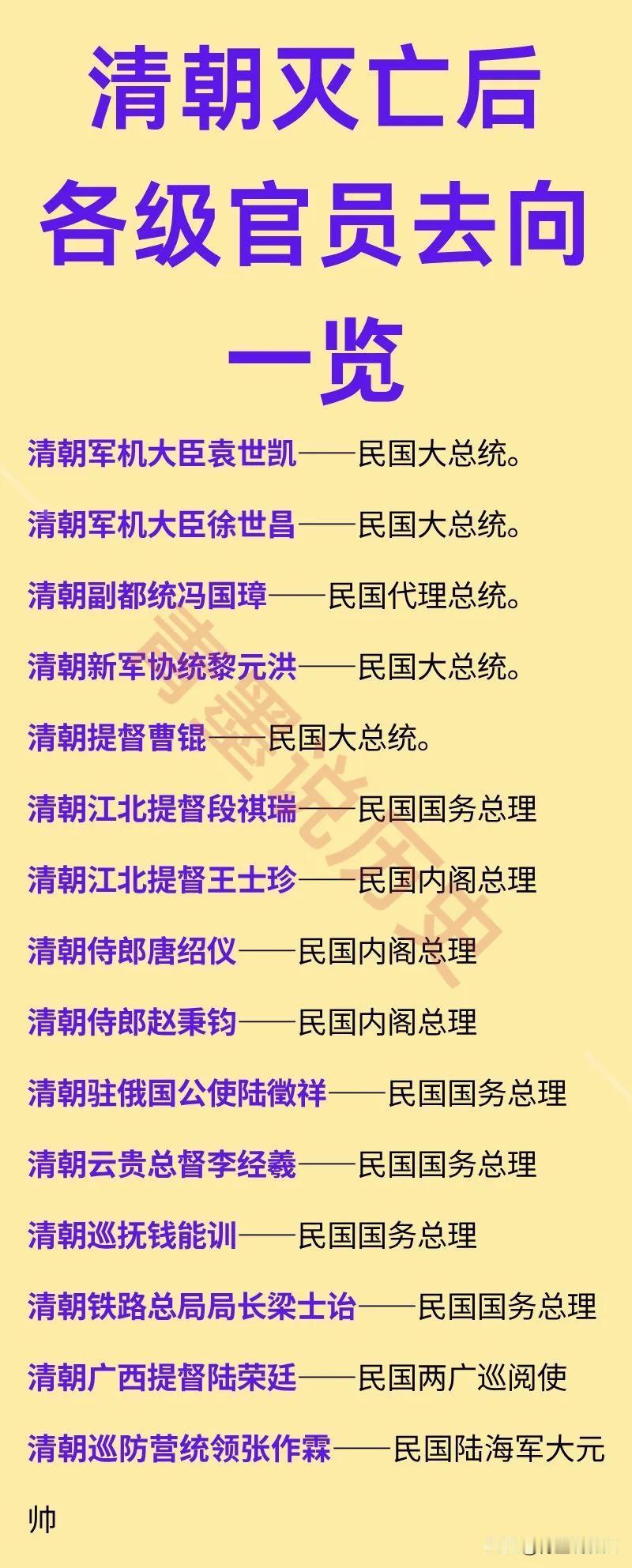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