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水泽孕出江苏饮食的温软底色,汉魏时“菰羹鲈脍”已见风华,
《齐民要术》记“菰菜羹”,正是淮扬菜最初的模样,
那时人便懂顺水土取鲜,不糟践一份食材。
唐宋文人把雅趣炖进烟火里,陆游写“鲈肥菰脆调羹美”,道的就是苏地家常味;
文思豆腐切得细如发丝,刀工里藏的不只是手艺,是江南人对日子的慢琢磨。
明清漕运让扬州成了食事枢纽,盐商宴催着菜式精进。
如今端午裹五芳斋粽、中秋咬长发月饼,
老味道里没散的,是江苏人代代传的实在与讲究。

北宋时便是皇家贡品,秦观曾寄醉蟹给苏轼,
附诗“团脐紫蟹脂填腹”,千年前的风雅仍飘着酒香。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背青肚亮,爪带金毛,蒸熟后膏红似火,肉嫩如玉,
入口鲜甜中带点湖腥气,老饕说“腥气越重,蟹越鲜”。
当地人吃蟹讲究“九雌十雄”,重阳后母蟹满黄,立冬公蟹膏肥。
最地道的做法是清蒸,捆好蟹上锅,水开蒸25分钟,拆绳蘸姜醋,蟹肉丝丝甜。
若想换花样,面拖蟹裹面粉炸至金黄,
或做蟹黄汪豆腐,豆腐滑如雪,蟹黄点成金。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三国时孙权在此设“花津渡”码头,渔民便用竹簖围出蟹塘,让蟹苗在石臼湖、
固城湖的清水里“练游泳”。
明代《高淳县志》载:“淳邑湖荡多蟹,秋深时肥美异常”,
连老北京四大名医施今墨都夸它是“蟹中状元”。
青背白肚的固城湖蟹,蒸熟后红得透亮,蟹黄像溏心蛋般流油。
清蒸是最地道的吃法,姜片垫底,旺火蒸15分钟,
掀盖时满屋飘着湖水的鲜气。
老饕们还会用蟹肉拌高淳水八鲜,或是拿蟹黄熬成秃黄油,拌饭能多吃三碗。

传说绕着"H"形蟹壳转——大禹治水时赐蟹神耜,日久融为背甲纹路。
乾隆南巡时尝此蟹,赐名"玉爪金钩",自此成为贡品。
湖畔至今流传"秋风响,蟹脚痒"的民谣,中秋渔家必办"蟹宴",
老饕们守着"九雌十雄"的规矩,非等到母蟹满膏、公蟹溢脂才动筷。
这蟹生得青壳白肚,金爪螯强,蒸熟后蟹黄红亮赛秋阳,蟹肉细如银丝,甜得像刚掰的嫩藕。
当地人最爱"面拖蟹":
蟹块裹面糊炸至金黄,再与毛豆同煮,汤汁浓稠能挂勺。
老渔民说:"洪泽蟹的鲜是带水汽的,连蟹壳都透着铁锅炖鱼的香。"

老宿迁人讲究“九月尝黄,十月品膏”,这时候的母蟹抱着一肚子金黄流心的蟹黄,
公蟹则揣着白玉似的蟹膏,蒸锅一掀盖,那香得能勾掉人魂儿。
当地吃法最是本真,芦苇秆往蟹腿上一捆,撒把葱姜倒点黄酒,旺火蒸得蟹壳通红。
老渔民说:“咱骆马湖的蟹,水煮就成,甜丝丝的不用蘸料。”
可年轻人偏爱创新,蟹粉银鱼羹、蒜蓉烤蟹这些新派吃法,倒也把老味道玩出了新花样。
您瞧那蟹粉银鱼羹,金黄的蟹黄裹着银鱼,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
这蟹不光是口腹之欢,更藏着宿迁人的乡愁。

它的传说得从春秋战国讲起,楚王在太湖边初尝便上了瘾,
命人快马加鞭往宫里送。
这蟹生得俊俏,青壳白肚黄毛金爪,活脱脱水中的锦衣卫。
苏州人管没本事的叫"软脚蟹",写字像"蟹爬"。
中秋前后是吃蟹的黄金期,太湖蟹刚褪完最后一次壳,黄满得要溢出来。
老苏州讲究用蟹八件,敲敲打打能吃出仪式感,再配盏温过的黄酒,寒气全散了。
如今吴江人玩出新花样,蟹粉拌进东坡肉,蟹肉塞进生蚝肚,
连面里都要揉进蟹黄,叫人吃了直喊"灵个"。
太湖边的吃蟹节热闹得很,汉服姑娘提着灯笼巡游,非遗手作摊子挨着蟹宴长桌。

南朝《述异记》里就有的“簖”,是溱湖渔民用竹枝编的“水下龙门”,
能爬过去的蟹才配叫簖蟹。
老泰州人说:“南有阳澄湖闸蟹,北有溱湖簖蟹”,
这“南闸北簖”的叫法,倒像是一对水陆并称的兄弟。
青背白肚的金爪蟹,在溱湖二级水里养得膘肥体壮。
蒸熟后,雌蟹黄如金箔,雄蟹膏似凝脂,筷子尖一挑,鲜气直往鼻子里钻。
当地人最爱清蒸,姜片垫底,水开蒸十五分钟,蘸点姜醋。
要是馋辣,用豆瓣酱爆炒,红油裹着蟹身,连蟹壳都要嘬干净。

产自盐城,背壳如青玉磨光,肚皮白得透亮,金爪黄毛威风凛凛。
乾隆年间《盐城县志》就夸它“味较他处独美”,
传说大禹治水时巴解智斗“夹人虫”,意外成就这道人间至味。
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醉蟹斩获金奖,从此名扬四海。
蒸笼里蟹壳由青转红,香气直钻鼻子。
剥开蟹壳,金黄蟹黄如流霞,白嫩蟹肉蘸点姜醋,鲜得人舌尖打颤。
除清蒸外,醉蟹更是一绝:
曲酒、花椒腌透蟹身,酒香混着蟹香,嘬一口蟹黄,甜中带鲜,回味无穷。

明末郑正中捞起时曾叹"脂如玉",李白更把蟹螯比作金液,
说"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如今的白马湖蟹,青壳白肚像块温润的玉,
螯足裹着棕褐绒毛,步足金黄尖利,倒像从蟹爪菊里长出的精灵。
十月里蒸一笼,揭开盖那蟹黄如流金,膏脂似凝脂,
蘸点用醋、酱油、姜末熬的料,嘬一口,鲜得人舌尖发颤。
老饕们讲究"九月雌十月在雄",重阳前后约三五好友,
就着湖风喝女儿红,持螯把酒,倒真应了李白那句"蟹螯即金液"。

渊源可追溯至明清,郑板桥曾诗云“半湖秋水半湖蟹”,道尽其时蟹市之盛。
当地渔民至今保留“蟹簖”捕捞古法,
秋收后以竹簖围塘,待蟹自投罗网,此景被列入非遗名录。
2009年,兴化大闸蟹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老饕讲究“蟹八件”细品,但本地人更爱直接上手,蘸点姜醋提鲜,配壶高粱酒,吃得满手流油。
兴化人管吃蟹叫“啃蟹”,透着一股子豪气,
透鲜的蟹肉混着酒香,直叫人想起郑板桥那句“八爪横行四野惊”。
蟹农们还保留着“祭蟹神”的习俗,
秋分日船头摆三牲五谷,祈求蟹肥水美。

相传大禹治水时,巴解在阳澄湖畔率众以沸水烫死“夹人虫”,
意外品得其鲜,自此蟹入馔席。
唐时为贡品,宋人傅肱《蟹谱》称“苏尤多”,
清顾禄《清嘉录》更细数常熟“金爪蟹”、昆山“蔚迟蟹”等名品,
文人以“蟹八件”拆解,章太炎夫人曾叹“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
其形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蒸熟后壳红如玛瑙,蟹黄似金、膏白若玉,肉质细甜带回甘。
农历九月母蟹满黄,
十月公蟹盈膏,清蒸最显本味,配一碟姜醋、一盏黄酒,
便能品出“螯封嫩玉双双满”的诗意。

金秋时节,膏满黄肥,
拆一只蟹脚,蘸一勺姜醋,配一壶温酒,
便是江苏人最踏实的秋日仪式。
无论你尝过哪一湖的鲜,这份舌尖上的江湖气与烟火暖,
总归要亲自咬一口才懂。
来说说,你心中最念的那一口,是哪个湖的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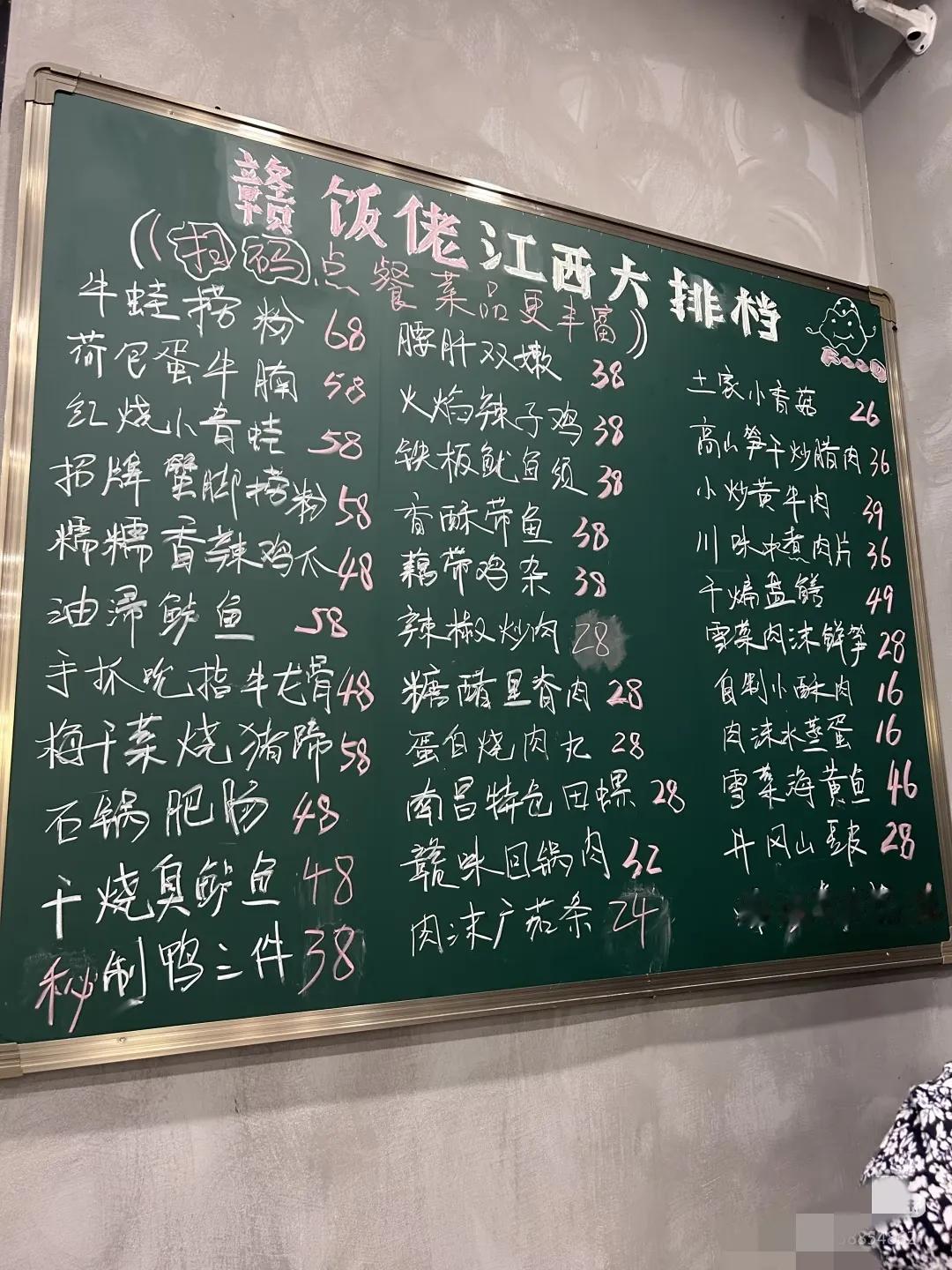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