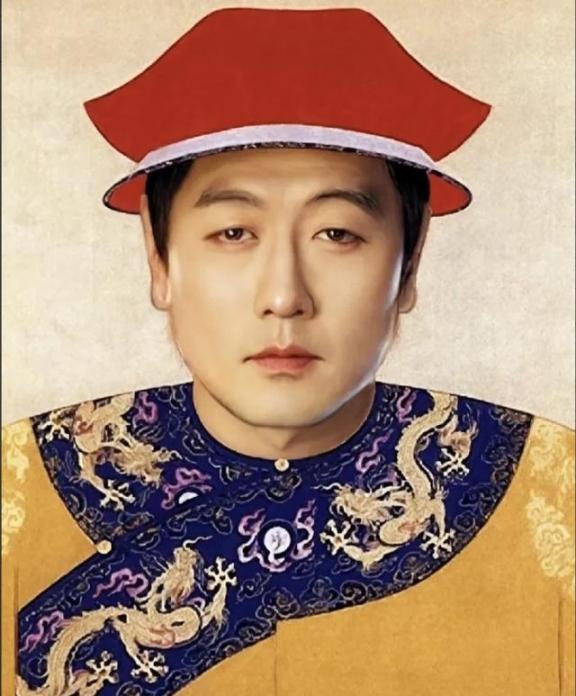乾隆二十九年,一封奏折建议为雍正诸兄追赐荣号,补录宗谱。乾隆朱笔圈批:“允禔旧事,不再议。”四字定局,彻底封死了胤禔生前最后一线平反可能。 哪怕雍正登基后曾陆续为允祥、允祉等兄弟恢复名分,哪怕太子胤礽后来也重新入谱,康熙的皇长子,却始终未得洗白。 乾隆为何坚持回避此案?一切要从胤禔当年失势说起。 康熙四十七年,皇宫内务府突然调令,要求彻查皇长子胤禔王府账目、来往客人、府中文书。无任何解释,只一道命令。 那段时间,朝中传闻不少。有说他私下延请术士布坛“改运”,也有人私下议论他与民间江湖人物交往频繁。 事情的引爆点,是一封诗稿。诗中多次暗指“天命有归”“长者当政”“太子不才”,虽未明言皇权更替,但已足够敏感。更重要的,是有人拿出了证据,称该诗为胤禔旧部所作,府中抄录流传。 康熙震怒。当夜召见胤禔。无人知晓两人谈了什么,只知道第二日清晨,皇榜张贴:皇长子胤禔养疾,暂归王邸,削去朝权,限制交游。 外间尚未反应,太子党人与对立阵营已开始互相告诫:胤禔已被排除。不久之后,内务府又发现他曾委托属下编写一套《帝学述要》,内容表面是讲君主之德,实则对比历代长子失位、储君废立,暗示当前太子应慎言慎行,不可负国望。 康熙未曾公开表态,仅私下批示:“存心不正。” 再之后,胤禔被软禁于景山福宁宫,终身不得离宫一步。他未再上折子,也未曾求情。只每日读书抄经,后期连贴身伺候的宦人都换了数轮。 再往前推几年,胤禔其实并非毫无可能接近储位。虽非嫡出,但长子之名在外,早年曾领兵护边,颇有武功。加之为人沉稳,外间评价常在“宽厚”“有礼”之间徘徊。 真正引起康熙警惕的,是他过早布置人手,谋划朝中布局。 他曾私下资助一批寒门士子,以“讲学”为名延请入府,并暗中安排部分弟子拜入言官门下。还曾通过内务府外派人员打探各王府书信动向。其布局周密程度,在诸皇子中少有匹敌。 康熙开始时并未深究。但当太子胤礽两次被废,朝局动荡,各皇子暗流涌动,胤禔的行为被重新解读。 尤其是术士张明德一事,对他打击极大。张明德入府之后,曾数次设坛“驱祟”。有人在府内见到其所焚符纸上写有“克除内变”字样。虽无直接证据指向太子,但康熙从不容忍巫蛊之事。 张明德很快“失踪”,胤禔也在几日后被召入宫内,从此被隔绝于政治之外。 乾隆为何不为他翻案?看似无情,实则多重顾虑。 乾隆极重视“嫡庶有别、储位有正”,一旦替皇长子平反,是否意味着雍正继位曾有失正统?这一点,他绝不能动。 其次,胤禔虽无兵变之实,却早有图谋之迹。他自认功劳不下太子,私下结党,设讲堂、立口号、鼓动士人,不是造反,却已越界。 乾隆对这类行为极为敏感。即使他内心知晓胤禔之举未至死罪,也要在制度上彻底封口,堵绝后世质疑。 而胤禔晚年,也似乎彻底认清局势。他曾写下《易经随笔》数卷,自印留存,不敢流通。序言中写:“人之一念,可通达;可陷身。”寥寥几字,算是自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