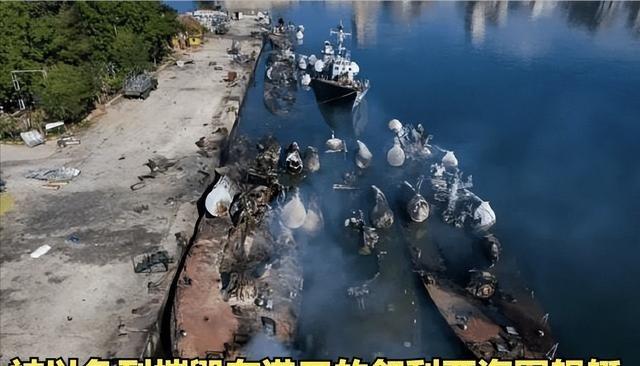为什么说美国人一旦破产,基本就没机会翻身?一位居住美国10多年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街头的流浪汉,可不全是穷人,他们反而更多的是中产阶级,甚至是曾经的成功人士,破产了才变成流浪汉的,可为什么他们破产后不能重新打拼呢? 纽约布鲁克林的地铁口,59 岁的孙卫东裹紧那件沾满污渍、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外套,枯瘦的手指在乞讨牌上反复擦拭着 “可提供数学辅导” 几个模糊的字迹。 很难有人将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眼神浑浊的流浪汉,与曾经手握李政道奖学金、在华尔街拿着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复旦天才联系起来。 如今,他成了华人圈里最出名的美国街头流浪者 —— 每当有同胞在街头遇到他,或是通过社交媒体劝他回国时,孙卫东总是沉默良久,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孙卫东的沉沦并非孤例,在美国 65.3 万流浪汉群体中,像他这样从人生巅峰跌落至生活泥潭的前中产阶级,占比超过了半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调查显示,45% 的流浪汉在破产前拥有百万美元资产,30% 曾是企业高管或各领域的专业人士。 但这些曾经的成功人士,一旦坠入贫困的深渊,想要重新爬起来却难如登天,这背后,是美国社会对 “失败者” 近乎残酷的系统性排斥。 破产者东山再起的第一道坎,便是信用体系的 “死刑判决”。 美国是一个纯粹的信用社会,个人破产记录会在信用报告中保留至少十年,而这十年里,生活的每一步都会被这一记录牢牢束缚。 租房时,房东只要看到信用报告上的破产记录,大多会直接将其过滤掉,连看房的机会都不给;求职时,雇主在背景调查中发现破产履历,便会下意识地认为此人 “缺乏责任感”。 曾有一位美籍华人企业家,因公司经营不善倒闭破产,走投无路之下想靠刷盘子糊口,却发现只要有工资到账,银行就会优先划扣用于抵债,无奈之下,他只能打黑工,用现金结算。 更残酷的是,破产往往伴随着资产的彻底清零,而美国每年 1% 的房产税和高昂的物业费,早已耗尽了他们最后的缓冲空间 心理创伤与成瘾陷阱,则成了破产者重新站起来的第二重枷锁。在美国流浪汉群体中,70% 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或成瘾问题。 大麻在多个州的合法化,让许多在绝望中挣扎的破产者,轻易就能接触到这些能暂时麻痹神经的东西,进而染上毒瘾或酒瘾,陷入 “吸毒酗酒 - 无法工作 - 更加绝望 - 依赖成瘾物” 的恶性循环。 按理说,这样的困境本应被社会福利体系接住,可美国的保障网络早已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一场重病,可能让一个年收入二十万美元的家庭瞬间掏空积蓄,甚至背上债务,最终走向破产。 而本应作为兜底保障的住房保障计划,也因联邦预算连年削减,沦为了 “纸面福利”。 在纽约,申请公租房的等待时间长达 8 年,许多人等到头发都白了,也没能等到一个安稳的住处; 洛杉矶的收容所床位缺口超过 10 万个,每到夜晚,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蜷缩在帐篷里、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 面对日益庞大的流浪汉群体,美国政府的态度充满了矛盾与功利,所谓的 “解决措施” 大多停留在表面。 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在华盛顿部署国民警卫队,强行清理流浪营地,威胁那些拒不配合的流浪汉,称他们将面临罚款或监禁; 可清理之后,却只是将这些流浪汉安置到 “远离首都核心区” 的偏远区域,美其名曰 “打击犯罪、维护城市形象”,实则是在掩盖社会治理失效的政治作秀。 即便美国的街头充斥着这样的困境,每年仍有数十万人怀揣着 “美国梦”,前赴后继地赶往这片土地。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他们相信自己能成为 “幸运儿”;还有人被长期灌输的 “成功学叙事” 裹挟,坚信美国是 “只要努力就能逆袭” 的热土 如今,孙卫东依旧在布鲁克林的地铁口徘徊,母校复旦大学的校友会曾得知他的情况,为他提供了临时住所和简单的工作机会 可长期的流浪生活早已让他丧失了适应正常工作的能力,没过多久,他还是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铁口。 在美国的繁华与破败之间,孙卫东们的故事揭示着一个残酷的真相:这片土地既孕育了一夜暴富的传奇,也制造着一夕沉沦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