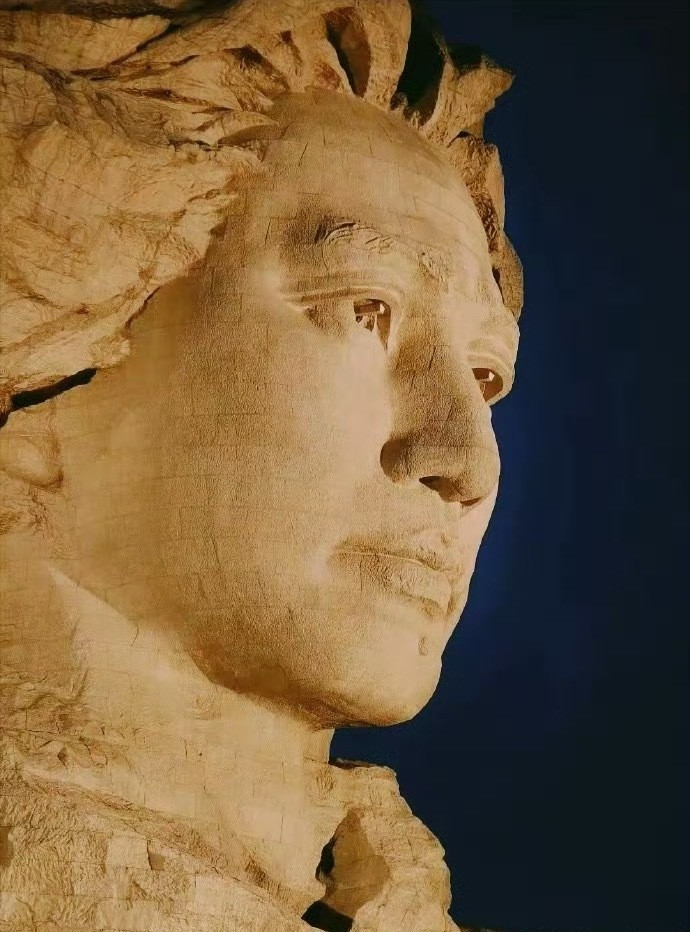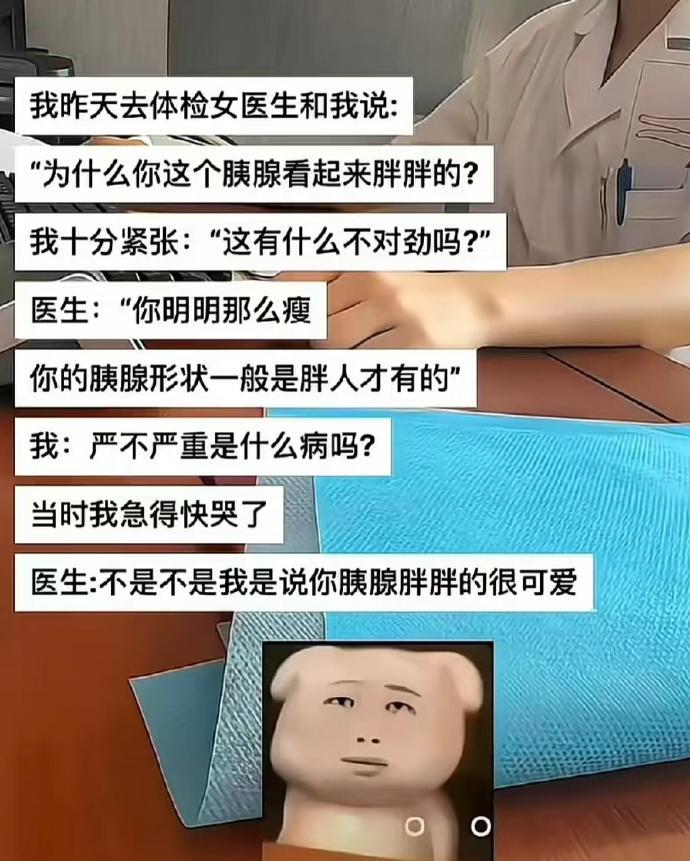他从大军区政委降为地方干部,搞文艺有声有色,后靠边站十几年 “1961年早春,北风还硬,周桓把帽檐压得很低,小声对身旁老部下说:‘换条战线,也要有胜仗可打。’”这句话,道出了他离开军队之后的心气儿,也预示了一个上将转身投入地方文艺战线的罕见轨迹。 周桓的故事须从一张退学通知书讲起。1928年,初三没念完,他因病回家。父亲劝他学手艺糊口,他却硬拖着行李跑到天津,蹭读天津中山中学,学费全免。课堂之外,他第一次碰见地下党员,第一次听到“推翻旧世界”四个字;那年头,书本之外的风声更让血液加速。两年后,他悄悄从津门奔赴湘鄂赣苏区,年仅十九岁便成了红五军政治部秘书,军长是彭德怀。写文告、刻蜡板、油印传单——枯燥到眼花,但他咬牙坚持。有人疑惑,为什么不端枪?他只笑:“宣传也是子弹。” 1933年调总政部,他负责发动群众分田地。天黑赶路,白天开会,晚上写材料,鞋底磨穿,他把草绳捆在布鞋外继续走。几个月后又去中央警卫师,当政治部主任,警卫毛泽东、周恩来出入,谨慎又紧张。随军辗转,积攒的其实是政治工作经验——这是他后来安身立命的“武器”。 到长征尾声,他已是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陕甘之交,红军需要同东北军谈判,周桓被推了出来。有人形容他“笑容和霜刃一起闪”,软硬皆施,让东北军这支杂牌队心甘情愿地停火、让路,埋下日后改编的种子。很快,抗战全面爆发,他改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部长。两位退伍的东北军师长带两百旧部归队,他领头翻越太行山,一路收容散兵游勇两三千人,在浆水川立了新根据地。统战、整编、教育,三手同用,一年打出名堂。 抗战末期,他调回总部做秘书长,日常就是见友军,写电报,谈条件。说话得像针,又像棉。抗战胜利后,他出现在沈阳街头,身份是东北军政大学政委。不到半年,被罗荣桓点名调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当副主任。那段时间,东北报名参军的青年多到排长队,周桓夜里一张桌子批卷宗,凌晨把盖完章的任命书送到训练场。两年,扩军至七十万,地方武装三十五万,军区后勤、医院、学校同步拉起。他常说一句话:“兵要练,骨干更要练。”这是他心里的指标。 1949年夏,他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共和国刚成立,东北要成“工业上将”。干部结构不平衡,他与谭政、肖劲光一道,把二十余个临时机构合并,腾出人手支援大后方。紧接着抗美援朝打响,部队需要熟面孔稳定军心,他坐镇沈阳,多次飞安东,前后方协调,忙到声音嘶哑。 1955年,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邓华任司令,他当政委。授衔时,他拿到上将肩章,外人看风光,熟人知内情——想让他多休息,他偏不。在他眼里,军政工作就是不断发现漏洞、补漏洞。惋惜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风向急转,因与彭德怀渊源深,他被调出军队,改任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艺。职位表面“平移”,实际上是明降。老参谋悄悄问:“政委,这算挫折吗?”他摆手:“岗位不同,打仗不变。” 新岗位,他把文化馆、剧团、出版社当作兵团来管。辽芭的《白毛女》重排,他亲自盯服装;长影拍《冬梅》,他蹲片场聊剧本。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群众最缺精神食粮。1964年辽宁省文艺汇演,戏曲、新歌、速写展铺满沈阳体育馆,中央派人观摩,周桓只是坐在角落,手里捏一张观众意见表。有人感慨:“这老将干起文艺,比指挥团长还带劲。” 遗憾的是,文艺工作做到高潮,运动骤然来临。1966年,“军阀”“走资派”的大字报一起飞,他挨批斗,头发被涂墨,靠墙站一整夜算常事。1970年代初,他被下放,住在海城郊区一间四面透风的小房。时常有群众来翻看他写过的戏曲脚本,翻完又走;那几年,他唯一乐趣是给青年辅导写诗,“押韵要像磨刀”——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 1979年春,文化部请他进京做顾问。三十年戎马,二十年文艺,十年沉寂,他归来不急不躁。文件刚批到手,他先去八一电影制片厂,跟导演讨论军队史料真实性;三天后,他又跑到辽宁歌舞团排练厅,指导朝鲜族舞蹈动作。有人问他为什么还折腾,他淡淡回答:“宣传工作,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小花边。” 周桓晚年不谈磨难,偶尔提到庐山会议,只是一句“形势比人强”。最常讲的,是战士与观众的眼神——前者盯胜利,后者盯舞台;二者都要真诚,假不得。他的一生,几次起落,脚下的路却始终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信念通过语言、旋律、形象抵达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