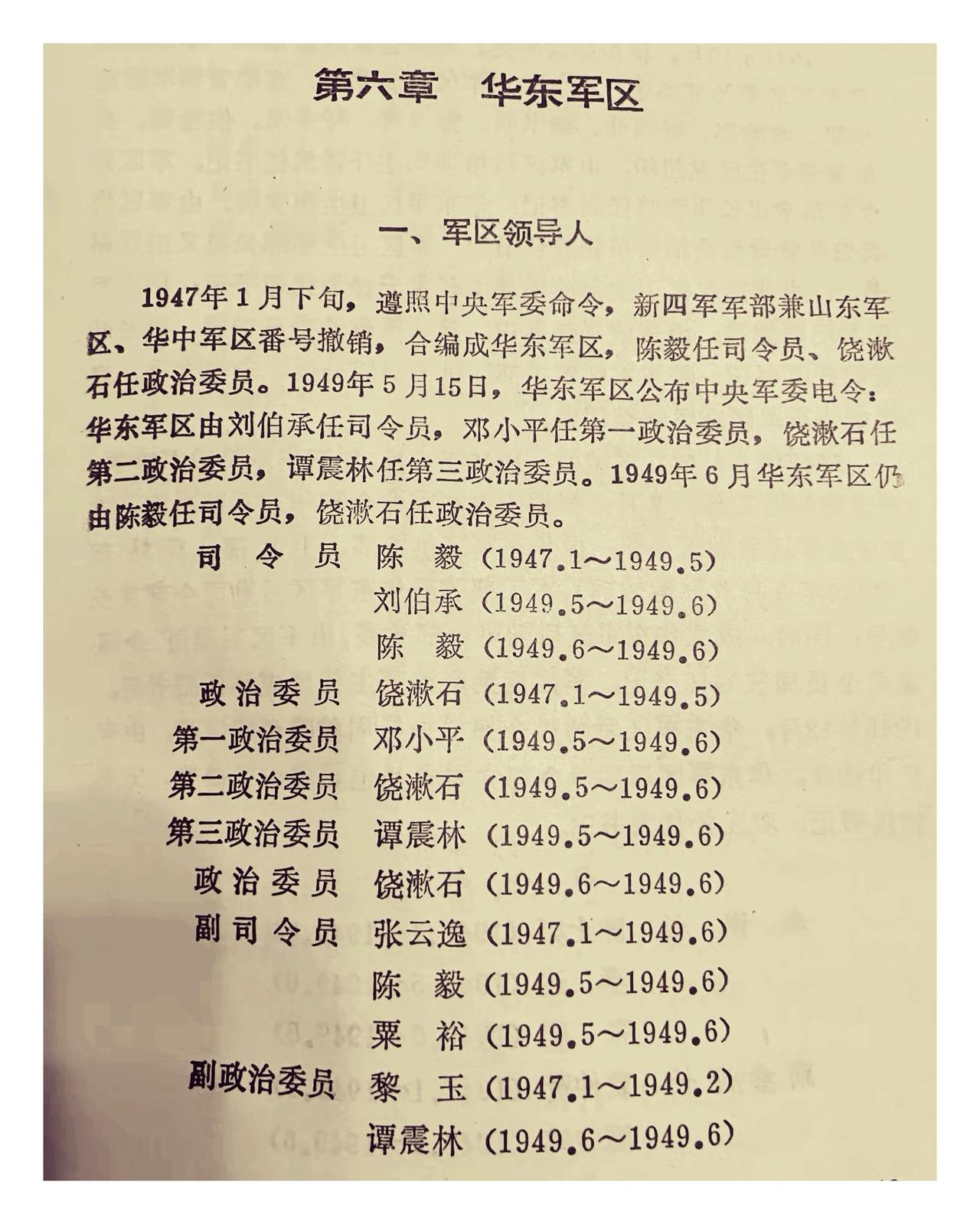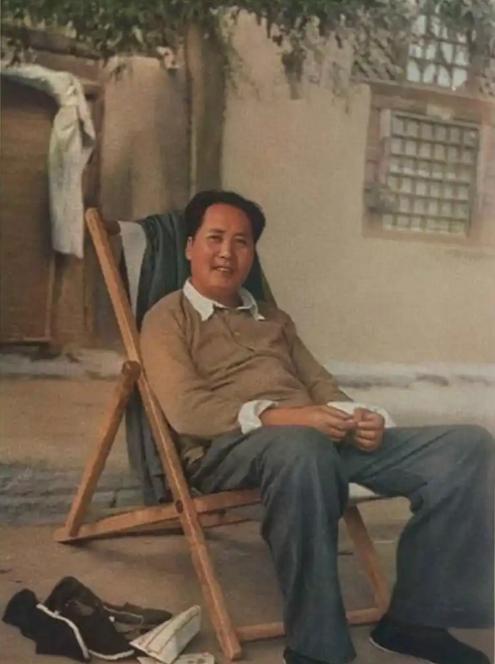国民党上将总司令张发奎,绝对是国民政府中真正的奇葩,在他的部队中,有名有姓的共产党人有两千多名,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却不管不问。 1927年武汉街头的梧桐叶刚刚泛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司令部里收到了汪精卫签发的"分共"密令。 这份要求立即清剿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指令,被他随手放在了抽屉最底层。 当天下午,他召集叶挺、廖乾吾等心腹军官密谈,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张发奎看着这些明显带有共产党身份的部下,只说了句"形势紧张,你们好自为之"。 三天后,叶挺率部南下时,每个共产党员都领到了一笔足够路上使用的路费,这笔钱正是张发奎从司令部经费中调拨的。 在那个党派界限日渐分明的年代,张发奎的部队简直是个异数。北伐战争期间,他率领的第四军被称为"铁军",而这支部队的先锋叶挺独立团里,十个士兵中就有九个是共产党员。 更让人吃惊的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十一军参谋长张云逸这些关键岗位,都由共产党人担任。 有次蒋介石派来的特派员暗访部队,回去后在报告里写道:"第四军政治部墙上,三民主义标语旁边竟然贴着共产党的宣传画。" 张发奎对此却毫不在意,他对部下说:"只要能打胜仗,管他是什么党派。"这种实用主义的治军理念,让他的部队成了国共合作的特殊试验田。 张发奎的包容并非没有底线,他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1926年攻打武昌城时,共产党员组织的敢死队冒着炮火架设浮桥,这种牺牲精神让他深受震撼。 他在日记里写道:"共产党的政工干部有办法让士兵拼命,国民党的军官只会喊口号。"因此他默许共产党人在部队里开展活动,甚至允许他们发展党员,只要不公开反对三民主义就行。 当武汉分校的共产党员学员面临被遣散的命运时,是张发奎站出来说"编入我的军官教导团",保住了这股革命力量。 1927年的夏天成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后,武汉的汪精卫也开始动摇。张发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厌恶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却又无法认同共产党的阶级革命。 当周总理秘密接触他,希望他参与武装起义时,张发奎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是国民党的军人,不能背叛党国。" 但他也没有出卖这个秘密,反而提前给叶挺、贺龙等人透风,让他们做好准备。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斥责他"通共",张发奎只辩解了一句:"他们都是北伐功臣,我下不了手。" 这种在国共之间走钢丝的做法,让张发奎成了双方都不放心的人物。汪精卫觉得他对共产党太宽容,蒋介石始终提防他成为新的军阀,而共产党则认为他不够彻底。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汪精卫严令张发奎清剿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他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却给共产党人开了"通行证"。 当时第二方面军有近三分之二的军官是共产党员,张发奎没有派兵抓捕,只是逐个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离开部队,要么脱离共产党。" 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显得格外另类。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的这种矛盾性格更加明显。他在淞沪战场上建立秘密炮兵观测所,专门打击日军战舰,却拒绝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命令。 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的司令部里有中共秘密党员担任侍从秘书,负责起草重要文件。1939年桂南会战期间,他采纳共产党人提出的游击战建议,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有次国民党特务举报某团长是共产党,张发奎压下报告说:"这个人打仗很勇敢,等打完这仗再说。"结果这个团长在战斗中牺牲,成了无名英雄。 张发奎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但政治上的摇摆不定最终影响了他的命运。他始终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既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又不能接受共产党的革命路线。 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让他在历史转折关头屡屡错失机会。南昌起义前,中共曾许诺让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只要他公开反蒋,但他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汪精卫。 等到汪精卫叛国投敌,他才不得不投靠蒋介石,却始终得不到信任。晚年在香港定居时,他看着墙上挂着的北伐地图,常常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错就错在总想在国共之间找平衡。" 这位国民党上将的部队里走出了五位元帅和六位大将,这在国民党军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叶挺、贺龙、张云逸这些共产党人都曾在他麾下效力,而他始终以"能打仗"为由包容他们的存在。 这种看似奇葩的做法,其实反映了那个年代部分爱国将领的真实心态:在民族大义面前,党派之争应该暂时搁置。 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他参与内战时,张发奎毅然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他说:"打日本人我义不容辞,打自己人我做不到。" 1980年张发奎在香港病逝,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希望骨灰能葬在广州黄花岗。这个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了一辈子钢丝的军人,最终选择回到那个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