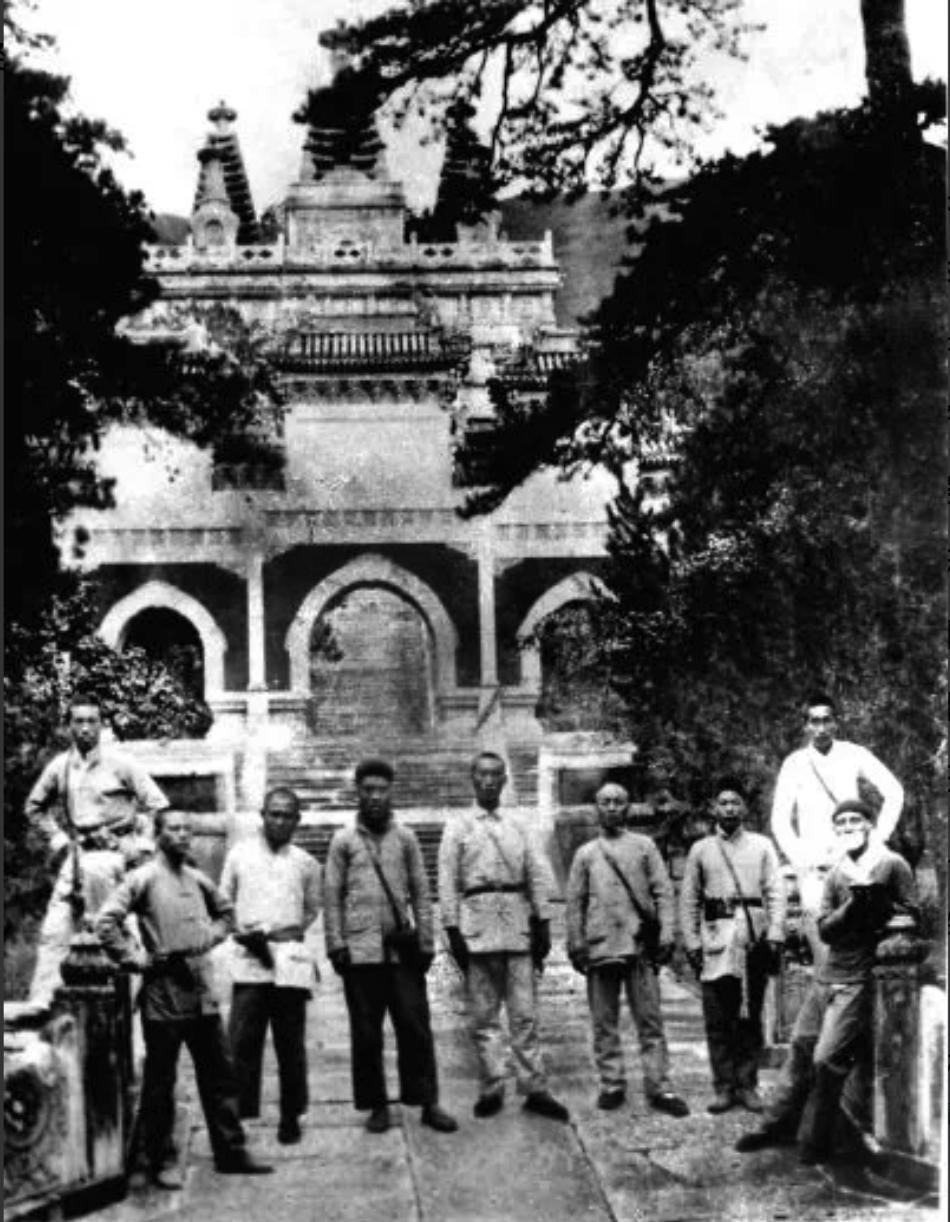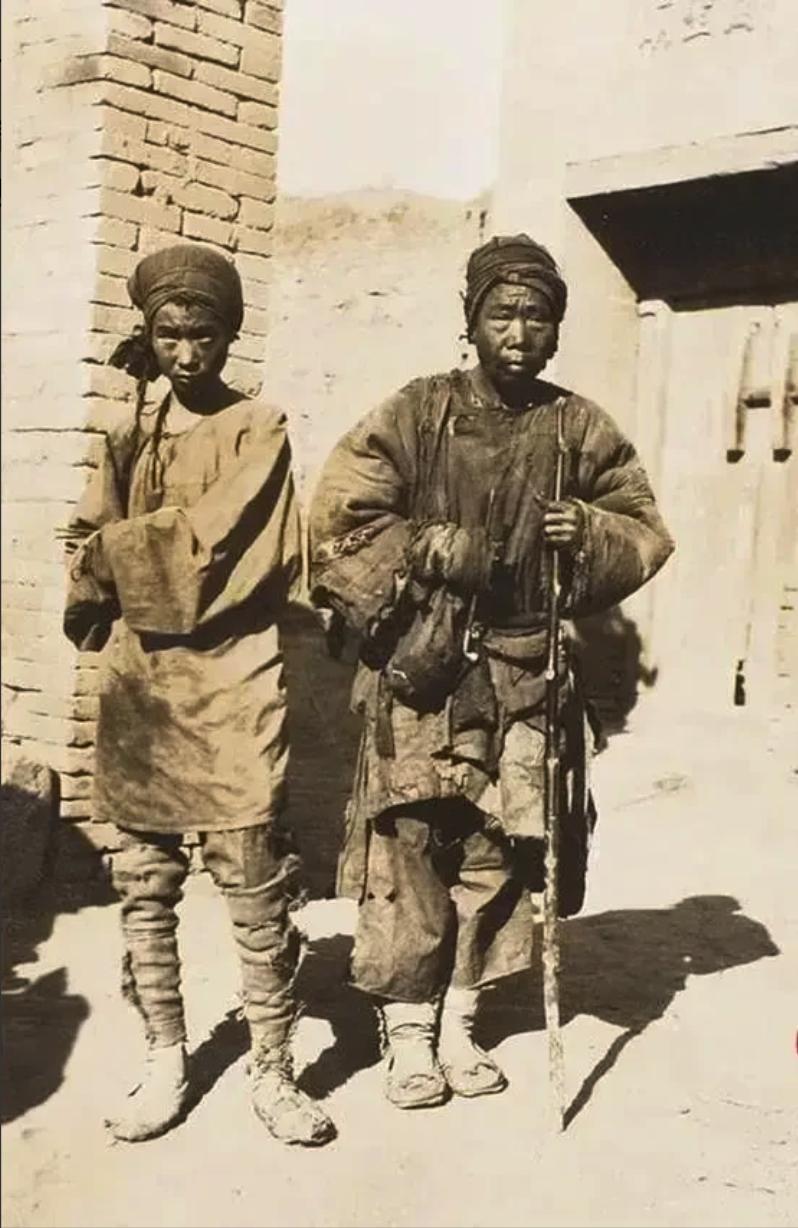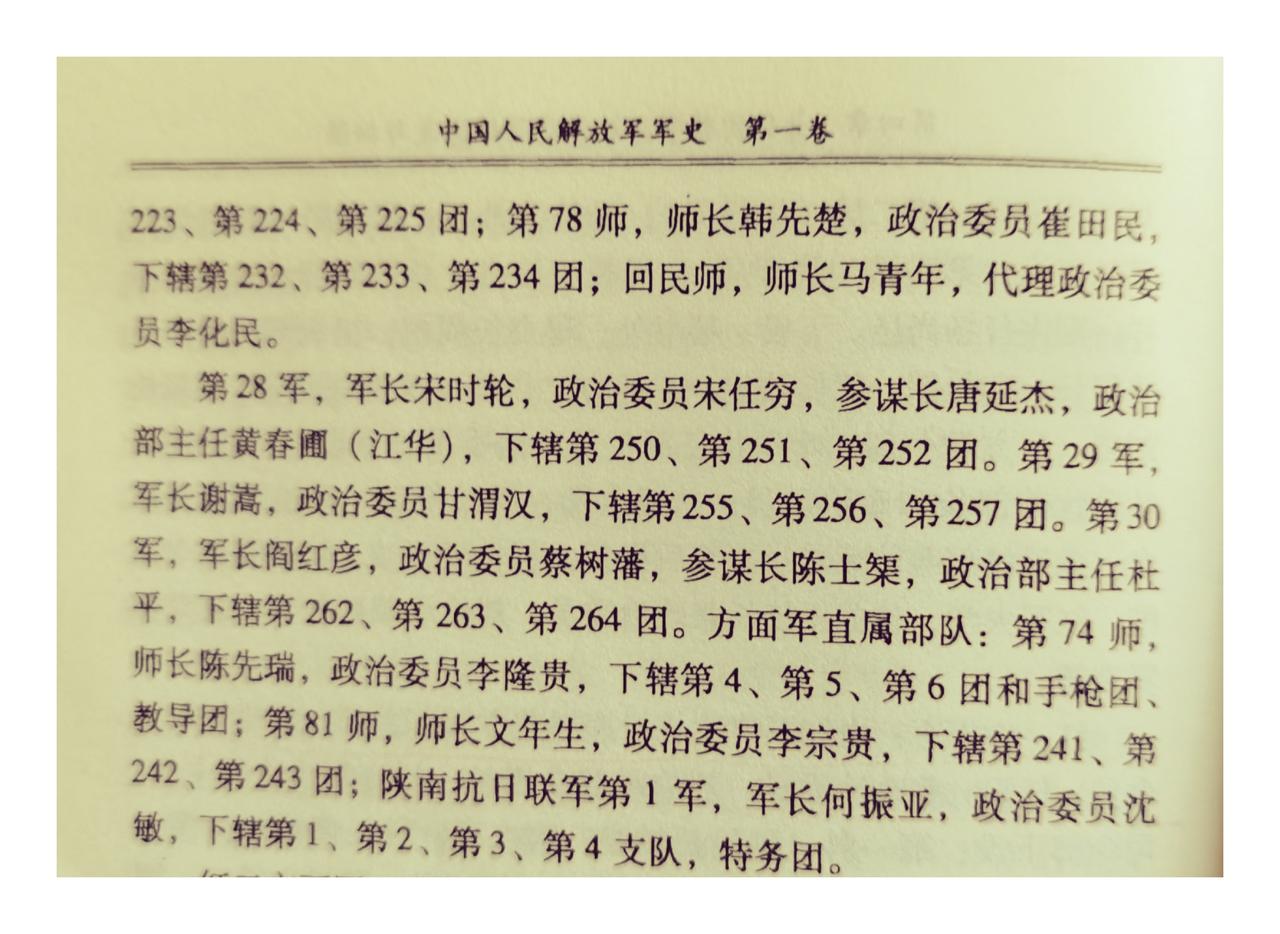1990年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委领导集体找他谈话,听取他的意见。很明显,这是平调,并非升迁,张万年却十分坚决地回答说服从命令。军委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张万年说我今年快63岁了,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我在广州的家就先不搬了。军队历来是人走家搬,张万年却说不搬家了,意思是等他退休后到广州养老。没想到两年后张万年非但没有退休,反而获得提拔,担任了总参谋长。 1990年,张万年快63岁了,他接到命令,要去济南军区当司令。 张万年倒也没反驳,去军委谈话时,开口第一句就是:“我在广州的家不搬了。”那意思摆得挺明白,济南就干个两年,交接清楚就退。 军队里历来讲规矩,人走家搬,他这回破了个例,没人说什么,领导也点头了。 到济南以后,他整天泡在部队里,听汇报、下连队、跑训练场。 那时候他不像个有“再进一步”打算的人,反倒像个准备善后的人,尽量把事情捋顺点,好让接班人省事。 但谁也没想到,两年一过,情况全变了。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一开完,新一届中央军委要组班子,名单上突然多出他这个名字:总参谋长。有点像是本来打算收摊儿的铺子,一夜之间翻红了。 不少人觉得惊讶,连张万年自己都反应慢了半拍。 他确实没做准备。 他以为两年一过就能回广州,躲开北方的干冷,安安稳稳过晚年。 可这回,退休遥遥无期。 说到底,选他不是拍脑袋。邓那阵儿反复提,总参谋长得是“真正带兵”的人,不要搞花架子的。 张万年这个人,不太爱说场面话,也不爱写什么“思想汇报”,但部队听他的。 他带过兵,打过仗,从基层摸上来的那一类人,部队最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他参军早,1944年,16岁那年,家乡动荡,参了八路。那一代兵,进部队不靠推荐信,全靠一条命扔在前线。 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自己都说不清。有时候伤疤多了,连记忆都乱了。解放战争里,他的部队总是被派去打硬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团长,后来当了“塔山英雄团”的团长,又去带了“铁军师”。这些番号不是说好听的,战史上有记录,谁打过,谁顶过,谁掉队,账都明明白白。 1978年,他还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 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立刻回部队。 很快,广西那边出动了,他率部队上前线,参加对越作战。他在一线待得时间不短,别人劝他在后方指挥,他摇头,说“眼睛得自己看”。仗打完,部队表现不错,报纸登了一篇长文,采访的是他本人,说他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 那篇文章被邓看到了,对他有印象,这事成了他后面一步一步升上来的伏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军队开始裁军、整编,那是大动作。 张万年也动了位置,从武汉调到广州,再从广州调到济南。 调来调去,看着像调动,其实更像是组织在观察他,看看他在不同地方管事的样子。 到济南后,他干得扎实。 军委那边听汇报听得顺耳,干部下面也服气。加上前些年邓对他有过关注,1992年一到换届,他就成了“上牌桌”的人选。 总参谋长不好干。 九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全在变。美军打伊拉克那一仗,打醒了不少人。 精确制导、电子战、空地协同,全是新东西。中国军队那时候技术落后,观念也跟不上。 张万年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干部学习高技术战争。 他常说一句话:“看不懂就打不好,得先把脑子换一换。”他不是搞技术出身的,但他知道自己不懂,就逼着大家学。 他自己参加培训班,听讲座,还把一帮总参干部拉着一起听。 他反复讲,“打仗别看你级别有多高,弄不清人家按哪个按钮发射,你就吃亏。”当时听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能反驳。 他说得对,那几年,整个军队被他搅得动起来了。 除了打仗,他还干了一件让人记得住的事:驻港部队筹备。那是个麻烦活,涉及部队编成、人员选拔、法律对接,还有和香港社会的关系协调。 他一手抓纪律,一手抓形象。 有人跟他说,这种事交给政工部门就好,他不答应,说“不能等出了事再补漏”。 他办事细,文件改来改去,光一个“驻港部队行为守则”他就改了六七稿。有人觉得他较真,他回一句:“较真才能不出乱子。” 到了1995年,他升任军委副主席。 这个职务份量很重,尤其在那个时候。因为很快,台湾那边选举引发局势紧张。 大陆开始军演,导弹试射,一时之间,各方关注。 张万年在这时候站在了最前面,负责协调总参的应对动作。外媒说他强硬,国内说他稳得住,不管怎么说,那个阶段的动作安排,都离不开他。 他不是轻易发话的人,但一旦发话,就没人敢不听。 2002年他退下来,没留任,也没多说话。 那年他已经七十五岁,头发全白了,走路慢了一些。 有人去看他,他总说一句:“现在讲的都不是我懂的了,我得闭嘴。”说完笑一笑,眼神还亮着。 2015年冬天,北京的风大,天灰着。 他走得不动声色,媒体出消息时,很多人停了一下,说了一句:“这人,是真打过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