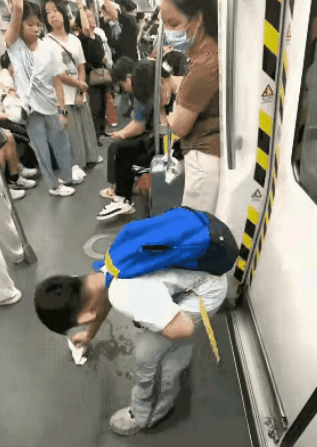1995年,广州一位倔强的老父亲执意北上京城,任凭儿女百般劝阻也不回头。直到开国上将亲自邀请他参观军事博物馆时,儿女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平凡的父亲竟藏着如此不平凡的过往...... 【消息源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战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南下干部口述史料》广东省档案馆2005年编印】 李德胜把搪瓷缸往桌上一撂,茶水溅在玻璃板下的老照片上。儿子李建军刚说出"爸您都七十多了"几个字,就被这声响吓得把后半句咽了回去。老人摸出皱巴巴的火车票时,女儿李小梅发现父亲右手虎口的疤痕在微微发亮——那是她小时候最爱缠着问,却总被岔开话题的旧伤。 "不就是去趟北京嘛,当年背着迫击炮翻五台山的时候..."老人突然刹住话头,摸出老花镜开始检查行李袋里的药盒。儿女们面面相觑,他们只知道父亲是1980年从北方调来的技术员,档案里"曾参军"三个字还是去年办老年证时才偶然看见的。 火车开动前,穿军装的中年人往车窗里塞了个牛皮纸袋。邻座的大娘好奇地问:"老哥是去参加战友会?"李德胜笑了笑:"找老伙计下盘棋。"纸袋里露出半截泛黄的《射击诸元表》,扉页钢笔字洇开了墨迹:晋察冀军区炮兵教导队,1939.3。 北京站月台上,两个佩着大校军衔的人脚跟一碰。老人摆摆手:"陈参谋现在抖起来了啊。"被称为陈参谋的白发将军突然红了眼眶:"报告炮长,三连应到六十八人..."话没说完就被老人打断:"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他们身后,军事博物馆的专车闪着双跳灯。 1995年的阳光穿过博物馆天窗,照在92式步兵炮的标牌上。李德胜突然蹲下,手指抚过炮架底部的凹痕:"这是昭和十四年阿部规秀的坐驾,咱们缴获时..."解说员惊讶地发现,展柜里尘封的《战斗详报》与老人此刻的讲述分秒不差。当他说到第四发炮弹卡壳时,突然解开衬衫第三颗纽扣——锁骨下方碗口大的伤疤让所有人倒吸凉气。 "当年要不是杨司令非让我住院,早跟着部队南下了。"老人摸着展柜玻璃,仿佛在抚摸当年的炮管。玻璃倒影里,白发将军正对年轻军官低语:"这就是教科书里黄土岭战役的..."话没说完就被老人孩子般的笑声打断——他发现了自己用罐头盒改装的瞄准具。 回韶关的列车上,乘务员看见老人对着车窗敬礼。窗外是暮色中的太行山轮廓,而老人眼里映着1939年的雪夜。当时还是新兵的他趴在冻土上,听见杨司令说:"小李子,咱们的炮要能打中那个亮灯的帐篷..."此刻他摸出口袋里的弹片,轻声哼起《炮兵进行曲》,调子与博物馆播放的史料录音完全重合。 三个月后,韶关厂区居委会收到北京寄来的包裹。褪色的军功章躺在崭新天鹅绒盒子里,底下压着泛黄的《火线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李德胜"三个字歪歪扭扭,与1995年退休金领取单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居委会主任突然想起,老人总说右耳听不清是"年轻时被炮震的"。 那年春节,李建军在父亲书桌抽屉发现本日文旧书。东京印书馆1940年版《阿部部队战史》第217页,铅笔批注力透纸背:"此处有误,第四发系哑弹,笔者亲见。"书页空白处还有句没头没尾的话:"杨司令,咱们的炮够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