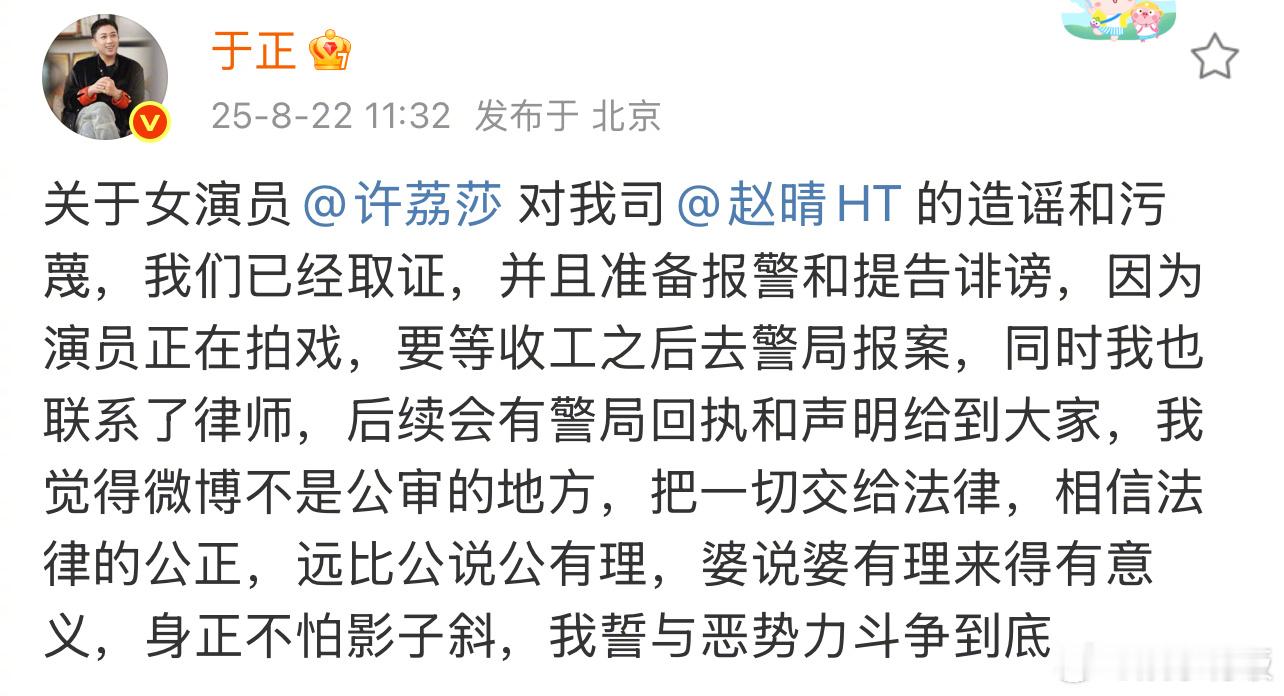有一次,俞飞鸿问金星:“做变性手术之前,碰过女人没?”金星回答:“没有,但娶过老婆。”接着她问俞飞鸿:“为啥都50多了还不结婚?” 1990年的纽约。那时金星刚拿到全额奖学金,在布鲁克林的阁楼里对着镜子发呆。镜子里的人肌肉线条分明,喉结随着呼吸轻轻滚动,可她总觉得那是副借来的躯壳。 为了留在美国搞现代舞,她和一个美国男孩领了证,结婚证上的“新郎”二字刺得她眼睛疼。没到半年,两人就和平解约,男孩临走前说:“你该找个能懂你裙子里藏着多少委屈的人。” 委屈这东西,她打小就攒着。九岁考军艺,老师摸着她的脚背直夸“天生的舞者”,可她盯着报名表上的“男学员”,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时她已经会偷偷把姐姐的花裙子套在军装里,夜里对着镜子转圈,觉得那才是真正的自己。 十二岁进沈阳军区歌舞团,凌晨四点的练功房,别人都在练劈叉,她却对着镜子捏自己的喉结,希望它能像冰块一样化掉。 有次排《红色娘子军》,她非要跳吴琼花,教官把乐谱摔在地上:“你见过带喉结的娘子军?”那天夜里,她把军被蒙过头,哭到枕头能拧出水。 可舞蹈终究是她的救命稻草。1988年在纽约,她跳《半梦》,台下的白人观众站起来鼓掌,有人喊“beautiful lady”,她鞠躬时,裙摆在舞台上扫出个漂亮的弧度——那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裙子,手抖得差点抓不住裙摆。 也是在那年,她在街头被个流浪汉嘲笑“人妖”,她没躲,反而挺直脊背:“我是女人,比你活得干净。” 1993年的北京友谊医院,母亲攥着她的手术同意书,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儿啊,这手术要锯盆骨、摘肋骨,疼啊。” 金星把母亲的手按在自己手背上,掌心的温度烫得惊人:“妈,不疼这遭,我这辈子都像穿着湿棉袄,捂得慌。” 第一次手术是隆胸,全麻醒来,她摸了摸胸口的柔软,笑着笑着就哭了,刀口裂开的疼都成了甜。 最疼的是除毛囊,医生用通电镊子一根根拔胡须根,电流烧得皮肉滋滋响,她咬着牙数到三百多,嘴里的纱布都被血浸透了。 最险的是生殖器重建手术。十六小时的手术后,护士发现她的左腿肿得像根紫萝卜,神经损伤严重。医生叹着气说:“能保住命就不错,别想跳舞了。” 可她偏不。复健室里,她拄着拐把腿往把杆上抬,汗珠子砸在地板上,溅起小小的水花。九个月后,她穿着舞鞋站在排练厅,旋转时,裙摆扫过地面,像只重生的蝶。 汉斯就是在这时闯进她生命的。1995年巴黎演出谢幕,这个德国男人捧着鸢尾花冲进后台,正好撞见她因为排异反应掉眼泪。她红着眼圈说:“我是变性人,你不怕?” 汉斯把花塞进她手里,用蹩脚的中文说:“你的舞蹈告诉我,你比谁都真。”后来领结婚证,民政局的人对着她的身份证犯难,汉斯拍着胸脯:“她是我妻子,法律不认,我认。” 《舞林大会》的评委席上,她的嘴比手术刀还利。有个小明星穿着镶钻裙跳芭蕾,足尖连站都站不稳,被她怼得满脸通红:“别用金箔纸裹着烂木头充艺术品。”转头却自掏腰包请北舞教授给对方补课。 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休息室永远备着红糖姜茶,哪个舞者崴了脚,她比谁都急,骂归骂,疼是真疼。 就像此刻,她看着俞飞鸿,忽然笑了:“我挨那十六小时的刀,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你不结婚,不也是不想将就吗?” 俞飞鸿碰了碰她的杯子,茶水晃出细碎的涟漪:“还是你活得明白。”窗外的月光漫进来,照在两人脸上,一个带着婚戒,一个没有,却都透着股谁也别想管的笃定。 上海的家里,三个收养的孩子正围着汉斯闹。金星推门进来,小女儿举着画跑过来:“妈妈,给你画的奖杯!” 客厅的陈列柜里,文化部“突出贡献艺术家”的证书旁,摆着张老照片——穿军装的少年在练功房压腿,眼神里已有了如今的倔强。 她亲了亲女儿的额头,心里清楚,当年那个对着镜子穿裙子的小孩,终究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金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