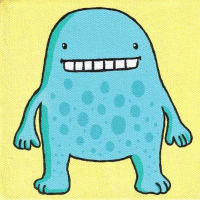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监狱的水泥地上,田汉蜷缩着身体时,怀里还揣着半块砚台。那是安娥1935年送他的,砚台边角被磨得光滑,背面刻着极小的“韧”字。 看守进来拖他时,砚台从怀里滑落,在地上磕出个豁口,像他此刻断了的肋骨。没人知道,这砚台里曾磨过《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聂耳当年就是对着这砚台里的墨,谱出了那激昂的旋律。 时间往回推五十年,湖南田家塅的私塾里,六岁的田汉正踮脚够先生案上的《千家诗》。 杨督学指着他鞋上的牛粪嘲讽“农家子难登大雅”,他仰头回嘴“官老爷披羊皮更俗”,气得督学吹胡子,却让躲在门后的表妹易漱瑜捂嘴偷笑。 后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田汉边啃冷饭团边翻译剧本,省下钱给易漱瑜买呢子外套,她总摸着他冻裂的手说:“你的笔比棉袍暖。” 1925年易漱瑜咳着血临终,攥着《南国月刊》的创刊号,那上面有田汉写的《获虎之夜》,字里行间全是他们在果园镇看社戏的影子。 安娥第一次出现在戏剧排练场时,裹着灰围巾,坐在最后一排啃干馒头。田汉正为《卡门》的结局发愁,她突然开口:“革命者的死,该像火星子,能燎起大火。” 那几年,他白天写《谢瑶环》,夜里给瘫痪的安娥擦身,她不能说话,就用能动的手指敲他手背打节奏,他便顺着节奏哼新写的唱段,病房里的月光,都跟着晃成了戏台的水袖。 文革开始那天,红卫兵闯进家时,田汉正给安娥读报。他们把《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子摔在他脸上,骂“反革命小调”,他扑过去抢,被按在地上。 审讯室里,铁棍敲碎了他握笔的右手,他却用左手在墙上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血字洇进墙缝,像极了他年轻时在长沙师范写《新教子》被教员摔碎的砚台。 那时他把《三娘教子》改成寡妇送子参军,说“戏得跟着时代走”。 1975年冬天,安娥躺在病床上,手里捏着平反通知。那是田汉去世七年后,组织派人送来的,通知上“恢复党籍”四个字被她摸得发皱。 她让女儿把田汉床底的木箱打开,里面有件没送出去的呢子外套,是1940年准备给安娥的,当时她去了敌后,外套就一直压在箱底,陪着他熬过无数创作的夜。 外套口袋里,掉出张泛黄的纸,是《关汉卿》的修改笔记,最后一行写着“玉可碎,不可改其白”。 安娥去世那天,窗外飘着雪,像极了1938年他们在重庆排《丽人行》的日子。那时林维中雇人往剧场海报泼红漆,安娥就用肥皂水一点点擦,田汉站在她身后。 把刚领到的稿费全塞给她:“别理那些,戏比天大。”如今女儿把那半块带豁口的砚台放在她枕边,砚台里仿佛还盛着墨,能写出比岁月更长久的东西。 葬礼上,有人轻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起时,风卷着雪掠过墓碑,像田汉当年在剧场后台,总爱哼的那句“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主要信源:(光明网——《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