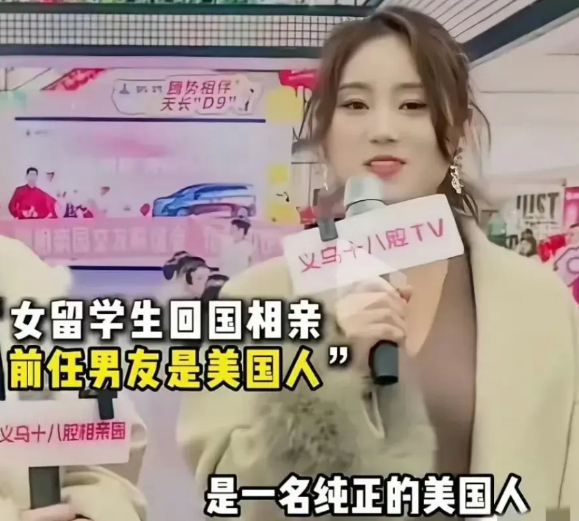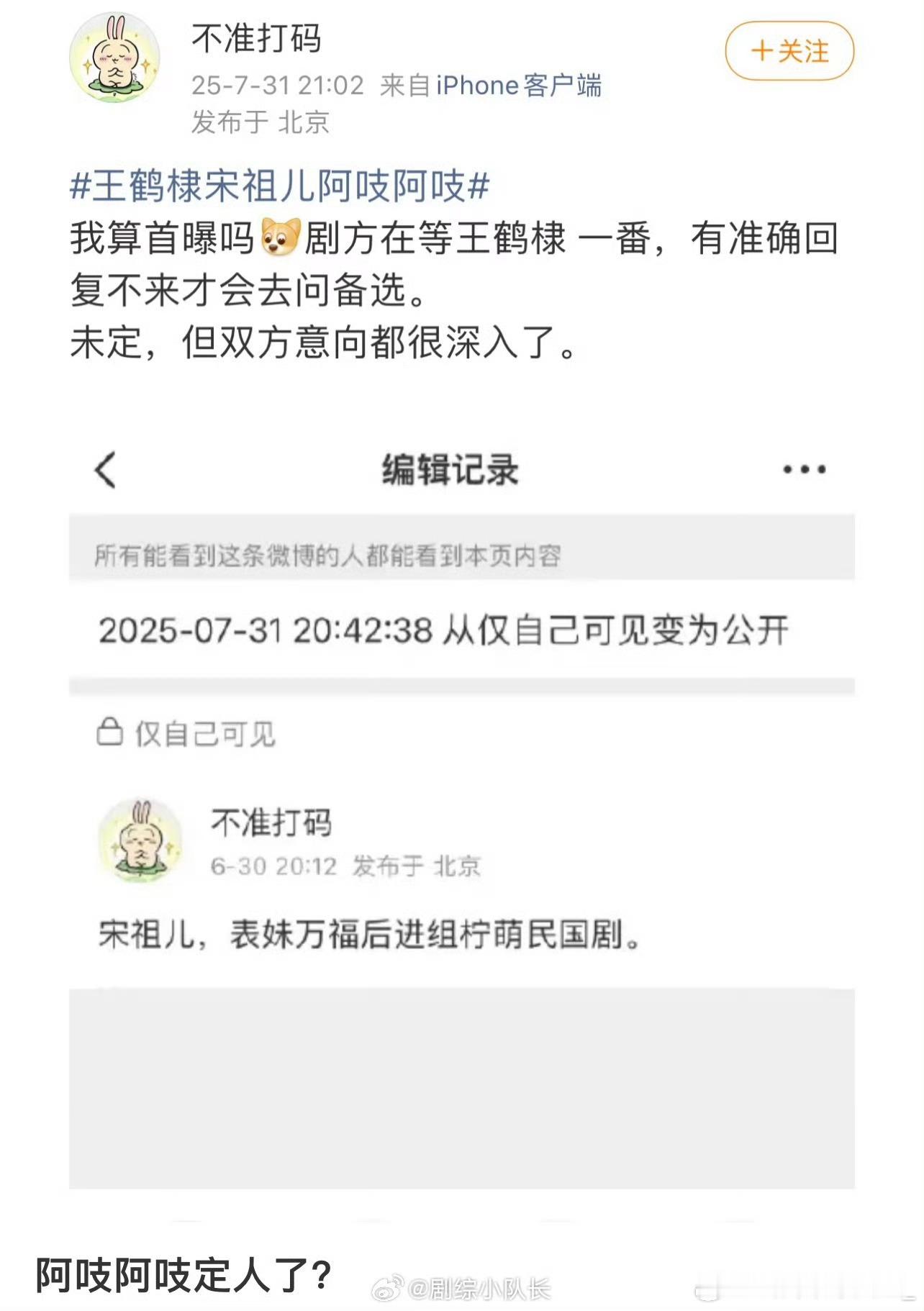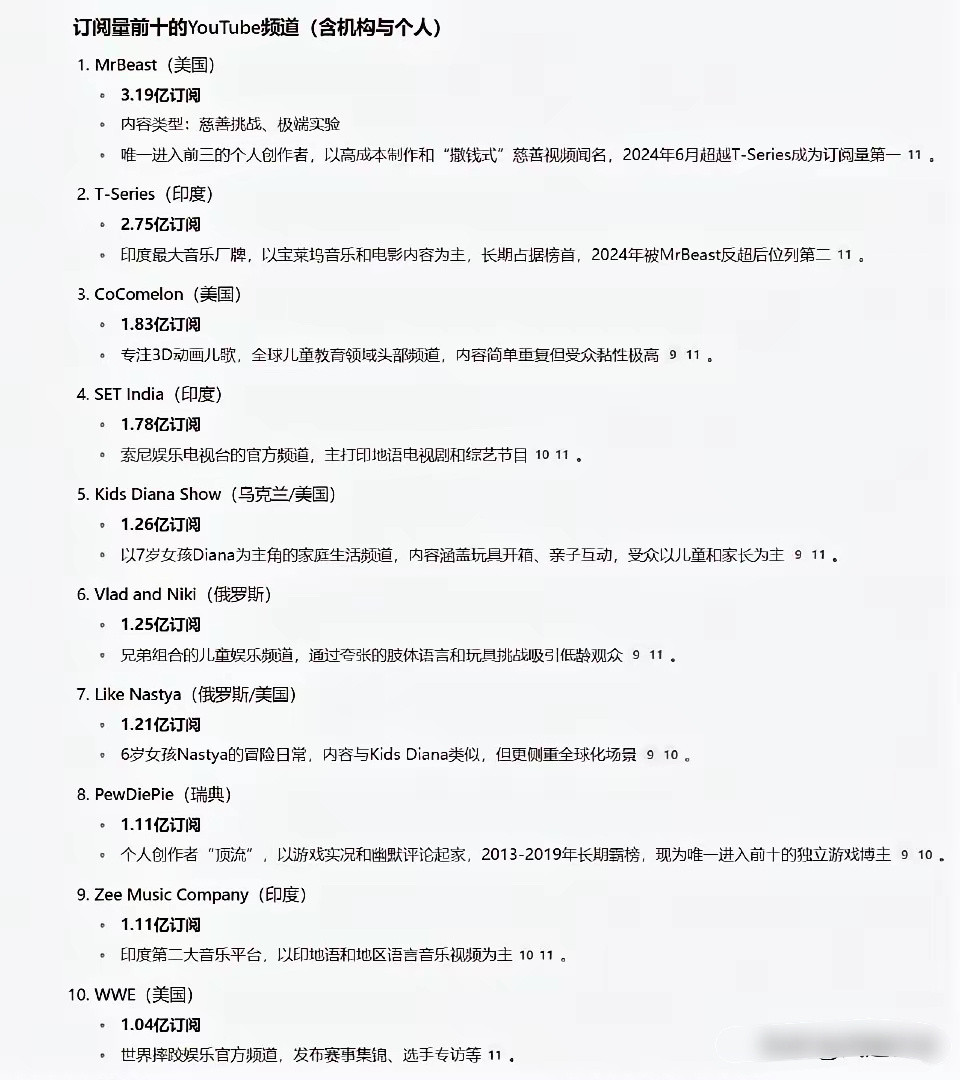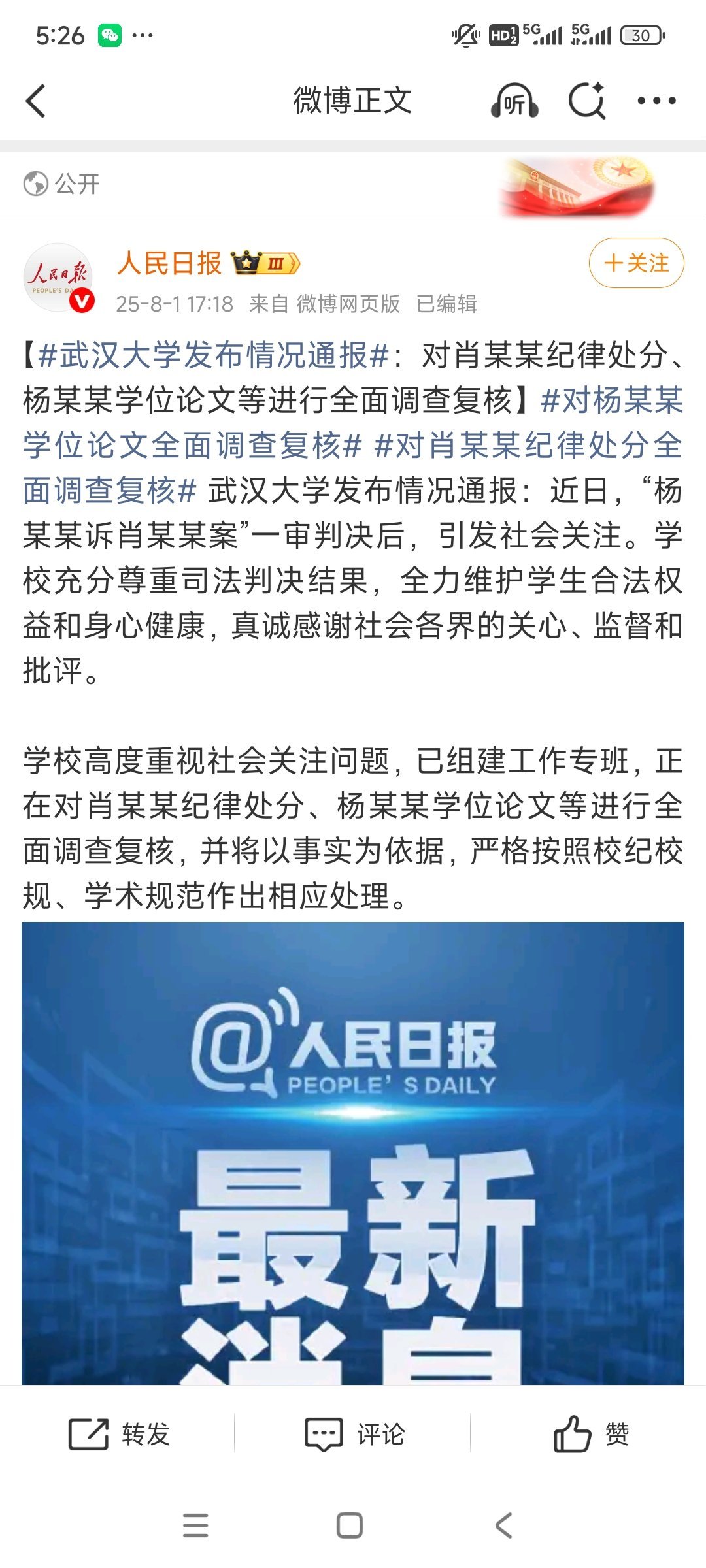92年:取消粮票。 95年:实行双休。 06年: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粮管所的历史任务也完成了,我们从06年开始,再也见不到排着长队去交公粮的场景。 几千年的农业税政策,在我们新中国的手中彻底废止了。 聊起农业税,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个很遥远的名词。 可如果把时间线往回推,它背后的故事一点都不遥远,甚至可以说,它贯穿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命运。 自从春秋战国有了“初税亩”,田赋就成了中国农民绕不开的一道坎。 历朝历代,农民与国家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就是那一担担粮食、那一串串铜钱。皇帝坐在宫殿里,王朝的机器能不能运转,靠的就是农田里收上来的那点东西。 几千年下来,农民和“交税”这两个字几乎绑在了一起。 哪怕到了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兵荒马乱,但地方衙门的催粮照旧。 农民家里再穷,哪怕揭不开锅,也得先把税交上去。 田赋不光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一种心理阴影。很多人一提到“官”,脑子里就想到“税”。 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看似有了新面貌,但底子其实没那么快能改变。 国家要恢复建设,粮食、资金都要依靠农村。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业税条例》,明确了农业税的征收办法。 对农民来说,交公粮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不管你家收成好坏,定额都要完成。 那时候,老百姓的心态很复杂。 一方面,大家愿意支持新政权,觉得这是为国家出力;可另一方面,心里也明白,粮食一旦交出去,家里人能不能吃饱,全看年景和分配。 几十年里,农业税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农民牢牢拴住。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经济逐渐松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活力,可农民肩上的负担并没有真的减轻。 除了农业税本身,还有“三提五统”等名目的收费。村里修路、盖校舍、办活动,往往要从农民手里摊派。那时候,农民心里憋屈,种了地,辛苦一年,最后算账,净落不下几个钱。 有人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种田像在给别人打工,辛苦是自己的,收获还得交一大半出去。 国家并不是没看到问题。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央连续下发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整治乱收费、乱摊派。 可文件下去了,效果有限。 地方财政没钱,干部压力在那儿摆着,不收点,运转不下去。 就算有检查,基层往往也有对策,农民负担问题,就这样成了一个久拖不决的老大难。 真正的转机是在2000年。 中央决定在安徽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这次试点的思路很明确,就是要摸索一条“减负”的路。 安徽的经验表明,如果由上级财政兜底,农民的日子立马好过不少。 2003年,这场改革在全国推开。中央财政每年拨款几百亿元,帮助地方弥补缺口。这个动作,算是从制度上动了“农民减负”的根。 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成了压轴戏。 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一天,可以说是写进了中国农民的集体记忆。 自此以后,农民种地不再需要交农业税,这个延续2600多年的制度彻底终结。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远远超出数字本身。 有人算过账,全国每年大概能减轻农民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约一百多元。 看起来数字不算太大,但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这一百多元能买多少东西?更重要的是心理感受。 几千年来,农民一想到田地就想到税,想到交公粮,想到上缴。 突然有一天,国家说不用交了,还会补贴你,这种心态上的轻松感,是以前任何一项改革都难以带来的。 取消农业税还带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国家角色的转型。 过去,国家是征收者,是要农民上缴的那一方。取消之后,国家变成了补贴者,是把钱和资源投向农民的一方。这种关系的变化,意味着农民和政府之间从“负担—征收”走向“支持—服务”。 在制度设计上,这一步走得很关键,它标志着城乡关系正在被重新塑造。 基层治理的逻辑也随之发生转变。 以前,乡镇干部一年到头最操心的就是收粮、催税,这是硬任务。取消农业税后,这个任务消失了,干部们要开始想办法发展经济、引进项目、落实补贴。 有人把这种转型形容为“从管钱到管事”。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其实背后是基层治理模式的深刻调整。 不过问题也随之出现。 失去了农业税这一块财政来源,很多基层政府一下子“悬空”了。 地方财政更依赖上级转移支付,有的乡镇甚至连日常运转都要靠拨款。 这也带来新的矛盾:如何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保证基层有足够的财力去维持公共服务?这道题,直到今天仍在探索。 从更大的格局看,取消农业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它 不仅仅是财政制度的调整,更是农民地位的改变。农民从“被索取者”变成了“被扶持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在交,总是在被动承担。 2006年之后,这个逻辑被打破了。农民不再是单纯的供养者,而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