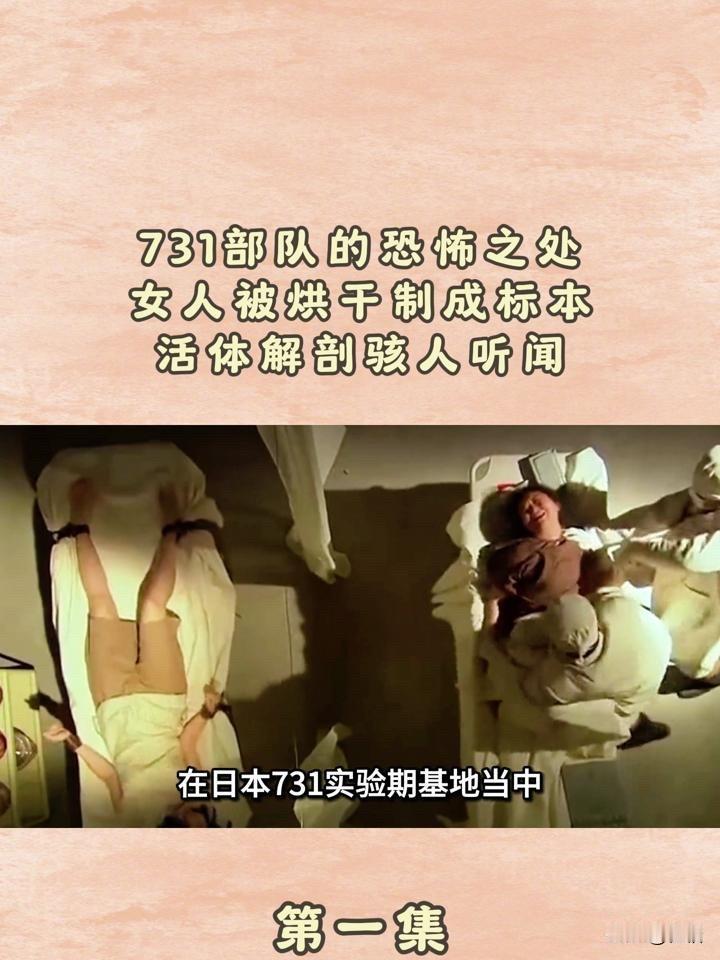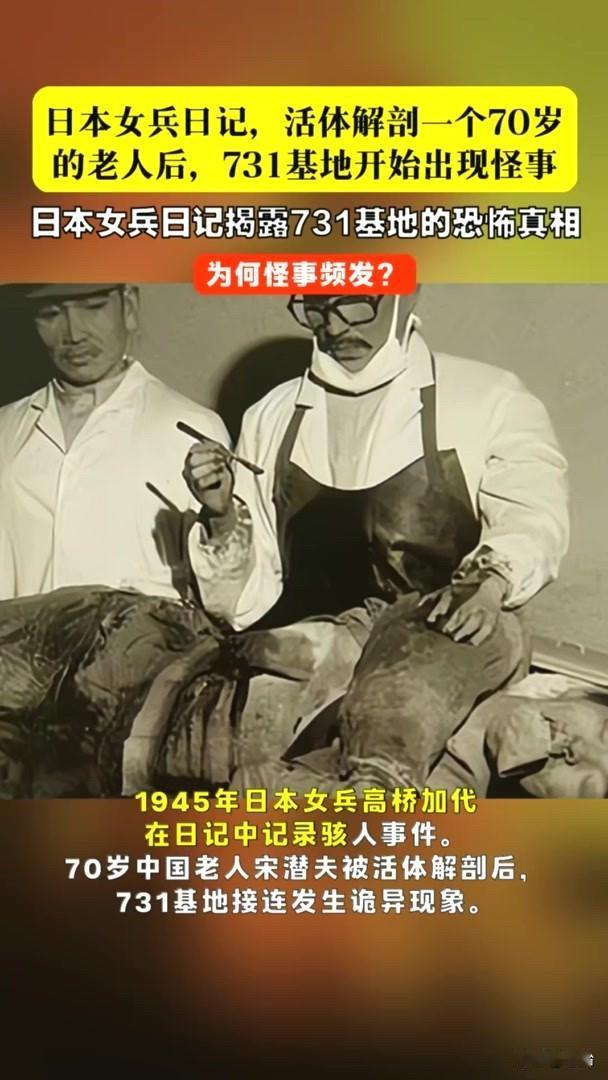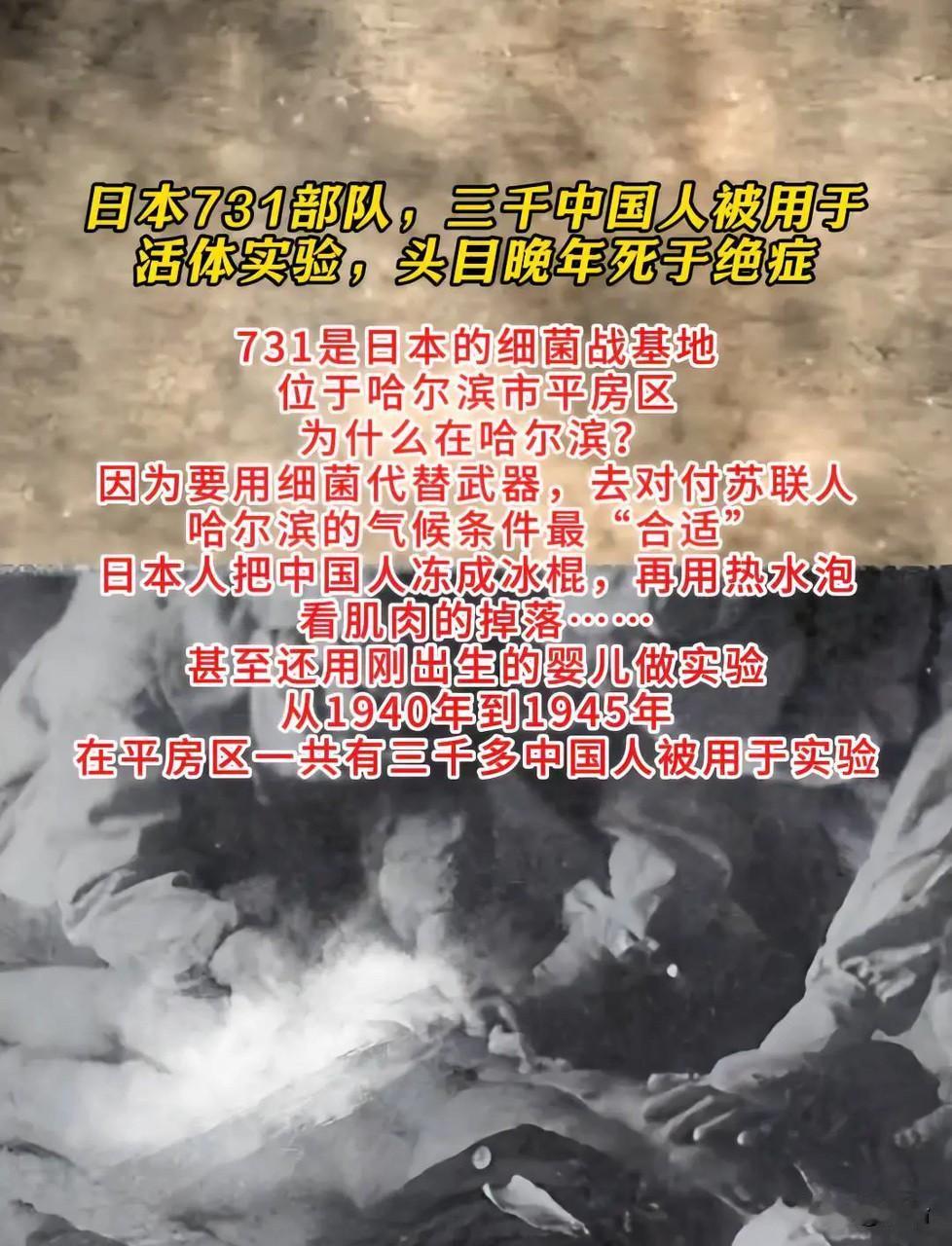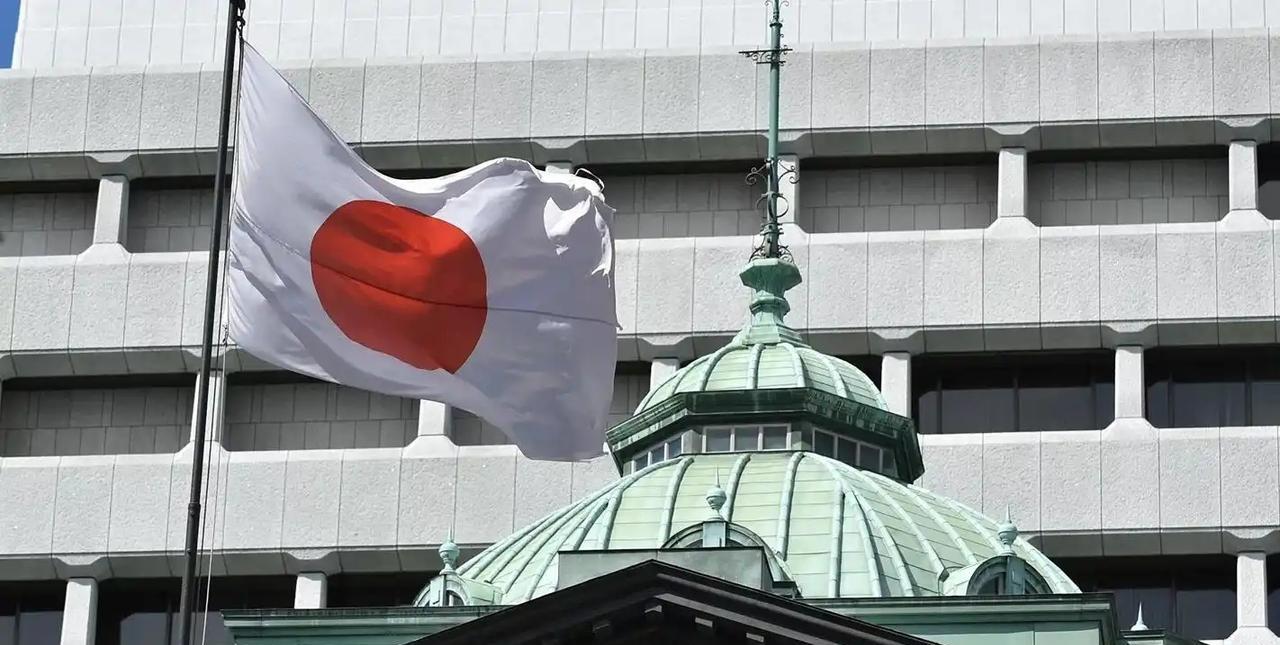1944年11月,在731基地的四方楼里,日本女军医高桥加代接到了一条命令,今天要解剖一个特殊的病例。活体解剖在731里算不得什么,青田军医官嘴里说的“特殊病例”,倒是引起了高桥加代的注意。 进解剖室前,她在走廊里撞见了负责押送的卫兵。那人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嘴里嘟囔着“这女人骨头真硬”。 解剖室的铁门锁“咔哒”一声弹开,寒气混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面而来。高桥加代捏着解剖刀的手紧了紧——她来731基地两年,见过被注射病菌后溃烂的平民,见过被活活冻伤的战俘,早就学会了把脸埋在口罩里,不去看那些痛苦的眼睛。可今天,手术台上的女人,让她的呼吸猛地顿了一下。 女人看起来三十多岁,穿着破烂的囚服,手腕和脚踝上的镣铐磨出了血痂。但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蜷缩发抖,而是挺直了脊背,头发被汗水粘在额上,露出的眼睛亮得吓人,正死死盯着天花板的铁钩,像是在数上面的锈迹。青田军医官踹了踹手术台:“高桥,开始!这是‘马鲁他’(731对活体实验者的蔑称)里少见的‘抗药性体质’,好好记录。” 高桥加代的手术刀刚碰到女人的皮肤,对方突然动了。不是挣扎,而是猛地转过头,目光像淬了冰,直直扎进她眼里。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嘲讽的平静,仿佛在说“你们这些人,也配碰我?”高桥加代的手一抖,刀尖在皮肤上划出一道浅痕,血珠渗出来,像落在雪地上的红梅。 “八嘎!”青田军医官扬手就要打,女人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说的是生硬的日语:“别碰她。要剖,就快点。” 卫兵说的“骨头硬”,此刻有了答案。高桥加代后来才知道,这女人是东北抗联的交通员,被捕时吞了藏情报的蜡丸,日军灌了她三天催吐剂,敲掉了她两颗牙,她硬是没松口。押来731前,她还咬伤了一个卫兵的耳朵。 解剖进行到一半,女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出的血溅在高桥加代的白大褂上。青田军医官不耐烦地吼:“加大麻醉剂量!”高桥加代握着针管,却迟迟没动手——她看见女人咳完后,用尽力气往墙角挪了挪,那里藏着一小撮干硬的泥土,是她从牢房带过来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屑。 这场景让高桥加代想起三年前,她在东京医学院读书时,妹妹拿着从中国寄来的明信片,兴奋地说“那里的人会在院子里种向日葵”。那时的她,以为战争是为了“大东亚共荣”,直到被征召进731,看见第一个被解剖的婴儿,才明白所谓的“共荣”,不过是用刺刀和手术刀写就的谎言。 “还愣着干什么?”青田的呵斥拉回她的神。高桥加代闭了闭眼,将麻醉针推进女人的血管。女人的眼神渐渐涣散,却在彻底失去意识前,轻轻说了句中文,声音很轻,像风拂过麦田。高桥加代听不懂,但猜得出,那一定不是求饶。 那天的解剖记录,高桥加代写得格外潦草。她在“实验对象反应”一栏,本该写“无明显抵抗”,却鬼使神差地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花——像妹妹明信片上的向日葵。 三个月后,高桥加代在整理废弃标本时,发现了那个女人的遗物:一块磨得发亮的铜怀表,背面刻着“抗联”两个字,表盖里夹着一张小照片,上面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她突然想起女人最后说的那句话,或许是在说“我的孩子,要好好活着”。 1945年日本投降时,高桥加代烧掉了所有解剖记录,只带走了那块怀表。她站在四方楼的废墟前,听着远处苏军的枪声,终于敢哭出来——为那些被她亲手送上手术台的生命,为那个眼神如刀的女人,也为自己被军国主义吞噬的良知。 有人说,在731的地狱里,没人能全身而退。可那个硬骨头的女人,用她的不屈,在一个刽子手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忏悔的种子。 你说,当罪恶成为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微弱良知,是会被彻底碾碎,还是能在某个瞬间,被一丝人性的微光唤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