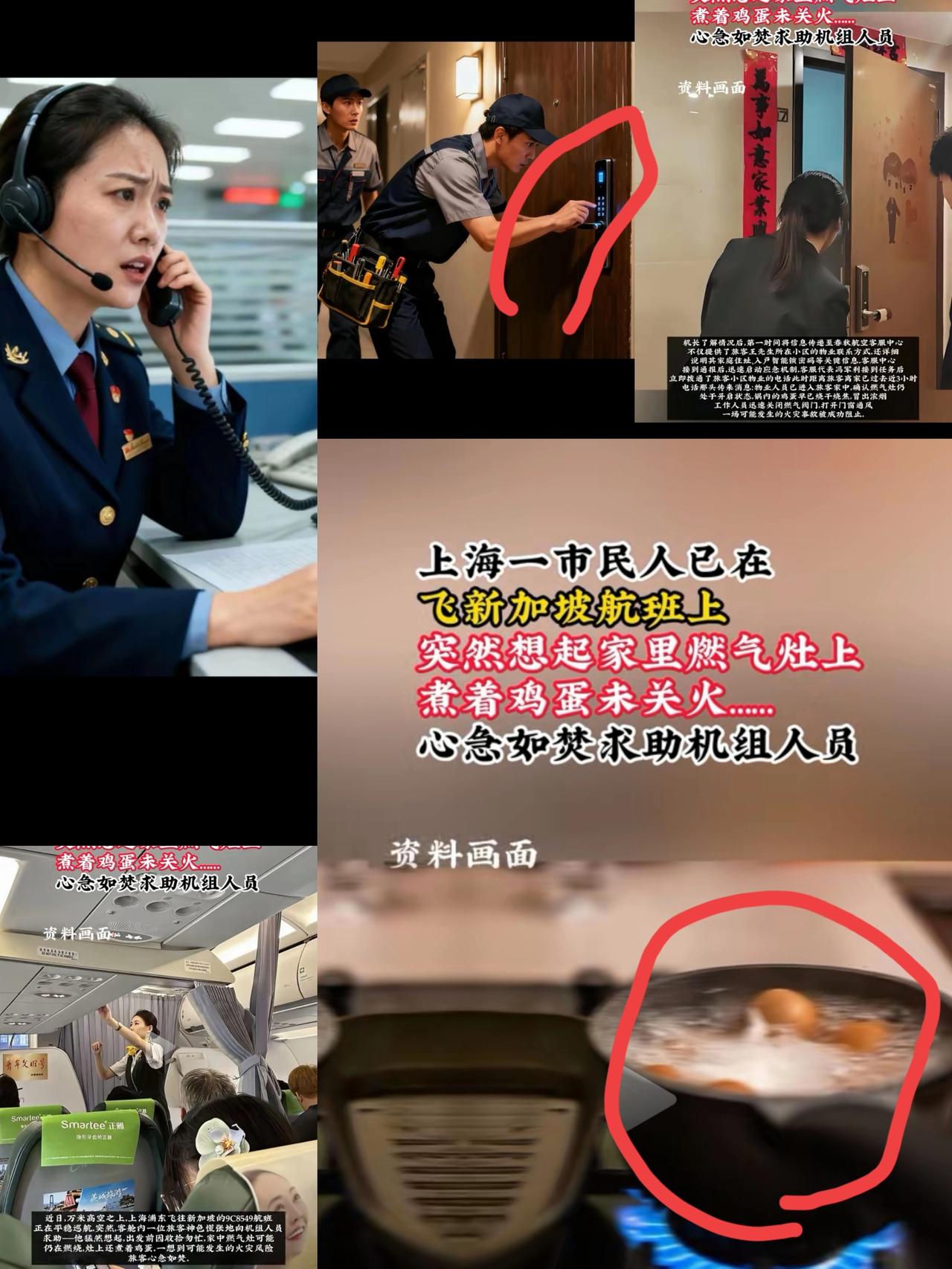1950年,宋时轮在饭店吃饭,无意间听到了老板的名字,他手猛地一抖,放下筷子对服务员说:“快带我去见她!”
当时,宋时轮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员,穿着一身军装,刚处理完公务,走进一家餐馆。
他翻了翻菜单,抬眼问服务员:“你们这儿有啥招牌菜?”
服务员指着菜单上一道菜说:“这个是我们老板娘董竹君自己创的,别处吃不着。”
“董竹君?”
宋时轮猛地站起来,抓住服务员的胳膊:“你再说一遍,老板娘叫啥?”
服务员被他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就…… 就叫董竹君啊。”
宋时轮这才松开手,语气缓和下来:“别怕,我认识她。二十年前,她帮过我大忙。你快带我去见她。”
服务员见他穿着军装,不像坏人,赶紧点头:“您跟我来。”
没过两分钟,一个穿着深色旗袍的女人走进来。她头发梳得整齐,戴着一副细框眼镜,看着很干练。
“您是?” 女人开口问。
“董大姐,我是宋时轮啊!” 宋时轮的声音有点抖。
女人愣住了,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睁大了眼睛:“你是…… 当年那个受伤的年轻人?”
宋时轮重重点头。
1929年,宋时轮刚从广州的监狱里出来。他腿上受了伤,是被敌人用烙铁烫的,裤腿上还渗着血。
他在上海的法租界里慢慢走,心里直发慌。和党组织断了联系,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
他找到朋友李堂萼。李堂萼在石库门门口拉着他,压低声音说:“特务盯我盯得紧,不能留你。你去法租界找个叫董竹君的,她开了家锦江小餐,说不定能帮你。”
李堂萼塞给他一封信,信封上写着 “董竹君亲启”。
宋时轮攥着信,一瘸一拐地找到华格臬路的锦江小餐。
店里伙计领着他进了账房。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算账,穿着月白色的旗袍,头发上别着支玉簪。她就是董竹君。
宋时轮把信递过去。
董竹君看完信,抬头打量他,见他腿上有伤,立刻说:“楼上有房间,先上去歇着。我让厨房给你下碗阳春面。”
到了楼上房间,董竹君让他坐下,解开他的裤腿看伤口。
她皱起眉,从口袋里掏出块真丝手帕,撕成布条:“都化脓了。我让账房老周带你去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
宋时轮这才注意到,她手腕上戴着个翡翠镯子,看着很贵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她丈夫夏之时当年从成都带来的聘礼。
董竹君早年过得不容易。她十二岁被卖到青楼,后来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跟着他去日本留过学。1929 年的时候,她已经和夏之时分开,带着几个孩子在上海打拼,开了这家锦江小餐。
三天后,宋时轮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董竹君把一个红色的皮箱放到他面前:“打开看看。”
宋时轮掀开箱子,里面有八块银元,还有一张去武汉的船票。
董竹君凑到他耳边说:“汉口江汉路有个春和茶馆,你去找穿蓝布衫的王掌柜,他能帮你找到党组织。”
宋时轮拿起银元,手指碰到冰凉的银元,眼圈一下子热了。箱子底下,还有半块葱油饼,已经有点发霉了。
“这是前几天给你留的,忘了拿上来。” 董竹君说。
宋时轮攥紧银元,对她说:“董大姐,这份情我记着。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还你。”
董竹君摆摆手:“快赶路吧,别耽误了时辰。”
宋时轮带着皮箱离开了上海,坐船去了武汉。后来,他找到了党组织,重新穿上军装,上了战场。 董竹君还在上海经营她的餐馆。
1937 年,淞沪会战打响了。
董竹君的锦江小餐已经改成了锦江川菜馆,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夏衍、潘汉年这些人,经常在餐馆的 “特别间” 里开会。
董竹君每天都站在门口,要是看到生面孔,就赶紧给里面递暗号。
有一次,几个军统特务突然闯进来,要搜查。
董竹君拦在他们面前,指着一个包厢说:“里面是杜月笙先生的朋友,你们要查,先去问问杜先生。”
特务们一听 “杜月笙” 三个字,没敢再动,灰溜溜地走了。
那时候,宋时轮正在雁门关外打游击。天特别冷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上海那个小餐馆,想起董竹君递给他的银元 —— 那时候银元揣在怀里,暖乎乎的。
1947年,莱芜战役开打前,宋时轮缴获了两匹东洋战马。他让人把马送到上海,给董竹君带了句话:“这马能拉车,比黄包车省劲。”
1950 年,锦江已成为国宾馆。董竹君带他看饭店全景图时,他掏出朝鲜战场缴获的军刀:“当年的情,用这个记。”
董竹君笑着摆手:“钱不用还,饭店早是国家的了。” 他却念起那半块葱油饼,两人相视而笑。
1967 年董竹君入狱,五年后出狱,桌上躺着宋时轮托人送的豆瓣酱,字条写着:“豆瓣酱暖胃,革命人暖心。” 彼时他正被审查,这份情谊更显珍贵。
1991 年宋时轮临终前叮嘱家人:“别忘了董大姐,她是恩人。”
1997 年,九十多岁的董竹君在病床上翻看回忆录,里面写着:“1929 年帮的那个年轻人,身上有扛事的劲儿,我就知他能成大事。”
一场偶然相遇,结下跨世纪的情。动荡年代里,这样的温暖与坚守,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