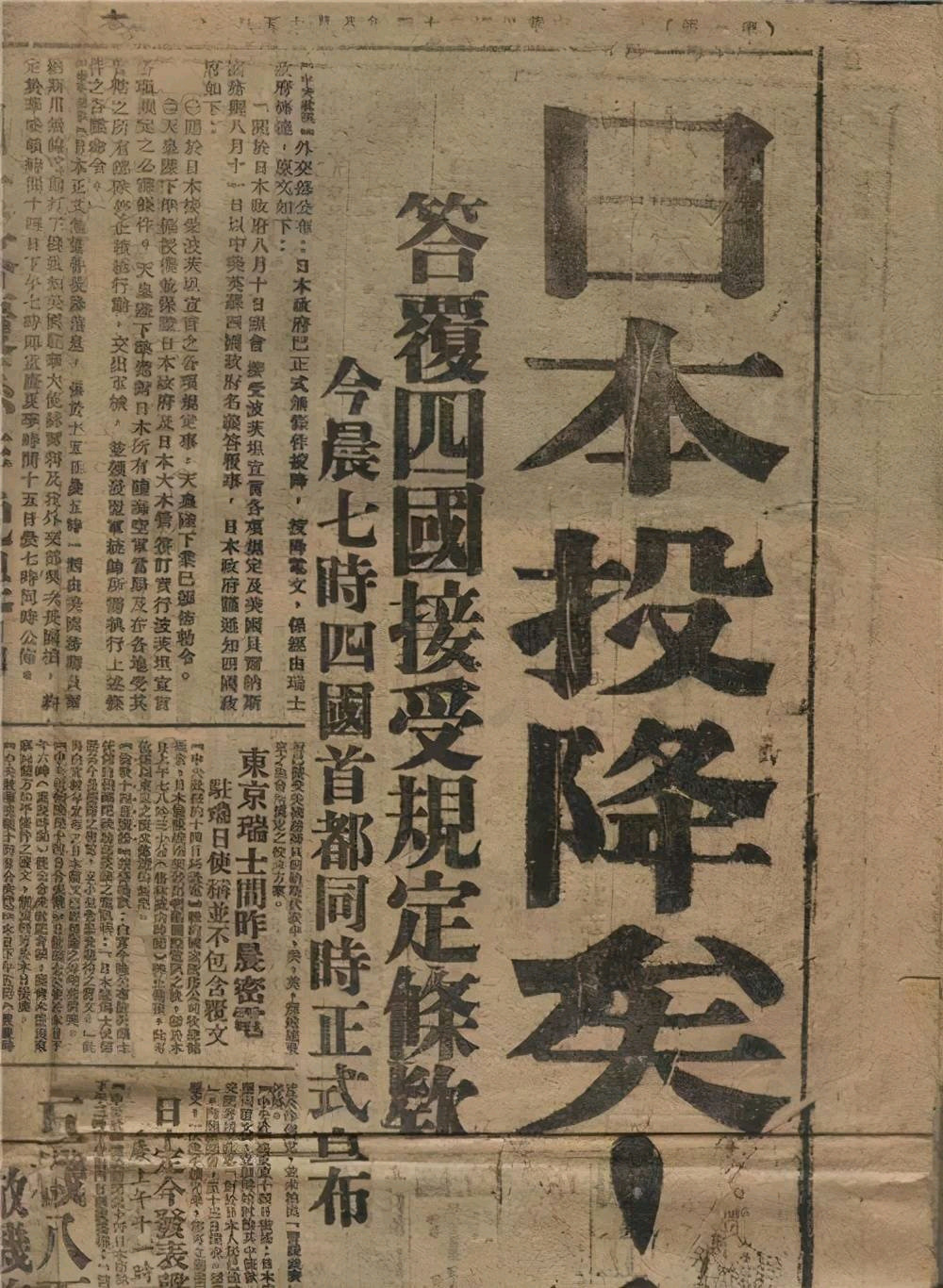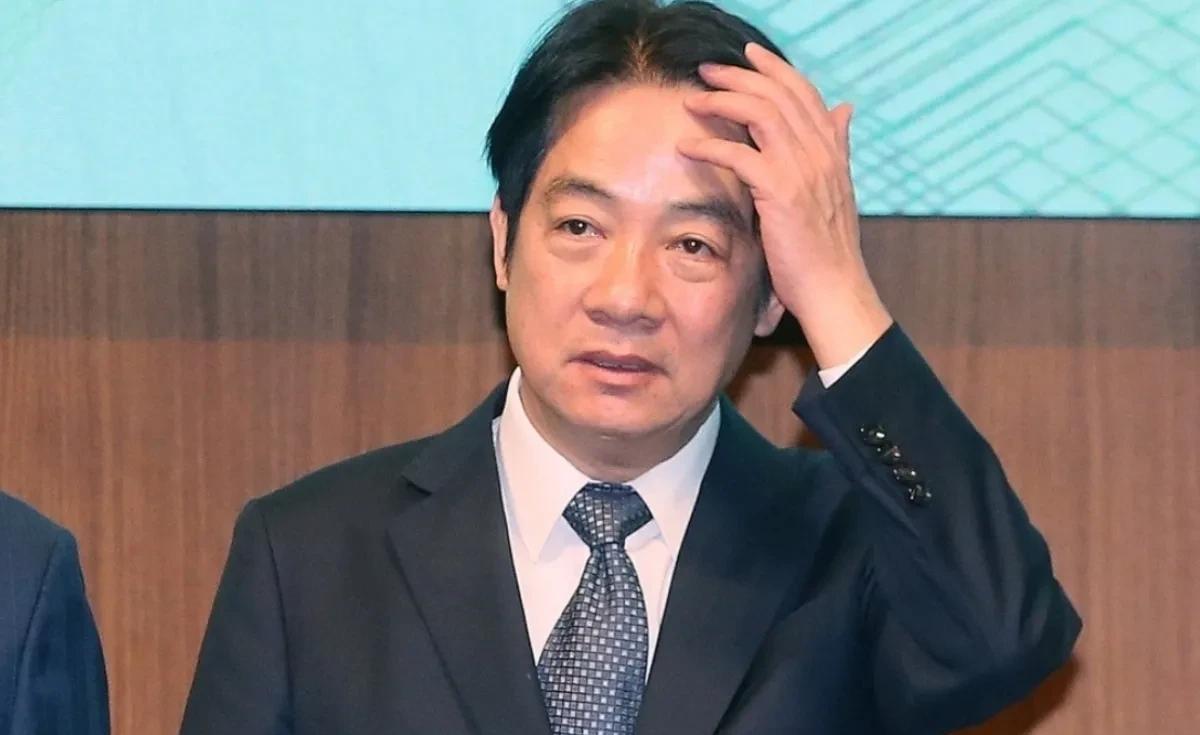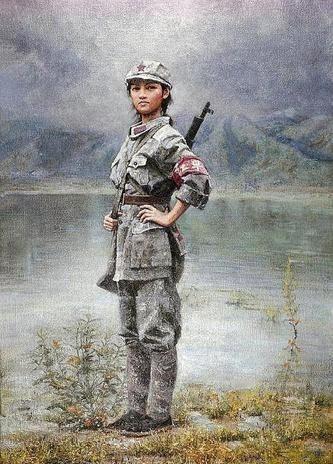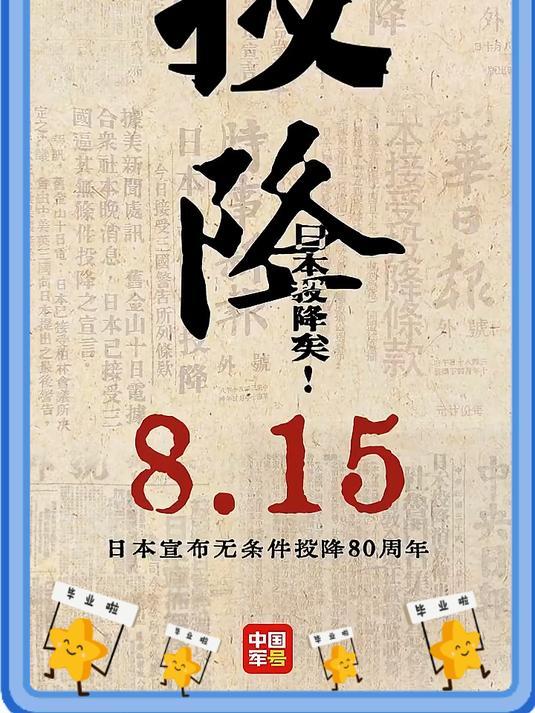古代战争,损失300精兵,基本上一个豪门家族就被打崩了,以后也再也难以翻身。 主要信源:(《水经注·卷三十二》;《三国志·吴书 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十》) 建安年间东吴营中,十五岁的少年凌统接过父亲的佩剑。 这剑很沉,剑鞘上满是刀痕。 他记得父亲凌操总说:“打仗就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砍下敌将首级就能换个出身。” 当年那个出身寒微的凌操,带着同样想用命搏功名的穷苦汉子们,在战场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些跟着凌操拼杀出来的老兵,全是余杭同乡或有过命交情的兄弟。 每场硬仗下来,队伍里总少几张熟悉的面孔,活下来的人便愈发如手足相依。 凌操战死后,三百老兄弟默默收拾刀甲,走到十五岁的凌统身后。 少年郎从此有了三百个不是父兄胜似父兄的依靠。 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老兵陪着凌统长大。 他们带小将军学排兵布阵,教他冲锋时怎么护住要害,打夜仗如何分辨风声里的马蹄。 行军途中总有人往凌统水囊里塞盐巴,说长力气。 十年光阴让这群汉子须发渐白,也让少年将军长成江东猛虎。 每次出征前,老部曲都要挨个帮凌统把铠甲绦带系紧,眼神像看着自家初上战场的儿子。 建安二十年逍遥津那场恶战来得突然。 曹操五万精兵压境,孙权带几个亲兵骑马逃命,把断后的活计丢给了凌统。 将军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带着三百人守在逍遥津桥头。 敌兵像潮水扑来,前排老卒最先扑进敌阵,刀劈断了就抱着敌人往河里滚。 桥面很快被血泡滑了脚,活着的人踩着袍泽的尸体往前冲。 打到日头偏西,河滩躺满了穿赤衣的兵。 最后几个老兵把凌统推上马背:“快走!将军家还得留后!” 少年郎背上插着三支箭,伏在马鞍上一路滴血。 他回头时,看见最老的那个百夫长抡着豁口的刀扑进敌群,像极了他小时候父亲冲锋的样子。 凌统醒来时躺在大帐里,医官正用烧红的刀子剜他背上腐肉。 痛得锥心刺骨,却盖不过心里头的空落落,三百张朝夕相对的脸全没了。 孙权的厚赏流水似的抬进营,官印绶带摆了一案。 凌统摸着崭新的将军印,手指头都在抖。 金银填不满心里的窟窿,他想听老兵再喊他一声“小主公”。 孙权给凌统指了条出路:征讨山越。 说是征讨,其实就是放他去招募新兵。 长江两岸的山越蛮子悍勇,正是最好的兵源。 队伍开进云雾缭绕的百越之地,凌统专挑穷山沟里饥一顿饱一顿的猎户,这些人给口饱饭就敢拼命。 一年多功夫,山里的营盘就扎下上万生力军。 新兵们见过他赤膊操练箭靶的样子,知道将军背上三条疤是为谁落的。 建安二十二年夏天阴雨连绵。 新兵营里闹起时疫,凌统日日往病号营钻。 军医急得跺脚:“将军莫再沾染秽气!”他照常给高烧的小兵擦身子,转头自己也躺倒了。 营里最好的郎中被快马请来,掀开帘子就摇头:“毒气攻心,救不回来了。” 那年秋天枫叶红透时,帅帐前新漆的“凌”字大旗被缓缓降下。 将军病亡的消息传回建业,孙权盯着战报怔了半晌,提笔在竹简上批注:其部曲皆归其子。 后来江东儿郎传唱:新丰渡口三百骨,金戈染血未凉时。 将军再未归故里。 他养出的虎狼之师,终究没能跟着他跨过长江。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赵露思银河酷🐟小人行为[汗]把赵露思后援会的几个官方🎺收回了。](http://image.uczzd.cn/8565074447865819336.gif?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