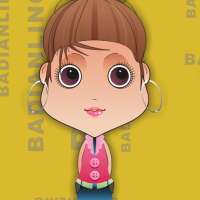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场。毛泽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这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 中南海的屋檐下,夜风时常带着一点书页翻动的声响,那不是哪个干部加班,也不是哪个翻译在校稿,而是毛泽东在看英文原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幕乍看有点难以想象,一个已经登上权力巅峰的领导人,还在一笔一划地在英文字母下面写中文注释,用的是铅笔,削得尖尖的,写几行擦几行。 不是兴致使然,更不是为了风雅,而是他觉得必须懂。 懂语言,才懂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世界不是什么模糊的概念,而是冷战的铁幕,是封锁,是制裁,是敌意。 毛泽东不愿让这堵墙只靠别人去撞,他决定自己动手,先学语言。 1954年的那个秋天,在广州,毛泽东叫来林克,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做我的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一岁,林克三十出头。 林克是他的外事秘书,本职是翻译、撰稿、处理涉外事务,没想到还要兼任“英语老师”。 可毛不是临时起意,他是真的要学。 他的日常安排密不透风,白天开会,晚上批文件,可只要有空隙,就拉着林克读英文。 睡前学、起床学、散步学、旅途中也学,甚至坐在从徐州飞南京的小飞机上,也要抽出一小时来练几段英文句子。 他学得不轻松。 湖南口音让发音成了难题,“night”总念成“light”,词尾的“s”发不出来,短音长音常常混在一起。 但他不在乎,一遍一遍跟着读,大声朗读,不会就问,错了就改。 他说别人笑没关系,笑就笑,他要学懂。 他学的不只是音和词,还有意思。他会问:“Nation为什么既是国家又是民族?”他想知道的是西方政治文化里,这些词是怎么被构造出来的,为什么一个词可以承载那么多概念。 对他来说,语言背后藏着逻辑,藏着制度,藏着对“世界是什么”的一种回答。 所以他不满足于看翻译本,英文版《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几乎页页有笔记。 注释一遍不够,就再看一遍再注一遍。 他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和别人炫耀,他是真的想通过语言去碰触思想的源头。 那些年,翻译的版本参差不齐,有的删节、有的表达不当,他觉得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林克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常常一边读一边感叹,“英文看起来枯燥一点,但清楚很多”。 他读的不只是经典,也读英文报刊。《纽约时报》他有时也翻几页,《北京周报》英文版他会让林克把难词一一注解。 有一回他特意要求找出一篇题为《Battle with Nature》的文章中的所有生词,准备细读一遍。 甚至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英文译本,他也亲自过问翻译进度,说要和林克“对读一遍”。 不是形式,是实打实地要吸收语言里那些冷静、准确、时常带刺的表达。他清楚,那些文字代表的是西方世界看中国的眼睛,他要自己看一看,看清楚。 他的英语学得越深,越显示出他对世界格局的认知也越具体。 他一面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一面又说:“你不了解美国,怎么和它斗争?”他对美的态度并不简单。 他说美国有坏的东西,也有好的东西。 坏的得斗争,好的要借鉴。他反对盲目排外,反对什么都打成“帝国主义腐朽文化”。 他甚至说,中央可以给各省第一书记配一个英文秘书。 听上去像玩笑,但他是认真的。 在他眼中,语言是一把钥匙,能开外面的门,也能照进里面的黑。 1958年在南宁,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那语气有点像训人,其实更像提醒。 他不是要别人都精通英语,而是要大家别怕外语。 他学,是想带个头。他觉得这不只是文化层面的事,更是政治层面的事。 学语言,就是了解世界,理解敌人,掌握主动。 而他理解语言的方式,也远不止于单词和语法。 有一次会见外宾,他笑着说:“两千多年前统一中国的,就是那个修长城的皇帝——秦始皇。中国(China)这个词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瓷器,一个是秦(Chin)。”听起来像开玩笑,其实他是在谈国家认同。 他在解构“China”这个词,把这个外来命名拉回到中国的历史里。 他是在借助语言去做一件宏大的事:重新解释“中国”的意义。他不满足于被称呼,更要参与命名。 语言在他那里,不止是用来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政治判断力的体现。 他很讨厌“万岁”这个词。 他说英文里翻译成“Long live”,意思是长寿。 年轻人喊还行,老人就别喊了。 他不是在讲语义学,而是在拆解权力语言,他觉得话语不该被滥用,哪怕是歌颂的话语。因为他明白,语言一旦失去分寸,就成了盲目的工具。他反对的,不是赞美,而是僵化。 毛泽东也不是一个用中文固守阵地的人。 他写给领导人的信里,偶尔会加一句“Good morning”,也会用“model”这个词去谈绘画教学。 他希望中国人能在思想上打开眼界,在语言上不再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