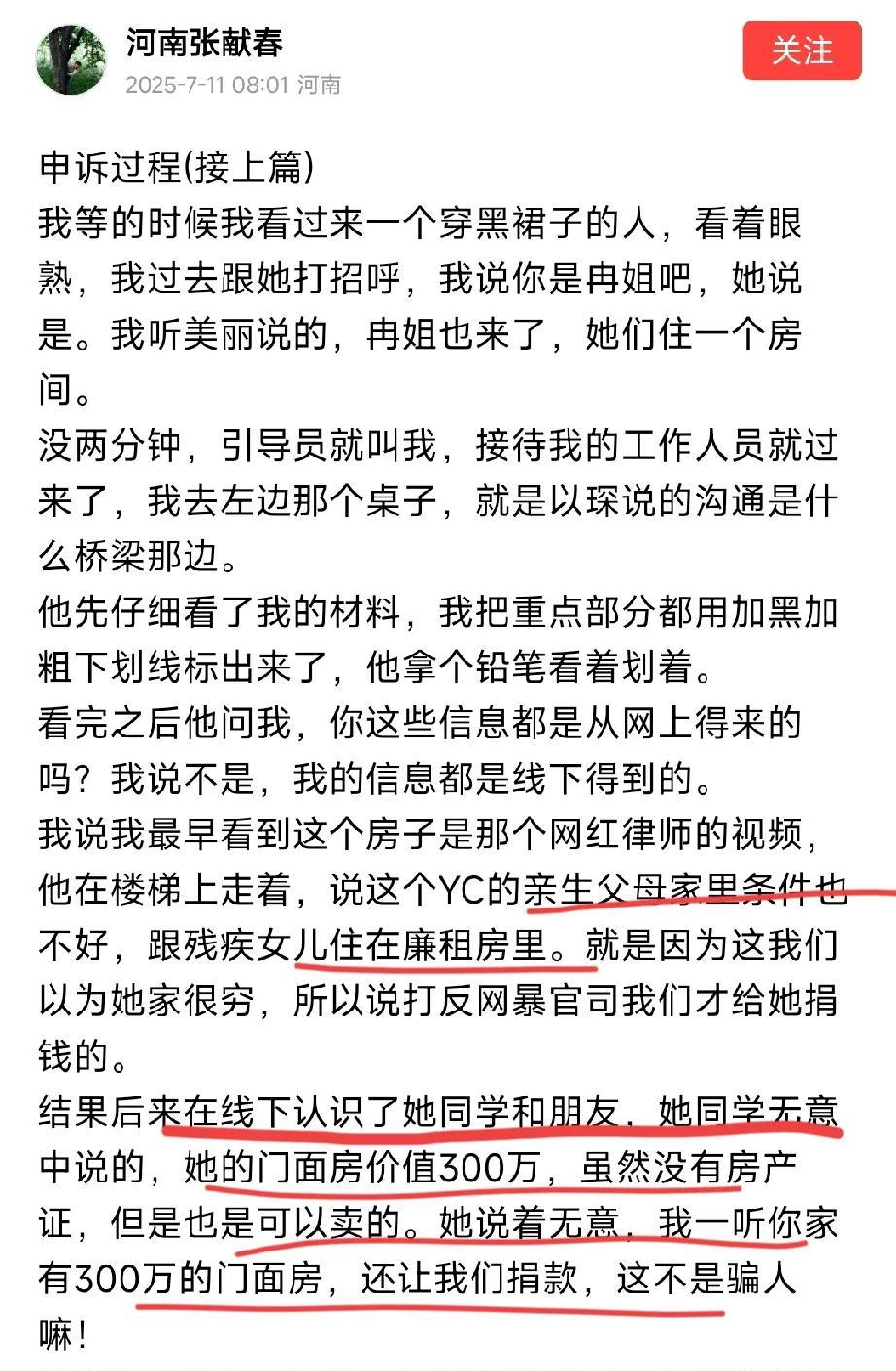父母离世那年,我才6岁!两个姑姑替我料理好后事后,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偏远的老家!
陈立松说
2025-07-11 16:32:30
父母离世那年,我才6岁!两个姑姑替我料理好后事后,把我一个人丢在了偏远的老家!
送葬队伍的唢呐声还没散尽,二姑塞给我个布包就转身上了拖拉机。车轮碾过院子里的青苔,留下两道深辙,像在我心上划了道口子。布包里是件打补丁的棉袄,还有五块皱巴巴的钱,我攥着钱追出去时,拖拉机已经拐过了村口的老槐树,扬起的尘土迷了我的眼。
老屋的木门没锁,风一吹就吱呀作响。我抱着爸妈的遗像缩在炕角,相框上的玻璃沾着没擦净的纸钱灰。夜里老鼠在梁上跑,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动,我吓得蒙住头,想起以前妈总说“老鼠怕人,你越凶它越不敢来”,可我怎么也喊不出声。
第二天醒来,灶台上只有个空水缸。我踩着小板凳去舀水,木瓢刚碰到水面就翻了,冰凉的水浇得我满裤脚都是。院墙外传来邻居张奶奶的咳嗽声,我扒着门缝看,她正往竹篮里装刚蒸的馒头,白雾腾腾的,混着麦香飘过来。
“小远,过来。”张奶奶突然朝我招手,皱纹里堆着笑。她把两个热馒头塞进我手里,掌心烫得我直缩手。“你姑姑托我照看你几天,”她擦着我嘴角的面渣,“说过阵子就来接你。”我咬着馒头点头,没敢说二姑临走时说“老家清静,让他自己待着”。
过了半个月,布包里的钱花光了。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去菜园拔青菜,却把葱当成了蒜苗。张奶奶看见我挎着空篮子回来,叹了口气,把她家腌的萝卜干往我兜里塞:“明早来我家喝稀粥,奶奶给你煮鸡蛋。”
有天夜里发烧,我裹着棉袄缩在炕头,浑身烫得像团火。迷糊中感觉有人摸我额头,睁开眼看见大姑站在炕边,头发上还沾着草屑。“跟我走。”她把我往背上一驮,脚步踉跄地往村外走。月光照在她鞋上,我才发现她裤脚磨破了,露出的脚踝冻得通红。
大姑家在镇上,三间小平房挤着她一家四口。表哥表姐总抢我的馒头,大姑看见就拍他们的手:“小远是客人。”可夜里我听见她跟姑父吵架,“这孩子吃穿不要钱?他两个姑姑就把担子扔给我?”姑父叹着气:“毕竟是亲侄子。”
转年春天,二姑突然来了,提着袋水果糖,说要接我去城里。大姑把我的旧棉袄往包里塞,塞着塞着就红了眼:“到了城里要听话,别给你二姑添麻烦。”我抱着大姑的腰不放,她手背上的冻疮裂开了,沾在我衣服上,像朵暗红的花。
二姑家住在单元楼,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表姐嫌我吃饭吧唧嘴,二姑就用筷子敲我的碗:“城里规矩多。”有次我偷喝了表姐的牛奶,她哭着闹着要我赔,二姑把我关进阳台,“反思好了再出来”。我扒着防盗网看楼下,想起张奶奶家的鸡窝,还有大姑蒸的红薯,眼泪掉在水泥地上,砸出小小的湿痕。
十岁那年暑假,我偷跑回了老家。老屋的锁锈得打不开,张奶奶听见动静出来,手里还拄着拐杖——她前年摔断了腿。“你姑姑找你快找疯了,”她拉我进屋,端出碗荷包蛋,“你大姑去年生了场病,总念叨你长高了没。”
正说着,大姑和二姑一前一后进来,看见我都愣住了。二姑上来就要打我,被大姑拦住:“孩子想家了。”那天她们没吵,坐在张奶奶家的小板凳上,商量着把我送回镇上读书,费用三家分摊。我啃着张奶奶给的玉米,听见二姑小声说:“其实我不是不想养,是怕城里开销大,委屈了孩子。”
后来我在大姑家长到十六岁,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开学那天,两个姑姑都来送我。二姑塞给我个红包,“别学你表哥谈恋爱,好好读书”;大姑往我包里塞煮鸡蛋,“食堂饭不好就回来看奶奶”。她们站在站台挥手,阳光照在她们头上,我才发现大姑有了白头发,二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
去年带妻儿回老家,张奶奶已经不在了。老屋重新翻修过,大姑说这是她和二姑凑钱盖的,“等你回来住”。二姑给我儿子糖吃,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撒了把芝麻,“你小时候抢糖吃的样子,跟这小子一模一样”。
夜里躺在老屋的炕上,妻儿睡在身边,鼻息均匀。窗外的虫鸣和当年一样响,我摸着墙上爸妈的遗像,突然明白,有些爱藏在打骂里,有些疼裹在沉默中。就像这老屋的墙,看着斑驳,却在风雨里,替我撑了这么多年。
0
阅读: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