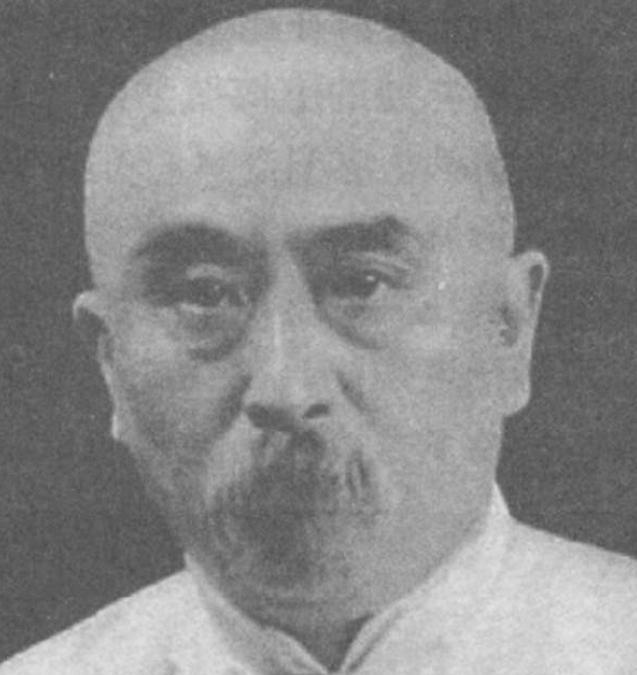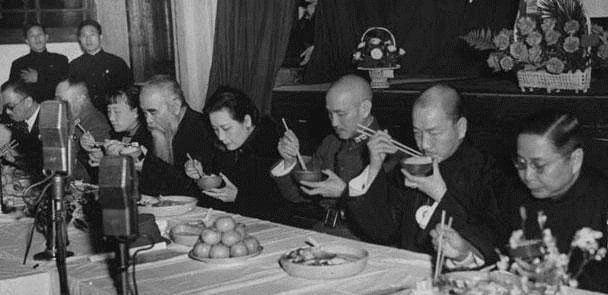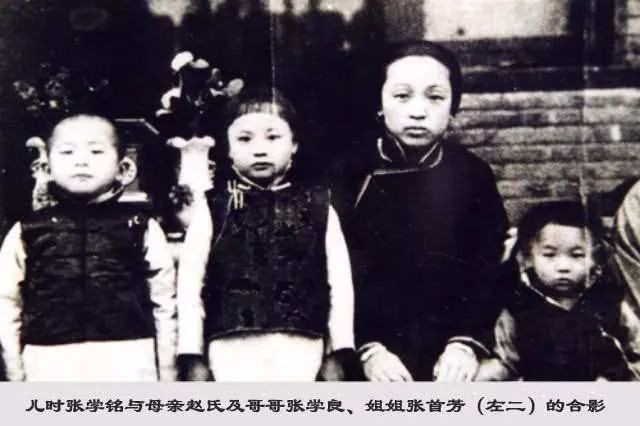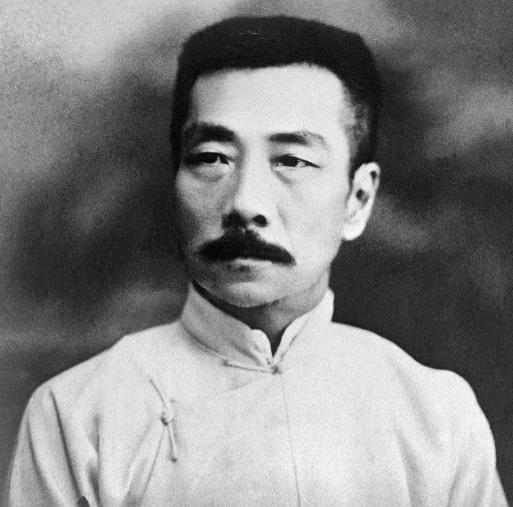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1910年,一个清冷的冬夜,陆士谔守着他那间小药铺,一边熬药,一边听铺子前租书的伙计跟人闲聊,说起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私奔,哪个巡捕房的头子收了黑钱。这样的事他听得多了,没什么稀奇。可这天,一个梦,扰得他整宿没睡。 梦里,他走进一个奇异的地方,街上满是灯火,楼高如云,有人坐着火车在空中穿行,还有人竟然飞去了天上。他在人群中穿梭,看见孩子在学校里读书,女子也能做生意,男人不再留辫子,也没人再讲满语。他问人这是哪年,那人笑道:“这不是新中国吗?”梦一醒,他脑袋发热,提笔就写,把这场荒唐的梦一字不落记了下来。 几天后,一本名叫《新中国》的书就从他的笔下诞生了。 写书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说到底不过是因为穷。陆士谔从小读书,祖上是读书人,家中也藏着不少书。可到他这代,赶上天下动荡,家里早没了读书的本钱。他作为长子,只能早早挑起生活的担子。小时候他也读圣贤书,想着有朝一日能中个举人,光宗耀祖。可连年战乱,考场荒废,他连个秀才都没混上。 为了活下去,他做过不少事:街头卖艺、码头搬货、茶馆跑堂。他也曾敲着铜锣在街头吆喝草药,熬得一身铜锈味,只为换点碎银。可这一身技艺,他爹不认,骂他败坏门风。实在没法,他才转去学医。师傅是江苏一带有点名气的郎中,他就跟着跑腿、煎药、看诊,几年下来,倒也能独当一面。 医术学成,他回到上海,在闸北开了个药铺。药铺不大,养活自己还行,想供弟弟上学就紧巴巴了。巧的是,那年他两个弟弟考上了官费留学,一个去了东京,一个去了伦敦,常来信讲些外国新奇事儿——自来水、电报、火车,还有叫世博会的大展览,什么东西都有,连中国也派人去看热闹。他听着听着,脑子活了。 药铺里一半是药柜,另一半干脆支了书架,开起了租书铺。自己也写点小说贴补家用,写江湖义气、奇闻异事、才子佳人,一写就停不下来。两年时间,他写了三十多本,快马加鞭,哪种好卖写哪种。他也知道,读者不爱看大道理,就爱看离奇事。 可《新中国》却不一样。这书不写恩怨,不讲情爱,只是一个梦境。梦里没有洋人横行的租界,也没有兵匪四起的惨状,有的是高铁、电灯、飞船,还有人人讲国语,孩子免费上学,百姓安居乐业。 书印出来后他拿去找人看,有人翻了几页,说他疯癫,有人则笑他吃饱了撑的,鲁迅也看过,丢下两字:“胡说。”可他不气,他说:“我写的不是现在,是百年后的事。” 那些年,他的药铺一直开着,生意时好时坏。他不止一次幻想,若真能活到那梦里,亲眼看看那高楼大厦、灯火通明的地方该多好。他弟弟从英国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画着伦敦的万国博览会,他仔细端详,觉得自己梦里的城市比这还要气派。 他写书不为青史留名,只求糊口。可后来清朝灭了,上海闹革命,药铺被抢了两回,他干脆关门,埋头在家写《月宫旅行记》,让中国人登上了月亮。他的文字无人赏识,书也卖不动了。他照旧写,只是读者越来越少,租书铺也关了。直到他病重,临终前还在改那本《新中国》,只说:“再加几句,好让梦更圆满。” 几十年后,那个城市终于如他笔下一般出现。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城市灯光璀璨,人山人海,地铁穿城而过,高楼接天连地。人们拍照、录像,却无人记起那百年前有个姓陆的医生,梦中过了一趟未来。 后来有人在旧书摊翻出一本泛黄的《新中国》,封面印着“陆士谔”三字。再往后,陆士谔的故事被人一层层刨出来,说他预言未来。可其实,他从未想过预言,只是想象一个不那么苦的中国,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