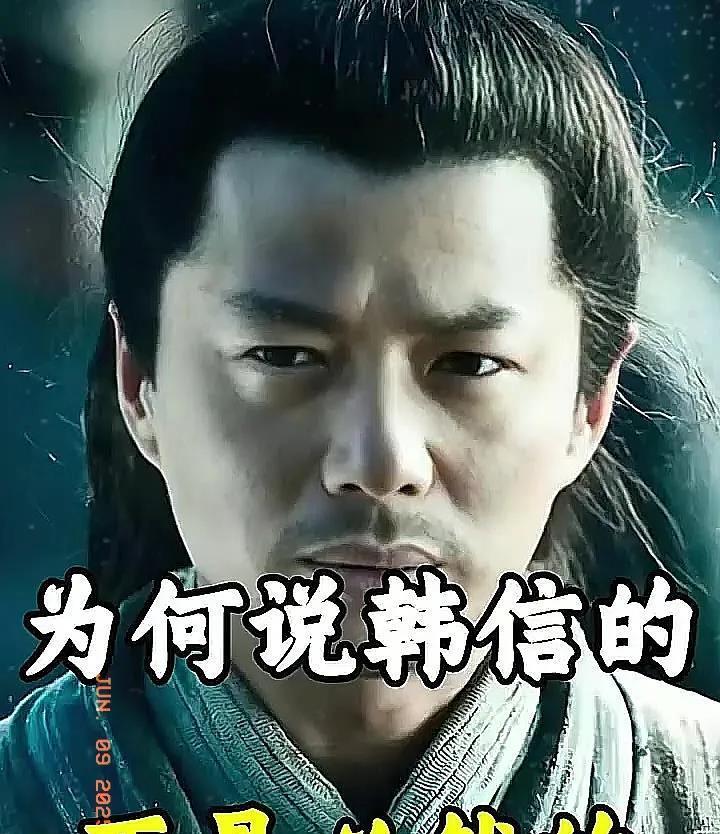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请求市长陈毅,给她一个房子。陈毅当即下令,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不料,她竟带着几个年轻男子一同入住。
这年的上海,此时这里的街头上还留着炮火熏黑的痕迹,陈毅市长办公室的台历才刚翻到七月。
一位身形瘦削的妇女带着文件袋站在走廊里,她脚上的布鞋沾着泥点,粗布衣袖磨得发亮,唯有挺直的腰板依稀能看出当年的风采。
凌维诚握紧丈夫谢晋元的烈士证书,身后跟着几位头发花白的男人,他们布满老茧的手紧张地攥着褪色的军帽。
时光倒转至1937年深秋,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像座孤岛矗立在硝烟里,谢晋元带着四百二十名士兵死守阵地,仓库水泥墙上密密麻麻嵌着弹片,楼顶用竹竿挑着浸血的衬衣当作军旗。
这些士兵被报纸称为"八百壮士"时,其实每个人兜里都揣着遗书,有位广东籍小战士在墙砖上刻字:若我死了,烦请长官告诉我阿妈,她煲的西洋菜猪骨汤最靓。
谢晋元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总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军人护国就像老母鸡抱窝,得拿命暖着。"
淞沪会战撤退命令下来时,他主动请缨断后,当时日军在仓库周围架起三十七门火炮,租界里的外国记者用望远镜看得直咂舌:"这些中国人连棺材钱都省了。"
可谁都没想到,他们硬是扛了四天四夜,打退敌人十余次冲锋。
捷报传遍全国时,凌维诚正在广东老家种番薯,她收到丈夫托人捎来的家书,信纸被雨水洇湿半边,最后几行字勉强能认:"若得凯旋,当与卿共赏龙华桃花;若有万一,盼卿如劲草立于风霜。"
她把信纸折成方胜塞进贴身的荷包,荷包上绣的并蒂莲渐渐被汗水浸得褪色。
噩耗来得猝不及防,1941年清明节刚过,租界里卖报童扯着嗓子喊:"孤军营谢团长遇害!"
原来汪伪政权多次劝降不成,买通四人在晨操时下了毒手,谢晋元倒下的那块操场,晚上还被士兵们用鹅卵石拼出"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挤上开往上海的运煤船时,怀里揣着国民政府发的抚恤金支票。
可到了银行才晓得,那张盖着红章子的纸片早废了,通货膨胀让金圆券比草纸还不值钱。
她在码头帮人缝补衣服,有次给洋行职员补西装,发现内袋里掉出半块压缩饼干,那是丈夫生前部队的军粮。
最苦的时候,她在菜市场捡菜叶子,听见卖鱼档的收音机放《义勇军进行曲》,卖鱼佬跟着哼唱,鱼鳞粘在皱巴巴的胶鞋上。
凌维诚蹲在地上抹眼泪,忽然有人往她竹篮里塞了条小黄鱼,抬头看见个缺了右手的男人慌慌张张跑开,后来才知道是孤军营的老兵,在码头当搬运工摔残了胳膊。
这些散落上海滩的老兵过得比乞丐强不了多少,有个山西老兵在弄堂口摆修鞋摊,工具箱里藏着豁口的刺刀;广东籍的机枪手在澡堂给人搓背,后背留着碗口大的炮弹疤。
凌维诚把自家阁楼腾出来,六七个老兵打地铺睡,半夜咳嗽声此起彼伏,都是当年在战壕里落下的肺病。
1946年夏天特别闷热,凌维诚带着老兵们在郊区开荒,他们在虹桥机场附近垦出二十亩菜地,种出来的卷心菜特别水灵。
有次往国际饭店送菜,厨房大师傅掂着紫皮茄子夸:"这菜精神,跟你们种的?"凌维诚笑着指身后挑担的老兵:"这些爷叔当年拿枪的手,如今使锄头照样威风。"
好日子没过两年,菜地被强征建高尔夫球场,老兵们抱着冬瓜茄子不肯走,管事的掏出手枪往天上放。
凌维诚拦在推土机前头,风吹起她两鬓白发:"要碾就从我身上碾过去,正好找我们团长报道。"
最后还是警察局来了人,看见老兵们胸前的抗战勋章,跺着脚骂征地的人:"这些可是四行仓库的兵!"
转机出现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个礼拜,陈毅市长收到封联名信,信纸用的是泛黄的《申报》,空白处挤满歪歪扭扭的签名,还有十几个血红的手印。
工作人员到吴淞路实地查看时,凌维诚正在天井里晒萝卜干,竹匾旁边堆着修补过的胶鞋,墙上挂着谢晋元穿军装的照片,相框边别着朵褪色的绸布红花。
政府很快拨下吴淞路466号三层小楼,搬家那天,老兵们把谢晋元的行军床摆在客厅。
凌维诚用旧军装改了几床被褥,晚上听见楼下有动静,举着煤油灯查看,发现独臂的老兵在擦那架生锈的机枪零件。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金属部件上,泛着和当年四行仓库墙头军旗同样的冷光。
往后的岁月里,这栋小楼成了老兵们的驿站,山东来的要回老家娶媳妇,凌维诚给他包上两斤大白兔奶糖;湖南籍的得了痨病,她天天熬川贝雪梨汤。
最年长的老兵弥留之际,紧紧攥着凌维诚的手念叨:"等见了团长,我给他报告,说太太把兄弟们都照顾得妥妥帖帖。"
1983年清明,凌维诚最后一次来到四行仓库,加固后的墙体嵌着八百多枚弹头,她颤巍巍的手指抚过那些凸起的金属,忽然在墙角发现几个模糊的刻痕。
管理员打着手电筒照过去,斑驳的水泥面上显出一行小字:"谢团长,下辈子还跟您打鬼子。"
凌维诚把额头抵在冰冷的墙面上,远处苏州河汽笛长鸣,恍如当年八百壮士的冲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