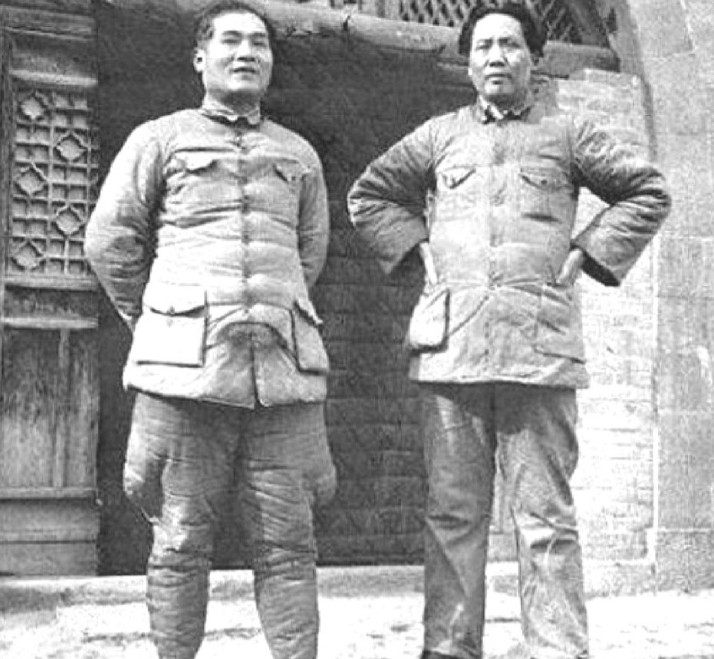1904年,通房丫李氏,站着侍奉丈夫与正妻长达33年。这日,她正在盛饭。谁知,管家突然冲进来高喊了一句,她手一歪,啪地一声碗摔落地面碎了一地。正妻刚打算开口斥责,丈夫却开怀大笑:“坐下,一同用膳!” 1904年,对李氏来说是个关键年份。那是清朝末年,她已经在谭府熬了33年,从12岁被卖进来当丫鬟,到15岁做了谭钟麟的通房丫头,再到这天,她47岁了。谭府是湖南茶陵的大户人家,规矩多得让人喘不过气。丫鬟得低眉顺眼,妾室地位也不高,李氏夹在中间,既要干活又要伺候人,日子过得像根紧绷的弦。她生了儿子谭延闿,1880年的事,可母子俩在府里没啥地位,正妻陈氏看不上她,下人也不待见她。她只能咬牙忍着,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 谭延闿小时候就聪明,李氏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买书,晚上教他认字。她没啥文化,但知道读书能改变命。她常跟儿子说,只要他出息了,她这辈子就算没白活。谭延闿没辜负她,1904年考中进士,成了翰林院编修。那天管家跑进来喊的就是这个消息,李氏一激动,手里的碗没拿稳,摔碎了。按理说,这种事在谭府是大错,陈氏肯定得发火,可谭钟麟却乐了,说让她坐下一起吃。这在当时可不常见,妾室哪有资格上桌?但谭延闿中进士,家里脸上有光,谭钟麟心情好,才给了李氏这点恩惠。 李氏12岁进谭府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父母没办法才卖了她。她干活麻利,长得也清秀,谭钟麟看上了,收她做了通房丫头。那年她15岁,年纪小,啥也不懂,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了他。谭府等级森严,正妻陈氏管家,几个姨娘争宠,李氏地位最低,连个正式名分都没有。她得站着伺候吃饭,得听陈氏使唤,稍微出错就挨罚。生了谭延闿后,她日子更不好过,陈氏不高兴,觉得她抢了风头,背地里没少给她脸色看。李氏不敢吭声,只能低头做事,把委屈咽下去。 谭延闿长大后,慢慢懂事了。他看母亲受苦,心里憋着一股劲,发誓要让她过上好日子。1904年他中进士,算是给了李氏一点盼头。那天摔碗的事,虽然谭钟麟没追究,还让她上桌,可这并没彻底改变她的处境。陈氏还是那个态度,下人照样阴阳怪气。谭钟麟在世时,偶尔对李氏好点,但也就是表面功夫,他毕竟是大老爷,家里的事听正妻的。1905年谭钟麟死了,李氏处境更糟,陈氏彻底翻脸,族里人也不把她当回事。她还是那个通房丫头,靠着儿子在外面的名声,才勉强撑着。 谭延闿中进士后,仕途挺顺,先在翰林院,后来做到湖南都督,再后来还当过国民政府主席。他孝顺,每次升官都惦记着母亲,寄钱寄东西回来。可李氏身子骨早熬坏了,1916年她病倒了,谭延闿在外忙,赶回来时她已经没了。他后悔得不行,觉得自己没多陪陪她。葬礼上,族里按规矩不让李氏的棺材走正门,说她是妾,没资格。谭延闿不干了,当场跟族人拍桌子,说母亲受了一辈子苦,死了还得受辱,他咽不下这口气。族人拗不过他,最后让步,李氏的棺材从正门出了。 李氏这33年,真不容易。她从一个穷丫头,到谭府的丫鬟,再到通房丫头,最后靠儿子争了口气。清末那会儿,女人命苦,尤其是妾室,没地位没权利,活着全看别人脸色。李氏没啥大本事,但她硬是靠着韧劲,把谭延闿拉扯大。她不图自己享福,就想儿子好,这份心让人没法不感动。谭延闿为她争正门出殡,也不光是孝顺,更是对老规矩的一种反抗。那时候讲究门第,庶出的人抬不起头,他这么做,是想告诉所有人,他娘不比谁差。 回过头看1904年那顿饭,李氏坐下来时,心里肯定五味杂陈。33年的苦,总算有了点回报,可这回报也太短暂了。她后来的日子,还是苦多乐少。谭钟麟的宽容,只是因为儿子出息了,不是真心看得起她。陈氏那边的冷眼,也没因为这一顿饭就少半分。李氏的故事,跟清末好多女人差不多,命不由己,靠自己熬,靠子女争气。她没啥惊天动地的事迹,就是普普通通地活着,但这份普通里,有种让人敬佩的劲头。 谭氏家族在湖南算得上望族,谭钟麟当过大官,家里规矩多。李氏进门时,谭府正红火,可她没享到福。清末社会就这样,女人地位低,妾室更惨,连葬礼都得按身份来。李氏能熬到儿子中进士,已经是奇迹了。谭延闿后来名气大,书法也好,政绩也不错,但他最让人记住的,还是对母亲的那份心。他用自己的地位,给了李氏最后的尊严,这比啥官衔都值钱。 李氏这辈子,其实挺接地气的。她没啥浪漫的光环,就是个苦命的女人,靠着一双手和一颗心,撑起了儿子的前程。1904年摔碗那一下,是她33年里少有的高光时刻,可这高光,也透着心酸。她不是英雄,但她的坚持,比英雄还让人动容。清末那会儿,像她这样的女人多了去了,默默受着,最后留下的,就是这么点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