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陈独秀这辈子活得轰轰烈烈,临了躺在江津的病床上,最放心不下两件事。
那就是跟自己过了12年的媳妇潘兰珍,另外一个则是跟名声有关的那笔钱。
别看现在说起此事来轻飘飘的,但那个年月里,这两件事可都是要命的大事。
他的婚姻真跟影视剧里演的一样曲折,生在大清朝光绪年间,家里早早给定了亲事。
十八岁那年娶了安徽老家的高晓岚,这姑娘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裹着小脚识不得几个字。
陈独秀憋着股子劲要出去闯荡,成亲没两年就跑到日本留学去了,东洋的新鲜空气把他脑子吹开了窍,回来就跟家里摊牌要离婚。
那时候离婚可是天大的丑事,气得他继母抄起擀面杖追着打,可到底没拦住这个倔脾气的读书人。
三十岁出头的陈独秀遇上了真命天女高君曼,她是他原配夫人的亲妹妹,按辈分该叫小姨子。
可俩人偏偏看对了眼,一个写文章骂旧礼教,一个跟着要妇女解放,他俩一起到杭州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此事。
但话说回来,高君曼也确实不简单,陪着陈独秀办《新青年》,跟着他南征北战,还曾站过岗放过哨。
可惜日子久了,两口子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各走各路。
1930年在上海滩,50岁的陈独秀碰上了22岁的纺织女工潘兰珍,这姑娘命苦,爹妈死得早,在纱厂干活还老受工头欺负。
有天她在弄堂口看见个穿长衫的老先生帮人写信,说话斯斯文文的,跟那些满嘴荤话的粗人不一样。
这老先生就是乔装打扮的陈独秀,正被悬赏通缉,可潘兰珍哪知道这些,只觉得这先生待人和气,慢慢就生出情意来。
要说潘兰珍对他那真是死心塌地,1932年他被抓,报纸上登出照片她才知道,跟自己过日子的"李先生"的真实身份。
没曾想得知此事后,她竟二话不说辞了工,跑到南京城外租间破屋子,三天两头去里面送饭送衣。
监狱长都看不下去了,劝她:"你这没名没分的图个啥?"潘兰珍就一句话:"我男人在里面受苦,我就要守着。"
等他出来头件事就是给潘兰珍补办婚礼,而这时候的他穷得叮当响,高官厚禄也不要,接他也不去,带着媳妇跑到四川江津种地糊口。
教育部的人倒是机灵,听说陈独秀写了本《小学识字教本》,特意送来两万块钱稿费,条件是让专家帮着改书稿。
他气得拍桌子:"我写的书,谁都别想动一个字!"这笔钱到死都没动过。
1942年春天,他的胃病拖成了胃癌,临终前他把潘兰珍叫到床前交代后事:"我走后你要找个正经人家改嫁,别守着虚名过苦日子,还有就是教育部的钱万万动不得,我这辈子不欠人情,死了也不能让人戳脊梁骨。"潘兰珍趴在床头哭成泪人,咬着牙点头应承。
他走后,那笔钱原封不动退了回去,潘兰珍在重庆找了份农场的工作,白天给人养鸡种菜,晚上守着丈夫留下的书稿过日子。
后来有人给她说媒,她总说:"我这辈子就认准一个陈独秀。"即使好心给她安排工作,她也摆摆手:"我有手有脚能干活,不占公家便宜。"
1969年潘兰珍病逝上海,临终前把陈独秀的手稿交给国家,自己连件像样的陪葬品都没留。
潘兰珍这个没文化的纺织女工,倒真把文化人的骨气学了个十成十,两口子穷归穷,可那份硬气劲儿,到现在说起来还让人竖大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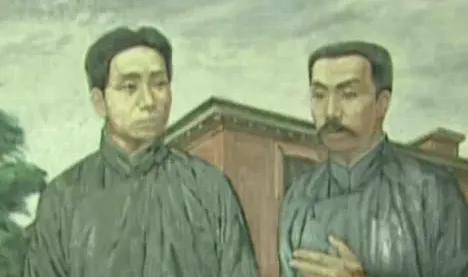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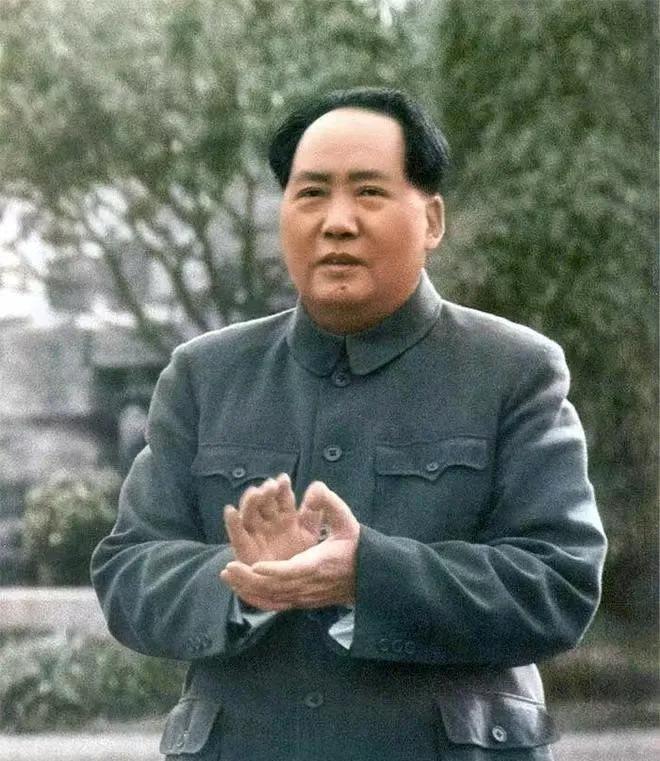

大海
这就是做人的根本和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