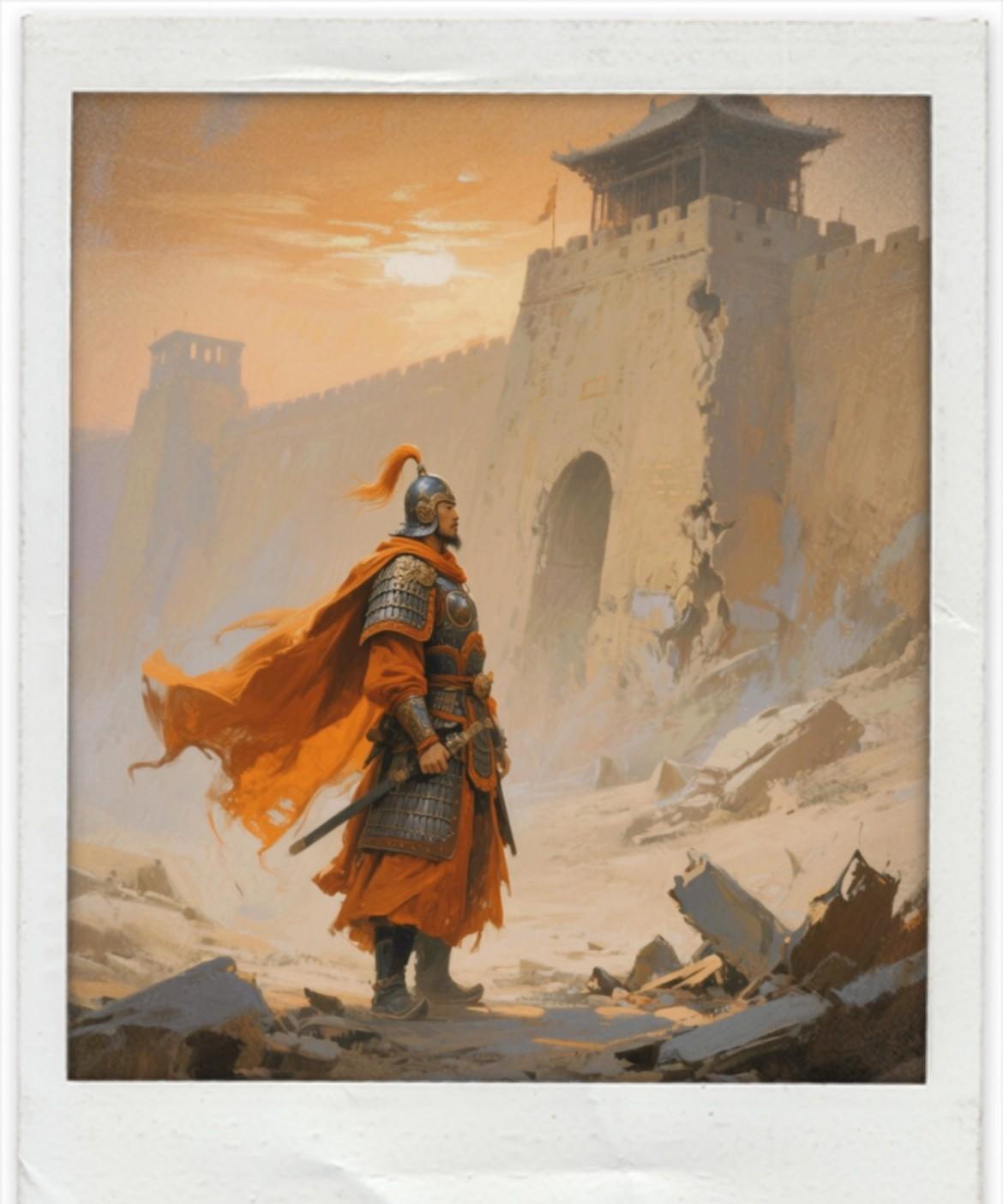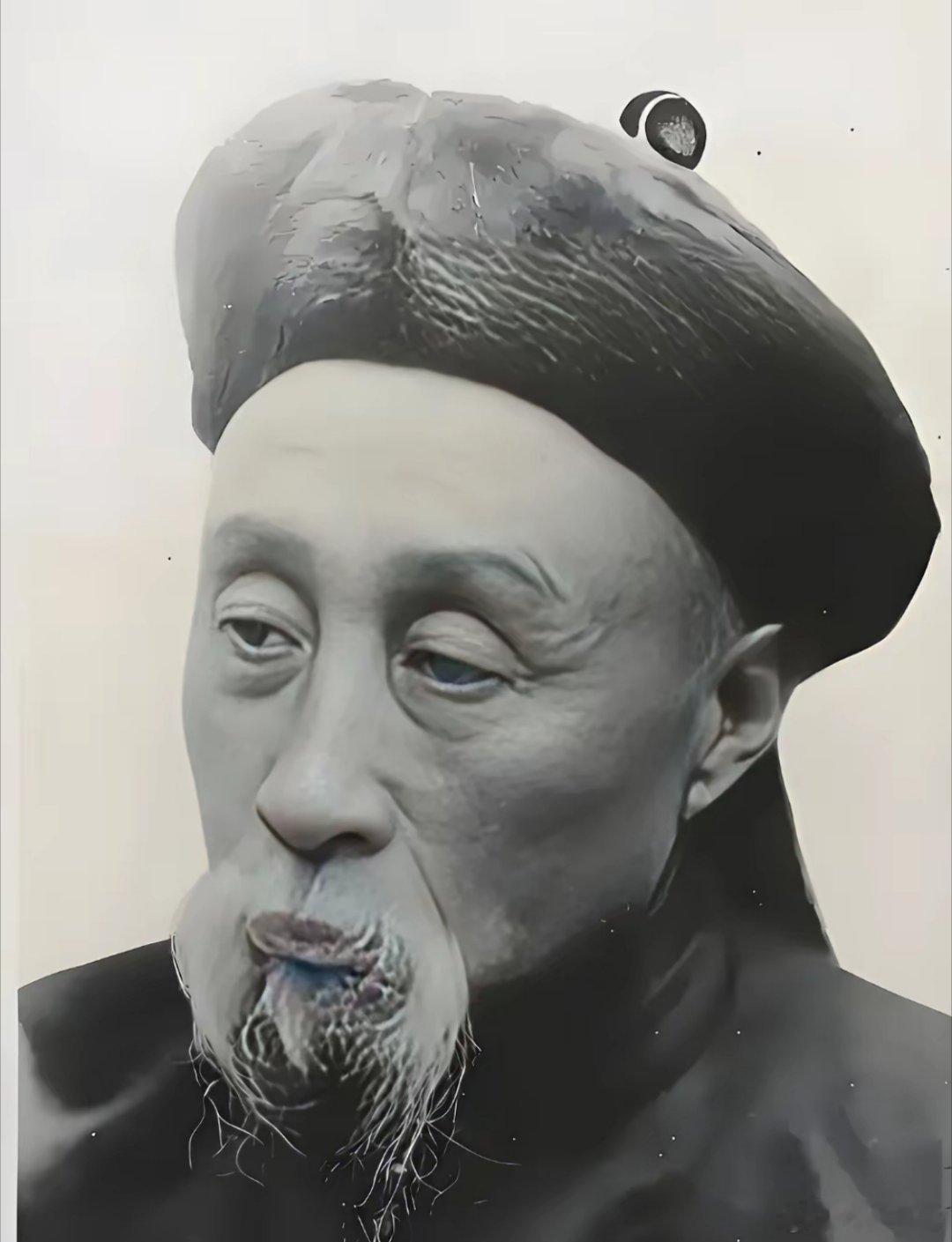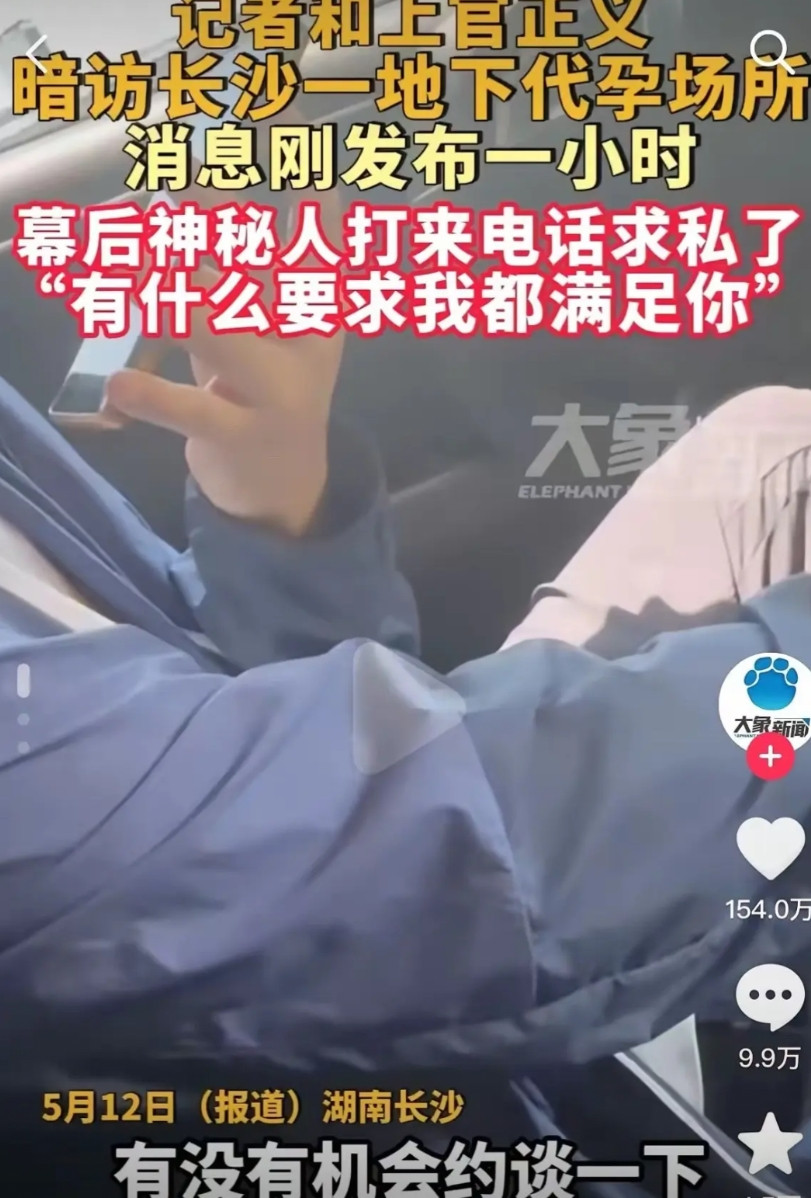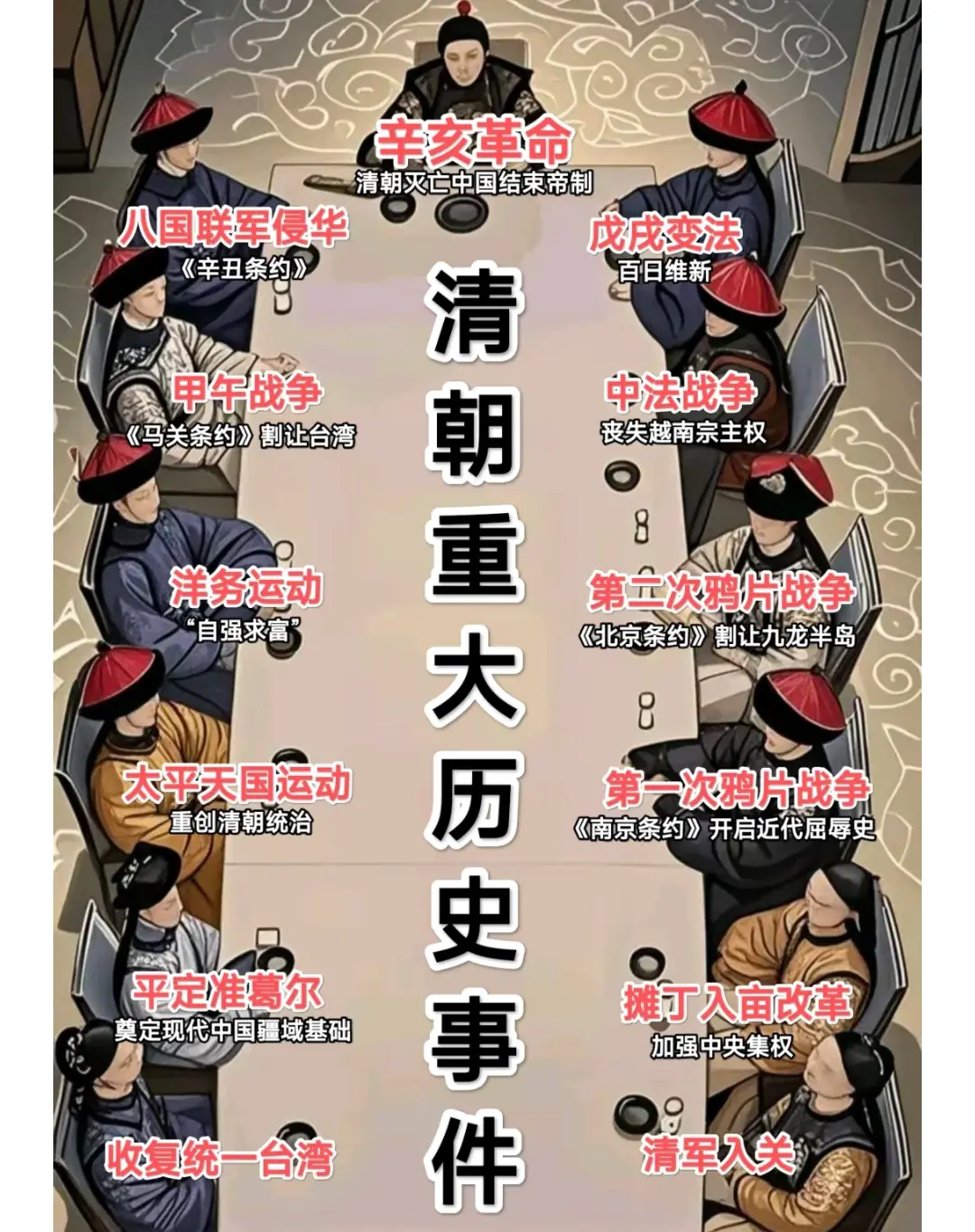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1936年10月20日,五十六岁的文坛巨匠鲁迅在病榻上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用笔杆子唤醒国民的灵魂战士,终究没能逃过病魔的掌心。 消息传到八道湾胡同时,周作人正在书房擦拭收藏的碑帖,握惯了毛笔的手微微一抖,青瓷茶盏在红木案几上磕出清脆的响声。 要说周家这两兄弟,当年可是绍兴城里出了名的才子。 1901年的春天,二十岁的鲁迅带着十八岁的周作人赴南京求学,兄弟俩挤在江南水师学堂的木板床上,裹着同一条薄被讨论《天演论》。 那些年鲁迅每月领了官费银子,总要先往弟弟口袋里塞几个铜板,生怕他在外头吃不饱饭。 1919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置办宅院时,特意选了三十多间房的四合院,为的就是让母亲和两个弟弟全家都能住得舒坦。 谁承想这栋凝聚着手足深情的宅子,最后竟成了割裂亲情的刀。 搬进新居头两年还算和睦,鲁迅把管家权交给弟媳羽太信子,自己每月把三百多大洋的教授薪水分文不少交到她手上。 这个东瀛女子穿着素色和服跪坐在榻榻米上接钱时总是低眉顺眼,转头就带着佣人直奔东安市场,丝绸要扯杭州织锦,点心要买稻香村头炉,连孩子玩的拨浪鼓都得挑珐琅彩的。 鲁迅抽着廉价的"哈德门"香烟写《阿Q正传》时,常听见隔壁院子传来留声机里梅兰芳的唱腔——那是周作人花六十块大洋新添的西洋玩意儿。 1923年7月19日的黄昏闷热得让人心慌,周作人攥着封信闯进大哥书房,薄薄的信笺上潦草写着"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 鲁迅捏着信纸追到月亮门,却见弟弟甩着灰布长衫的袖子疾步离去,竹帘子哗啦啦响得像骤雨打在青瓦上。 后来听帮佣的老妈子嚼舌根,才知道信子跟丈夫哭诉大哥偷看她洗澡。这没影的事像颗生锈的钉子,把兄弟俩二十多年的情分扎得千疮百孔。 搬离八道湾那天,鲁迅只带走了母亲和几箱书。朱安站在垂花门下绞着帕子,这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自打1906年被花轿抬进周家,就再没出过绍兴老宅的门。 新婚第四天丈夫就东渡日本,留她在青砖地上数了二十年晨昏。老太太心疼儿媳,总让厨娘单给她炖碗鸡蛋羹,可再嫩的蛋羹也补不上心里那个窟窿。 直到1927年鲁迅在广州遇见许广平,朱安还在北平守着冷灶台,给来客倒茶时总要先擦三遍八仙桌。 要说许广平这姑娘也是奇女子,放着广州小姐的优渥日子不过,偏要跟着大自己十七岁的先生颠沛流离。 1929年海婴出生时,鲁迅抱着襁褓在虹口寓所转圈圈,窗台上摆着许广平熬的鱼片粥。 这其乐融融的画面传到北平,朱安在佛堂里添了炷香,跟老妈子念叨:"大先生总算有后了。"她这辈子最体面的衣裳,还是许广平后来寄来的阴丹士林布旗袍。 周作人这边倒是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琉璃厂的掌柜们都知道八道湾周宅的太太出手阔绰。信子把西厢房改成日式茶室,榻榻米上摆着从东京运来的漆器食盒。 周作人翻译《枕草子》赚的稿费,刚够给太太买对翡翠耳坠。 1932年元旦,兄弟俩在中山公园茶室撞个正着,周作人刚要起身,鲁迅已经拄着文明杖快步走出月亮门,呢子大衣的下摆扫过门槛积着的残雪。 鲁迅葬礼那天,万国殡仪馆外挤满了穿学生装的青年。 许广平抱着海婴站在灵堂前,看见个戴圆框眼镜的瘦削身影在人群外徘徊。 那是闻讯赶来的周建人,三弟当年被二嫂逼得携家南下,如今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眼镜片后的眼睛肿得像核桃。 棺木入土时,周作人正在北大红楼讲《颜氏家训》,说到"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粉笔头突然在黑板槽里断成两截。 往后的年月里,周作人书房的灯总要亮到后半夜。他给《宇宙风》杂志写回忆录,提到大哥时总用"豫才"这个早就不用的别号。 1944年南京汪伪政府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看日本军官授勋,忽然想起二十岁那年大哥从东京寄来的《摩罗诗力说》手稿,泛黄的宣纸上还沾着神田区居酒屋的清酒香。 朱安最后的日子过得清苦,靠卖鲁迅藏书度日时,许广平托人从上海捎来生活费。 老太太临终前攥着儿媳的手不肯闭眼,朱安摸着婆母寿衣上的盘花扣轻声说:"您放心,我把大先生的衣裳都收在樟木箱里呢。"她不知道,虹口大陆新村的衣橱里,还挂着件许广平给鲁迅织的枣红色毛衣。 八道湾的老宅子现在住了二十多户人家,月亮门上的砖雕被煤烟熏得发黑。西厢房的日式拉门早换成纤维板,倒是院里的老枣树还在结果子,深秋时分熟透的枣子噼里啪啦砸在青石板上,像极了那年周作人摔门时,门环叩在砖墙上的声响。 信息来源: 澎湃新闻│《鲁迅与周作人:在北京安家四年后,兄弟俩彻底决裂》 宣讲家网│《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及兄弟绝交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