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杀安倍的山上彻也,审讯时说:如此努力的我,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01
1980年,山上彻也生在日本三重县。
那时候,日本的收音机里放的都是松田圣子,电视里演的是追捕,大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丰田车,人人都觉得好日子还在后头,长着呢。
山上一家,就是这好日子里头最体面的那拨人。
他爹,是个正经从京都大学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脑子活,手里有技术,自己开了家建筑公司。他妈,山上洋子,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小姐,娘家也是搞建筑的,家底比山上家只厚不薄。
山上彻也的童年,就像那个年代所有中产家庭的广告画一样,干净、漂亮、什么都不缺。
家里有哥哥,有妹妹,父亲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和墨水味,母亲的衣柜里挂满了当时最时髦的裙子。
山上彻也从小就聪明,话不多,但事儿看得明白。他知道,这个家是靠他爹那双画图纸的手,和他外公那个永远有活儿干的工地撑起来的。
这个家,就像一栋刚刚盖好的房子,地基扎实,窗明几净。
可房子再结实,也架不住地底下闹龙王。
80年代中后期,日本那疯涨的楼市就像个吹过了头的气球,眼瞅着就要炸了。
山上彻也的爹,就是无数被这气球带到天上去,又被狠狠摔下来的倒霉蛋之一。公司的项目越来越少,银行的催款电话越来越多。
晚上,山上彻也常常能透过书房的门缝,看见他爹一个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的不是图纸,而是一瓶三得利的威士忌和一摞厚厚的账本。
烟灰缸里掐灭的烟头堆成了小山,那股呛人的味道,就是这个家开始腐烂的味道。
家里的另一头,客厅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他妈,山上洋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一个叫“统一教”的玩意儿。家里开始频繁地出现一些陌生人,他们管彼此叫“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唱一些听不懂的歌。
他们说,世间的一切苦难,都是神对信徒的考验。
山上彻也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晚上,他爹喝多了,通红着眼睛冲进客厅,一把将桌上的《原理讲论》扫到地上,冲着他妈和那帮教友吼:“考验?我的公司要破产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也是考验?洋子,你醒醒!我们家要完了!”
他妈洋子,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她只是平静地扶起那帮受了惊吓的教友,轻声说:“亲爱的,这正是我们需要奉献的时候。把一切交给文鲜明大人,他会拯救我们的灵魂。”
爹的脸上,愤怒瞬间就没了,只剩下一种彻骨的,死灰一样的绝望。两个人的空间,一个在人间挣扎,一个在所谓的天国里漂浮,中间隔着一条谁也跨不过去的河。
1984年,河岸塌了。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嘭”的一声,碎得稀烂。
山上家的公司,一夜之间,从资产变成了天文数字的负债。
他爹没撑住。
那年年底,一个阴冷的下午,他爬上了一栋还没完工的高楼,那是他自己公司接的最后一个项目。
他从楼顶跳了下去,没留下一句话。
爹的死,换来了一笔6000万日元的人寿保险金。
这笔钱,是拿命换来的,是留给他们兄妹三人活下去的本钱。可对山上洋子来说,这笔钱是她向“神”证明自己虔诚的最好祭品。
葬礼刚过没多久,洋子就取出了200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捐给了统一教。
她跟孩子们说,这是为了给他们的父亲赎罪,让他死后的灵魂能升入天国。
山上彻也看着他妈那张因为狂热而容光焕发的脸,第一次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是他妈了,是个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儿的怪物。
家没了,钱也没了,洋子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奈良的娘家。
外公看着自己女儿这副德行,气得说不出话,但终究不忍心看着三个外孙流落街头。
在外公的庇护下,日子总算还能过。
可洋子就像中了邪,变本加厉。她把外公家当成了教会的联络点,把外公的钱一笔一笔地“奉献”出去。
1998年,外公去世了。
这个家最后的顶梁柱也倒了。
外公在遗嘱里留给了洋子两处房产,那是给孩子们最后的保障。
洋子拿到房产证的第二天,就找了中介,把房子卖了。到手的4000万日元,一分没留,全塞进了统一教的功德箱。
至此,山上彻也的那个黄金鸟笼,被他亲妈,一根一根,亲手拆了个干净。
笼子没了,可他们兄妹几个,也早就没了飞的力气,直挺挺地摔进了深渊里。
家徒四壁,这四个字砸在山上彻也的头上,比他爹从楼上掉下来那天,感觉还要重。
山上彻也天生就是块读书的料,脑子比谁都转得快。
高中毕业,他拼了命地学,愣是把自己送进了同志社大学的门槛。
这学校,放在全日本,也是响当当的名校,相当于中国的985。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觉得天总算要亮了,他能靠自己,把这个烂成一摊泥的家重新扶起来。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他没钱交学费。
他去找他妈,那个名义上的母亲。
洋子正在家里跟教友们学习教义,看见他进来,眼神里没有一丝母亲该有的温度。彻也攥着通知书,声音都在抖:“妈,我考上大学了,学费……”
洋子打断了他,脸上带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微笑:“彻也,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精神里。你应该向神祷告,而不是来找我要钱。”
那一刻,山上彻也心里最后一丝对母爱的幻想,彻底死了。
山上彻也没去学校报到,那张能改变他命运的纸,被他撕得粉碎,扔进了垃圾桶。
梦想,这玩意儿,是有钱人的消遣。
对他来说,活下去才是正经事。
哥哥的癌症越来越重,妹妹还在上学,养家的担子,不由分说地压在了他这个还没成年的肩膀上。社会上能干的活儿,他都干遍了。
工地搬砖,饭店刷盘子,便利店站夜班。
但他挣的钱,就像往一个无底洞里洒水,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2002年,经人介绍,他进了海上自卫队。
不是为了保家卫国,那玩意儿太空了。
山上彻也就是为了那份稳定的薪水,为了能让他哥多吃几片药,让他妹的午餐费有着落。
在“松雪舰”上,他是个没编制的低级自卫官,干着最累的活。
但他不抱怨,他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学习和训练上。
山上彻也玩命地考上了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校,想着有了技术,就能有个好前途。
可家里的那个窟窿太大了。哥哥的治疗费是个天文数字,妹妹也要花钱。
他的工资,扣掉借贷的利息,所剩无几。
最穷的时候,他背着一百多万日元的贷款,每天晚上躺在狭窄的行军床上,睁着眼,想的不是姑娘,不是未来,是怎么才能搞到钱。
人被逼到绝路上,什么邪招儿都能想出来。
2005年2月,他干了一件这辈子最混蛋,也最悲壮的事。他给自己买了一份高额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是他哥哥和妹妹。然后,他躲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拧开一瓶汽油,像喝水一样,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
山上彻也想用自己的命,做最后一笔买卖,给这个家换点钱。
胃里像着了火,烧得他满地打滚。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可老天爷偏要跟他开玩笑,他没死成,被人发现,抢救了回来。命保住了,但因为这次保险诈骗,他被自卫队干脆利落地开除了。
从鬼门关爬回来的山上彻也,鼻青脸肿地站在社会的烂泥地里,一无所有。
山上彻也没有倒下,他得活着,为了哥哥和妹妹。他开始疯狂地考证,吊车驾照、理财师资格证、建筑宅地交易师……只要是能挣钱的本事,他都去学。
那些证书一张张贴满了出租屋的墙,像是一个男人在跟命运搏斗时,被打掉的一颗颗牙。
这些年,唯一给他一点暖气的,是他的伯父。
伯父是个律师,当年楼市泡沫破裂时,他没像彻也的爹那样去跳楼,而是捡起了法律书,硬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建筑商逼成了一个律师。
伯父时不时地接济他们兄妹,前前后后加起来,给了他们两千多万日元。
有一次,伯父把他叫到自己的事务所,昏暗的灯光下,伯父的脸显得特别疲惫。他递给彻也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然后点上一根烟,说:“彻也,你很聪明,也很努力,这我都知道。但你要明白,你要对抗的,不只是贫穷,而是你母亲心中那个已经吞噬一切的魔鬼。那个东西,靠你一个人,是打不败的。”
山上彻也捏着信封,看着伯父吐出的烟圈,点了点头。他那时候就明白了,他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生活本身。
可明白归明白,日子还得过。
日本的经济就像个得了慢性病的老头,一直不见好。他有再多的证书,也只能在人才市场里找到一份又一份的临时工。他像一颗螺丝钉,今天被拧在这家工厂,明天又被换到那个仓库,拼尽全力地转动,却发现自己根本没在前进,只是在原地打转,直到把身上的螺纹都磨平。
这十年,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拳手,一次次被现实KO,又一次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鼻子里流着血,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却还在朝着那个看不见的对手挥舞着拳头。
02
2014年,一道光,像是耶稣显灵一样,照进了山上彻也那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
他的律师伯父,花了几年时间,到处搜集证据,跟统一教那个庞然大物硬碰硬地打官司,竟然奇迹般地打赢了。
法院判决统一教退还洋子当年捐赠的一部分钱财,整整5000万日元(在当时折合人民币约千万元)。
拿到钱的那天,山上彻也感觉自己像是在水里憋了几十年,终于能浮上水面,狠狠地吸了一大口气。
这笔钱,不是一串数字,是命。是他哥的命,是他妹的未来,是他自己后半辈子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希望。他甚至开始计划,给哥哥换更好的医院,让妹妹去上她喜欢的艺术学校,自己也可以找个地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就在这时,那个消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的母亲山上洋子,回来了。
她站在门口,头发花白,身形憔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彩。她哭得像个孩子,抱着彻也的腿,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说自己错了,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忏悔。
她说她想家,想孩子们。
山上彻也的心,是石头做的,也被这眼泪给捂热了。他恨她,恨得咬牙切齿,可她终究是他妈。他想,或许人老了,真的会醒悟。他把她接进了家,那个他好不容易才重新撑起来的,脆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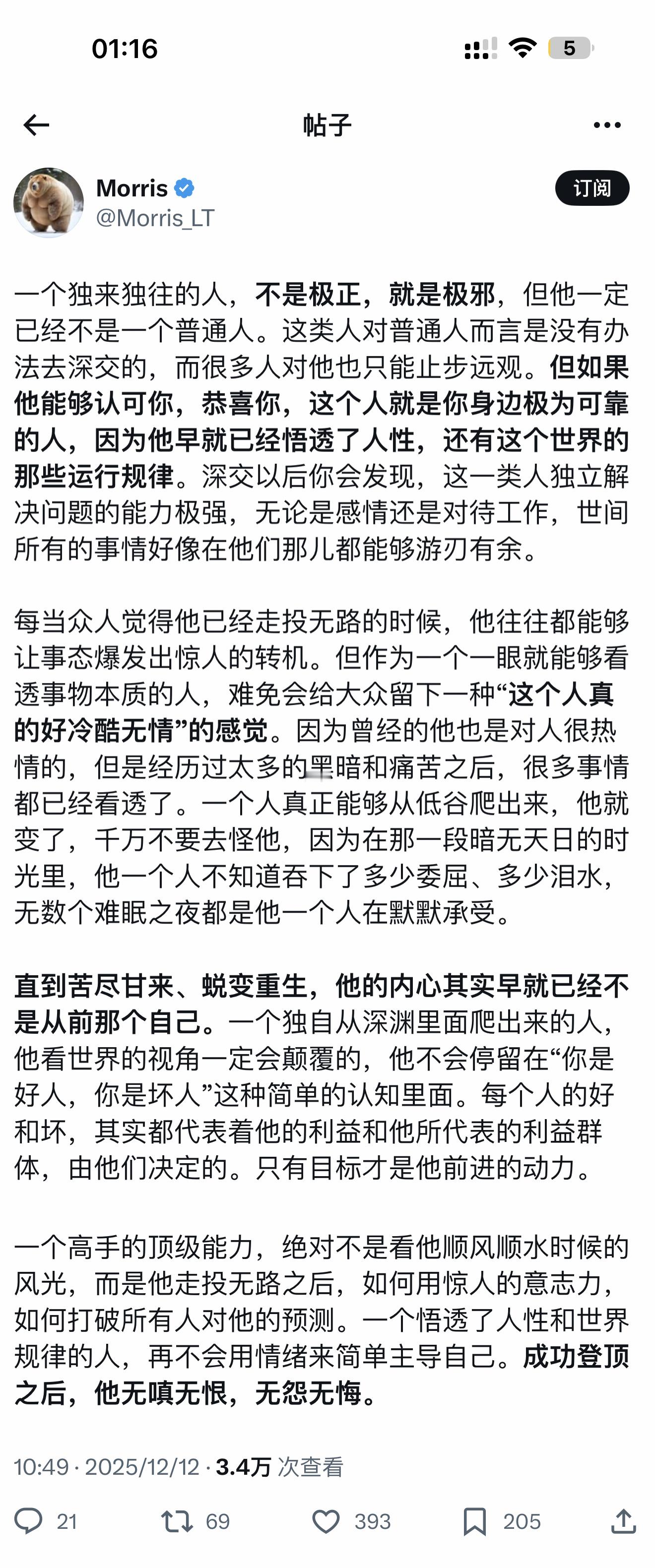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