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领导来说,下属的“忠心”远比“能力”重要得多。但尉迟敬德的结局又告诉我们,“忠心”并不能保证下属能获得一张“无限期饭票”,甚至“过度”的忠心对领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尉迟敬德与李世民原本是两个阵营里的敌手,前者是刘武周的马前卒,后者是大唐帝国冉冉升起的将星。
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攻破李唐的革命圣地晋阳,并一路挺进打到河东,眼看着就要跨过黄河打到关中了。看这架势,新生的大唐帝国似乎要夭折了。
刘武周的“腰杆子”就是尉迟敬德,这伙计拧足了发条,一举俘获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等大唐要员。
危急时刻,李世民发威了,他率领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设伏,打得尉迟敬德孤身逃跑。李世民乘胜反击,千里追凶,死咬住尉迟敬德不放,并将他困死在介休。

尉迟敬德是个识时务者,他举城投降,从此成了李世民帐下的一员悍将,并在此后的洛阳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所以有人鼓吹,尉迟敬德是大唐开国数一数二的将领,顶流明星。人家凭实力吃饭,哪个老板不喜欢?
说这话的人牙齿严重漏风,内容一窍不通!就尉迟敬德的军事能力,给李靖提携都不够资格,还妄想混到“军事家”的圈里?
这就是很多人的误解,往往将“军事家”和“将领”混为一谈。整个大唐帝国,真真算得上军事家的并不多,开国战争中唯有李靖才无愧于这个称号,连李世民也只能勉强算。

尉迟敬德充其量就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并不具备指挥才能,更没有统帅千军的才华,说白了就是元帅手中的一把钢刀而已。
即便是钢刀,其锋利程度比起秦琼来还是稍显钝了一点。
那么,李世民为何偏偏喜欢尉迟敬德,而不是李靖、秦琼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一个字——忠!对领导来说,下属的“能力”是选择项之一,“忠心”却是一个必选项,而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忠”几乎无人可以超越。
在战场上,尉迟敬德两次救了李世民的命,这叫“过命的交情”。
在尉迟敬德眼里,他只有李世民,没有齐王、太子,甚至皇帝。

李元吉不知深浅,偏要跟尉迟敬德“切磋”。尉迟敬德一点情面都不给,让李元吉输得颜面尽失。你以为尉迟敬德不懂人情世故?错,这家伙精着呢,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李世民看到他的忠心:在我眼里齐王就是个屁,您才是我唯一的靠山。
后来,太子亲自示好,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阵营,而尉迟敬德竟然冷冷地怼了回去,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秦王府的头顶,当时的真实情况其实是李世民一人单挑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父子三人,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这种情况下,尉迟敬德竟然无视太子爷主动抛来的橄榄枝,选择了跟李世民生死与共。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主动将自己融进了李世民的血液。

面对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的“劝进”,李世民表现得却优柔寡断。这其中固然有风险太大,不能贸然行事,但其实也包含了李世民另一层思考,那就是“检验部下的成色”。
临大事,上下同欲往往比“谋”还要重要,尤其是“玄武门之变”这种事,不可预知的情况太多,失败往往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动摇。
所以,李世民一再后退,用他“最软的姿态”来甄选身边“最硬的汉子”。
针对李世民的态度,秦王府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以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为代表的“硬汉派”,另一种就是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暧昧派”。

当李世民下定决心,并让人去请房玄龄、杜如晦来议事时,二人却借口皇帝不让他们去秦王府唯有推脱了。李世民大怒,令尉迟敬德持剑请客:不来就砍了他们!
其实房、杜并非三心二意,只是他们的“忠心”是有条件的:假如主子下定了决心,咱们的努力才有意义,你都犹犹豫豫的,咱岂不是白流血?我们的命不能这么不值钱。
很显然,房玄龄、杜如晦站得更高,但对李世民来说,此刻他更需要“愚忠”,毫无杂念的愚忠,所以尉迟敬德的印象分又增加了一些。
在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做了无可替代的,也没人敢做的事,脏事!比如,他亲手射杀了李元吉。再比如他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一身血污去威逼李渊。

您可能会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您说这话是从结果反推当时的情景,但对当事人来说,那叫形势瞬息万变,面对皇帝,谁有胆量发出赤裸裸的威胁?
就算李世民肯定成功,但请别忘了,李世民面对的不仅是皇帝,还是父亲。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李渊震怒,非要李世民拿尉迟敬德当替罪羊才肯罢休,李世民该怎么办?
您觉得李世民会为了尉迟敬德跟父亲翻脸吗?会为了尉迟敬德,宁可背负骂名也要死扛吗?会为了尉迟敬德,甘愿落下一个“得位不正”的沉重包袱吗?

历史上不乏其人,比如成济,那伙计为了替主子分忧,亲手杀了曹髦,结果司马昭却将他当替罪羊,灭其族以堵悠悠之口。
所以,尉迟敬德此举面对的不仅是李渊的明枪,还可能有李世民的暗箭,若非心无杂念的“愚忠”是断然做不到的。
尉迟敬德的性情跟他的“铁匠”职业很匹配,刚猛、火爆,一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画风。这样的人,历史小说中有一个模板,那就是“铁牛兄弟”李逵。
但我们又发现,二人在“相似”的外表下,却有截然不同的内质。李逵是真的简单,简单到将自己异化为宋江的尾巴,思想则退化为一截盲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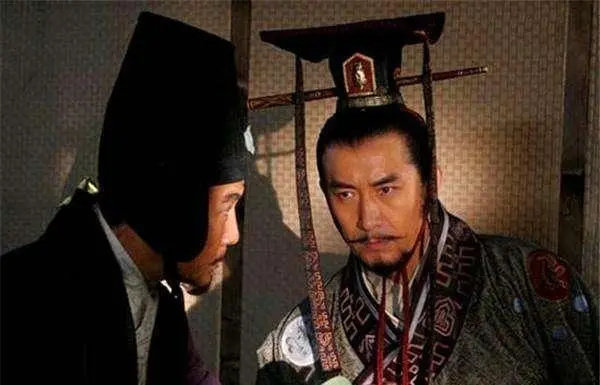
尉迟敬德不同,他火花四溅的行为下无不是个人的“思想”,比如,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得失分析,这种事李逵是做不来的。
所以,从尉迟敬德的个性上看,他其实不具备“愚忠”的基因,那么,他为何又能表现出毫无杂念的“愚忠”呢?
世上的人可分为“感性动物”和“理性动物”两类,总的来说,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属于同一类,都是感性动物,尤其是尉迟敬德。
再一次次的生死患难中,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他对李世民不仅仅是上下级,更是掺杂了“兄弟骨柔情”。

李世民也一样,最初我读史时,发现李世民的“哭功”比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慢慢地才发现,那绝不是表演,李世民就是那种人,很多愁善感。
这两种人碰在一起,生发出兄弟情意外吗?
我们发现,哪怕是帝王,高处不胜寒的他们更缺少这种人间最温暖的情感,比如刘邦与卢绾、刘秀与朱祐、李渊与裴寂、朱元璋与汤和等等,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就是这种关系,超越了能力,甚至超越了利益。
也正是这种感情,让尉迟敬德慢慢迷失了自我,忘记了他与李世民最重要的关系——君臣。
李世民终究是个皇帝,他要站在天下的立场上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能力不算出众的尉迟敬德逐渐被排除了核心圈,到地方任职去了。

不是李世民“过河拆桥”,把尉迟敬德留在身边就是个大麻烦,这伙计自负其功,对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指指点点,甚至当众责难,似乎他就是皇帝的代言人。
这种草莽,显然不适合位居朝堂,所以,从贞观三年起,李世民就将他一脚踢出了长安。而尉迟敬德显然还认识不到自己的短板,还沉浸在与皇帝的“兄弟情”中。
贞观六年,李世民宴请功臣,尉迟敬德竟然因为座次问题大发雷霆,怒次别人“没资格坐在他的前面”。李道宗想当和事佬,却被尉迟敬德一拳差点打瞎了眼睛。
李道宗不是等闲之辈,从身份上讲,他是李世民的堂弟,任城王。从资历上讲,他是李靖的弟子,贞观年间挑大梁的军队将帅,在消灭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的高度远不是尉迟敬德所能及的。

但尉迟敬德竟然将李道宗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差点将人家打残了。更要命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李世民的眼前。
于是李世民终于火了,撂下了狠话:以前朕读历史,总是责怪刘邦对功臣们薄凉,现在看来,刘邦也有不得已的地方。你要好自为之,不要做后悔莫及的事。
直到此时,尉迟敬德才彻底醒了:皇帝没有兄弟,忠心换不来一世饭票,原来都是自己“多情”了。
从那以后,尉迟敬德闭门谢客,玩起了养生,除了跟随李世民出征高句丽,再也没出过门。尉迟敬德的晚年其实有点凄凉,那些当年的战友们似乎都忘了他,没人去探望他。
就这样,尉迟敬德度过了三十多年“阖门自娱”的生活,直到高宗显庆三年去世。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