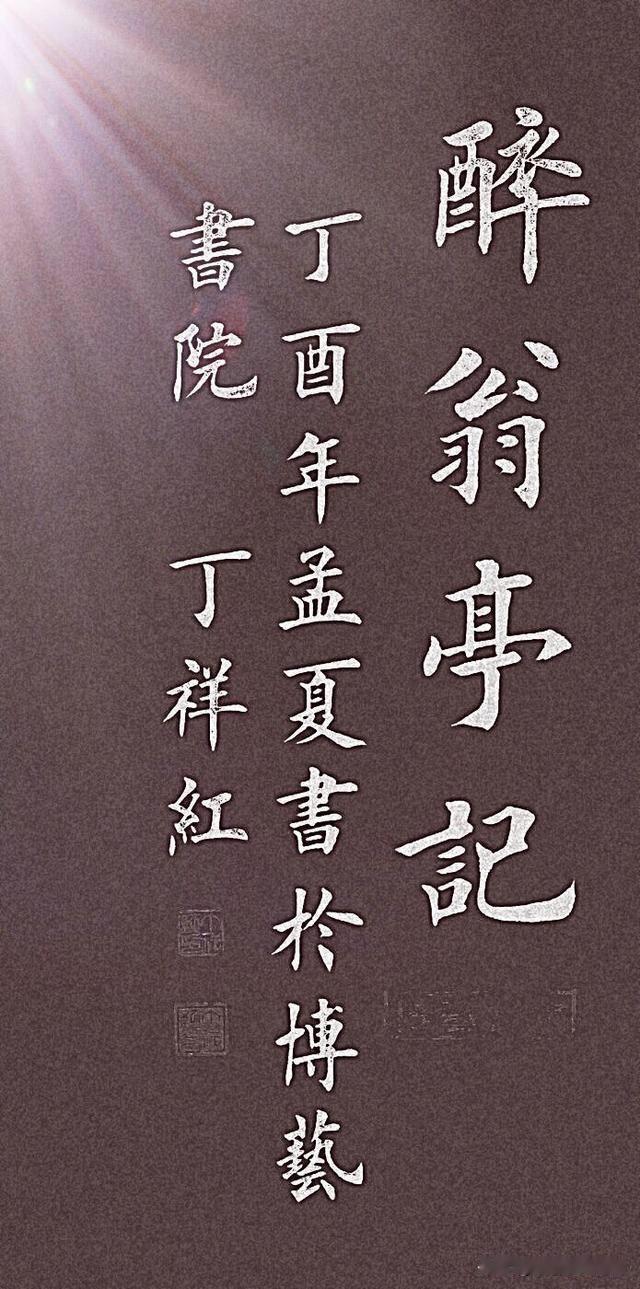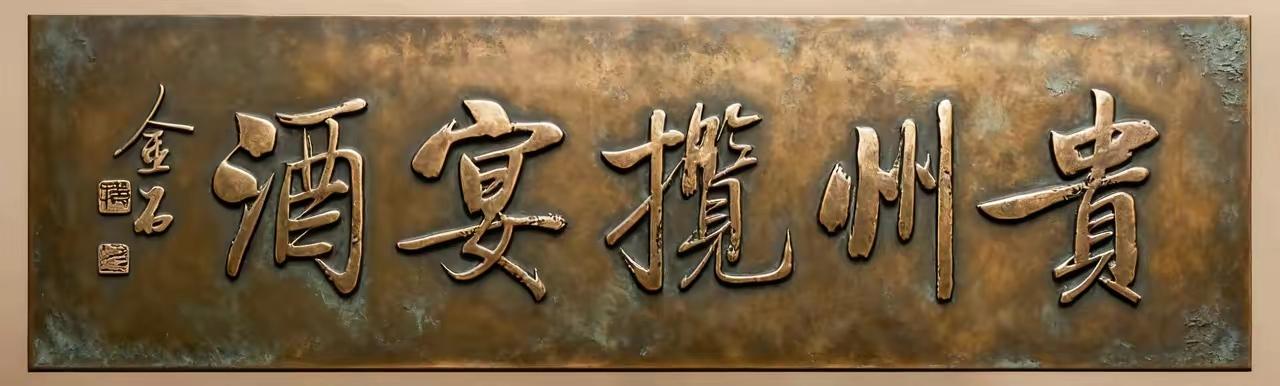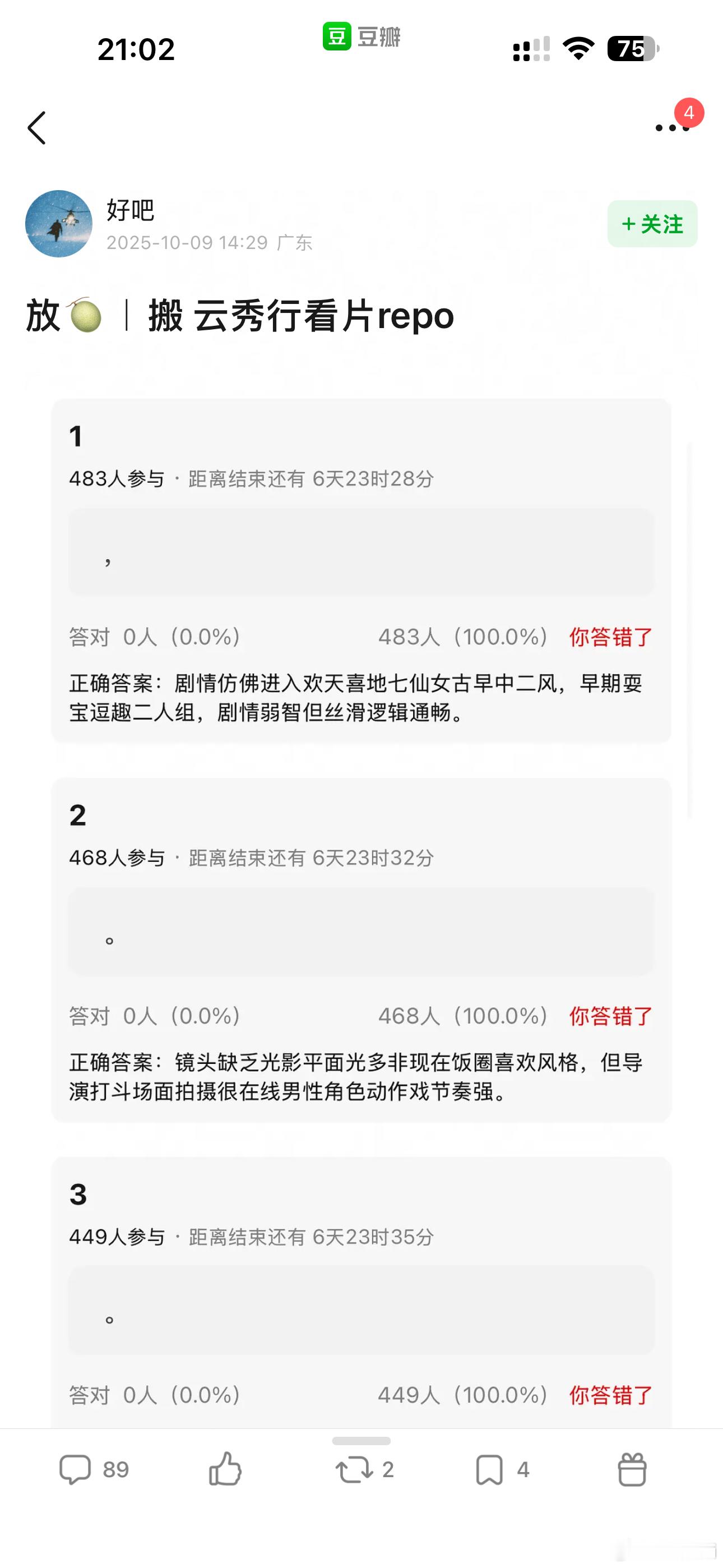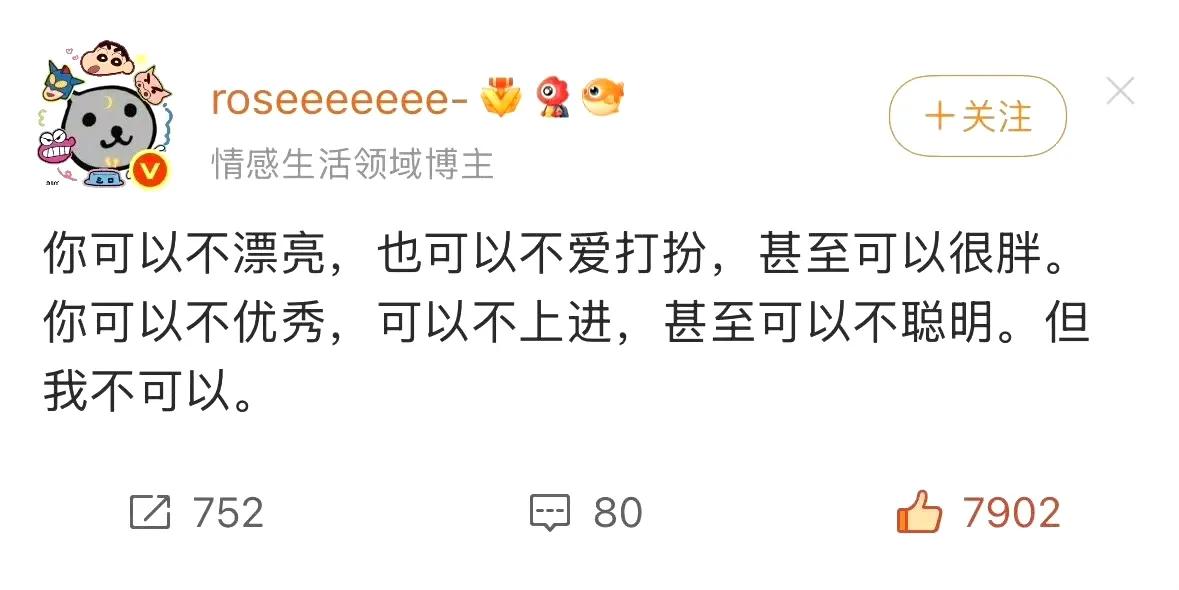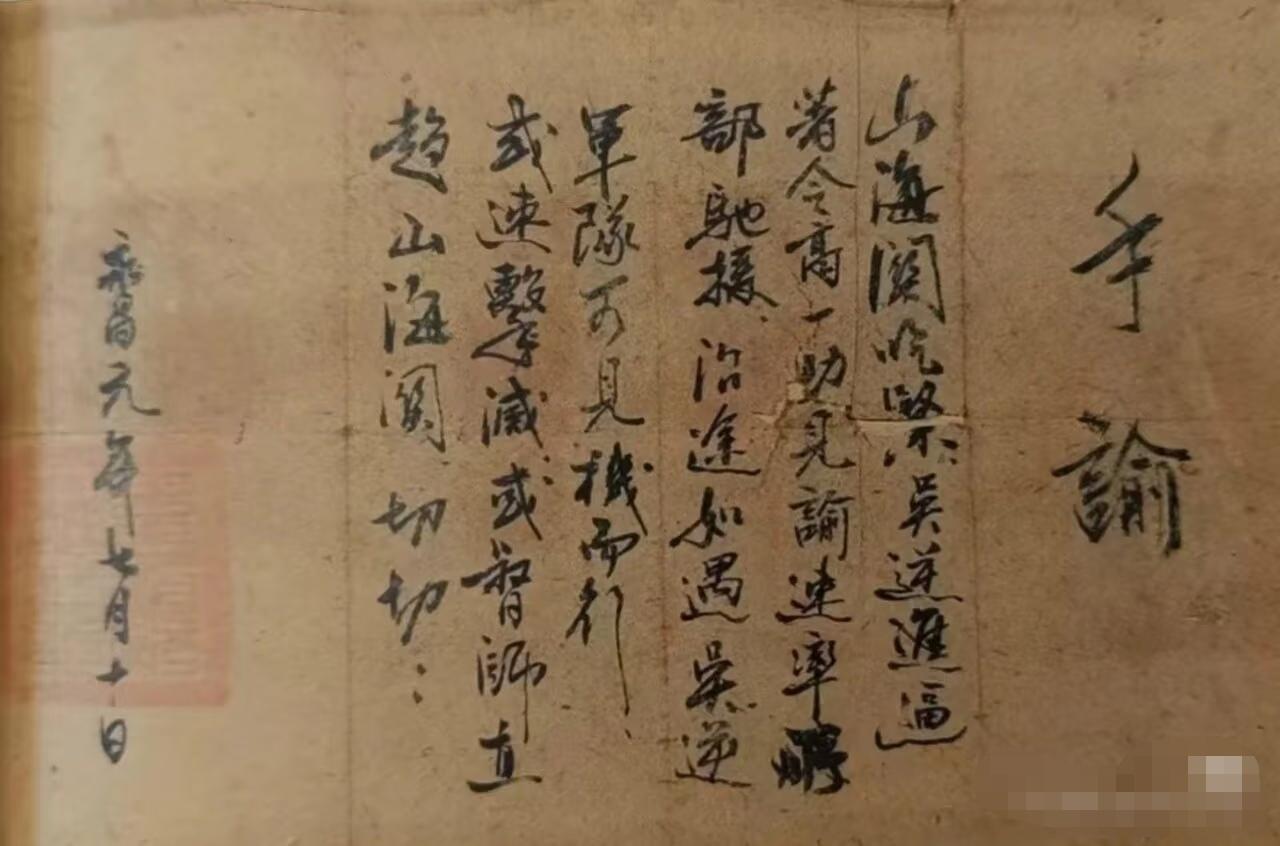江风卷着残叶,拍在赤壁的礁石上,碎成一片寒凉。杜牧披着青衫,立于矶头,手中一卷《三国志》被夜露浸得微潮。他抬眼望向西沉的明月,月光洒在江面,映出当年周郎破曹的古战场——江水滔滔,似在诉说“樯橹灰飞烟灭”的过往;他低头吟哦,笔锋落处,便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绝句,在夜色里流转,字字都似一把轻剑,挑破历史的帷幕,照见兴亡的真谛。

杜牧的一生,如一卷浸着忧思的史稿,以绝句为笔,以山河为纸,在晚唐的衰颓里,写下“鉴古知今”的警醒。他出身京兆杜氏,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通典》作者,家学的熏陶让他自幼便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成年后登进士第,却因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仕途辗转,始终未能施展“经世济民”的抱负。《新唐书·杜牧传》载其“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这份“敢言”的风骨,化作他诗中的锋芒,既写得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疏狂,更道得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他的诗,总与“兴亡之地”相生相伴。游金陵(今南京),他站在台城遗址上,见“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想起南朝陈后主沉迷声色、终致亡国的旧事,柳色越盛,越衬得历史的悲凉;过阿房宫故地,他写下《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的句子,痛斥秦的奢靡无度,“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论断,更是将兴亡的根源,直指统治者的昏聩;泊秦淮,他听着画舫里的靡靡之音,联想到“陈叔宝亡国”的教训,便有了“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讽喻——秦淮的水,曾映过南朝的歌舞,也映过晚唐的颓势,而杜牧的诗,恰如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荡过千年仍未平息。他的绝句,从不是无病呻吟的闲愁,而是“以小见大”的史鉴。《赤壁》一诗,借“东风”与“二乔”的假设,看似谈三国轶事,实则暗讽晚唐统治者“忽视天时、妄自尊大”的昏庸;《过华清宫绝句》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杨贵妃嗜荔枝的小事,揭露唐玄宗后期的奢靡,暗示“安史之乱”的祸根;即便是《江南春》里“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媚,也藏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追问——那些曾经香火鼎盛的寺庙,不正是南朝统治者沉迷佛教、荒废政务的见证?

晚唐的朝堂,如风雨飘摇的孤舟,杜牧的诗,便是舟上的警钟。他曾向宰相李德裕上书,提出平定泽潞藩镇的策略,却未被采纳;他任黄州、池州刺史时,兴修水利、整饬吏治,试图为地方百姓谋福祉,却终究挡不住王朝衰落的大势。但他从未放弃“鉴兴亡”的初心,直到晚年,仍在诗中写道“今来故国遥相忆,月照千山半夜钟”,字句间皆是对家国命运的牵挂。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诵读杜牧的绝句,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清醒。他的诗,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照见的,是“奢靡必亡”的铁律,是“居安思危”的智慧,是“以民为本”的初心。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这份“鉴兴亡”的精神,愈发显得珍贵:我们从“秦亡于奢”中懂得,要坚守勤俭节约的传统;从“南朝亡于惰”中懂得,要保持锐意进取的姿态;从“晚唐亡于散”中懂得,要凝聚团结奋斗的力量。

杜牧的笔早已停驻在晚唐的时光里,但他绝句中的兴亡镜,却永远悬在历史的长廊中。它提醒我们,忘记历史,便意味着背叛;忽视教训,便可能重蹈覆辙。在当代,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个人修身,都需要这份“以史为鉴”的清醒——正如杜牧用绝句警示晚唐那般,我们也当以历史为灯,照亮民族复兴的前路,让“兴”的经验得以传承,让“亡”的教训不再重演。江风依旧,赤壁的明月仍在;杜牧的绝句,也将在时光中继续流转,成为代代相传的“兴亡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