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相对自由,为错开返程高峰,这几年我基本都是提前一个月回家过年,因为在家也能办公。
正因如此,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村如今的荒凉:
只有为数不多的老人和一些村干部守着村庄。以前还有很多小孩子和老人,但这些年小孩子不是在县城上学,就是跟着父母迁徙到工作的城市一起生活。而老人,一部分作古,一部分则跟随子女到外地过日子。
夜晚,一个两百多户的村庄,只有几盏灯稀疏地亮着。
我们90后这一代人,从某个角度来说,还是幸运的。
大多数人都生长在农村,有一群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玩伴。小时候父母都在田间地里头忙活,没空管我们,我们一群人满村庄地追逐嬉闹。
上山摘野果,爬树掏鸟窝,下塘摸鱼虾。当然,农忙的时候,也帮父母割稻子插秧,闲的时候则一起玩弹珠、叠纸板、打子、跳绳、拍画片、捉迷藏。谁家有VCD则聚在一起看林正英的僵尸片、周星驰的喜剧片、成龙与洪金宝的武打片。
90后的我们,童年是快乐的。
后来父母们为了生计,不得不背着行囊去外地打工。不少人,也跟着父母迁徙到外地上学。
村里的田地开始荒芜,我上高三时,村里的田就被外地人承包了。
我们这个村,如今除了春节期间能有短暂的热闹,其余时间,都是一片寂静,只有蛙声与蝉噪,没有人语。
我想,可能再过几十年,等我们这一批仍眷恋着故土的90后也走了,我们村,可能也会消失在历史的浓烟中。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故土的概念,除了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其余时间都生活在城市里。
2013年,人民网等多家官方媒体就披露过一组数据,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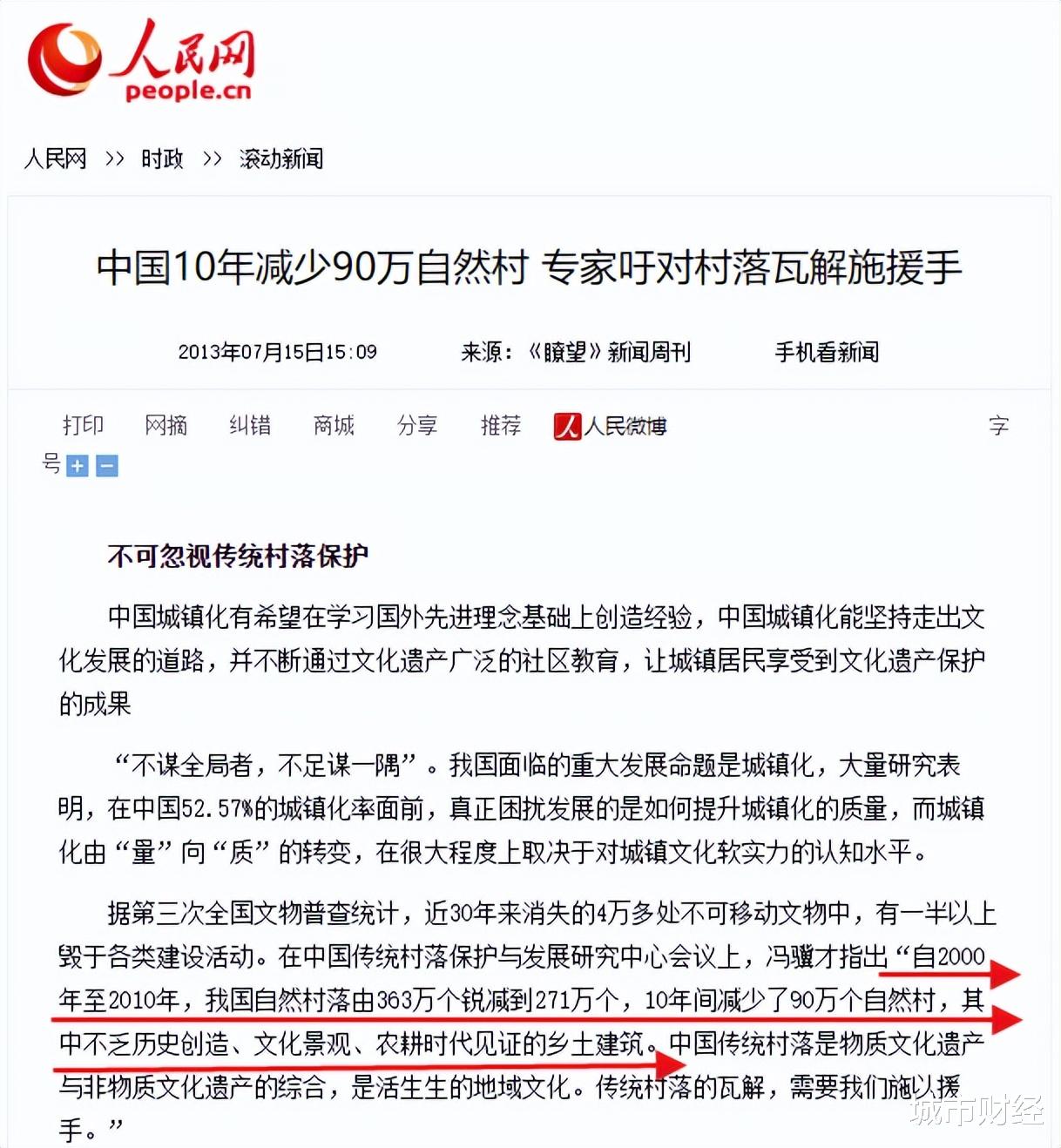
作为正在集体奔四的90后一代人,我们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家乡从热闹到冷清。
我们90后这一代,大多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我们的迁移路径,恰好描绘出了中国城市乡村的发展变局路线:
最初是乡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之后是,乡村、小城市人口不断减少,大城市人口仍在增加。
《河南社会科学》9月新刊的一则由郑州大学商学院的博士与博士生导师写的《收缩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论文提出:
2010-2020年我国收缩型城市数量加速增长。通过对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共识别出138个收缩型城市。
138个收缩型城市分布在全国22个省级行政单位中,分别是:
黑龙江省:绥化、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黑河、鸡西、伊春、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大庆。
辽宁:锦州、本溪、铁岭、鞍山、抚顺、丹东、辽阳、葫芦岛、阜新、朝阳、营口、盘锦。
四川:南充、巴中、内江、遂宁、资阳、自贡、广元、德阳、达州、乐山、雅安、攀枝花。
安徽:淮南、安庆、铜陵、六安、淮北、池州、马鞍山、宣城、宿州、黄山。
甘肃:武威、天水、平凉、白银、定西、陇南、张掖、酒泉、庆阳、金昌。
山西:忻州、运城、临汾、吕梁、大同、长治、朔州、晋城、阳泉。
湖北:孝感、荆州、黄冈、荆门、襄阳、十堰、随州、宜昌。
湖南:邵阳、衡阳、益阳、常德、岳阳、怀化、湘潭。
吉林:吉林、松原、通化、白城、四平、白山、辽源。
陕西:渭南、宝鸡、咸阳、商洛、汉中、安康、铜川。
广东:梅州、揭阳、汕尾、河源、潮州、湛江。
河南:南阳、驻马店、三门峡、漯河、焦作、鹤壁。
江西:宜春、吉安、抚州、九江、上饶、萍乡。
云南:临沧、普洱、昭通、曲靖、保山、玉溪。
内蒙古:乌兰察布、呼伦贝尔、赤峰、通辽。
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
河北:张家口、衡水、承德。
江苏:盐城、淮安、泰州。
广西:梧州、来宾。
宁夏:固原、中卫。
福建:三明。
青海:海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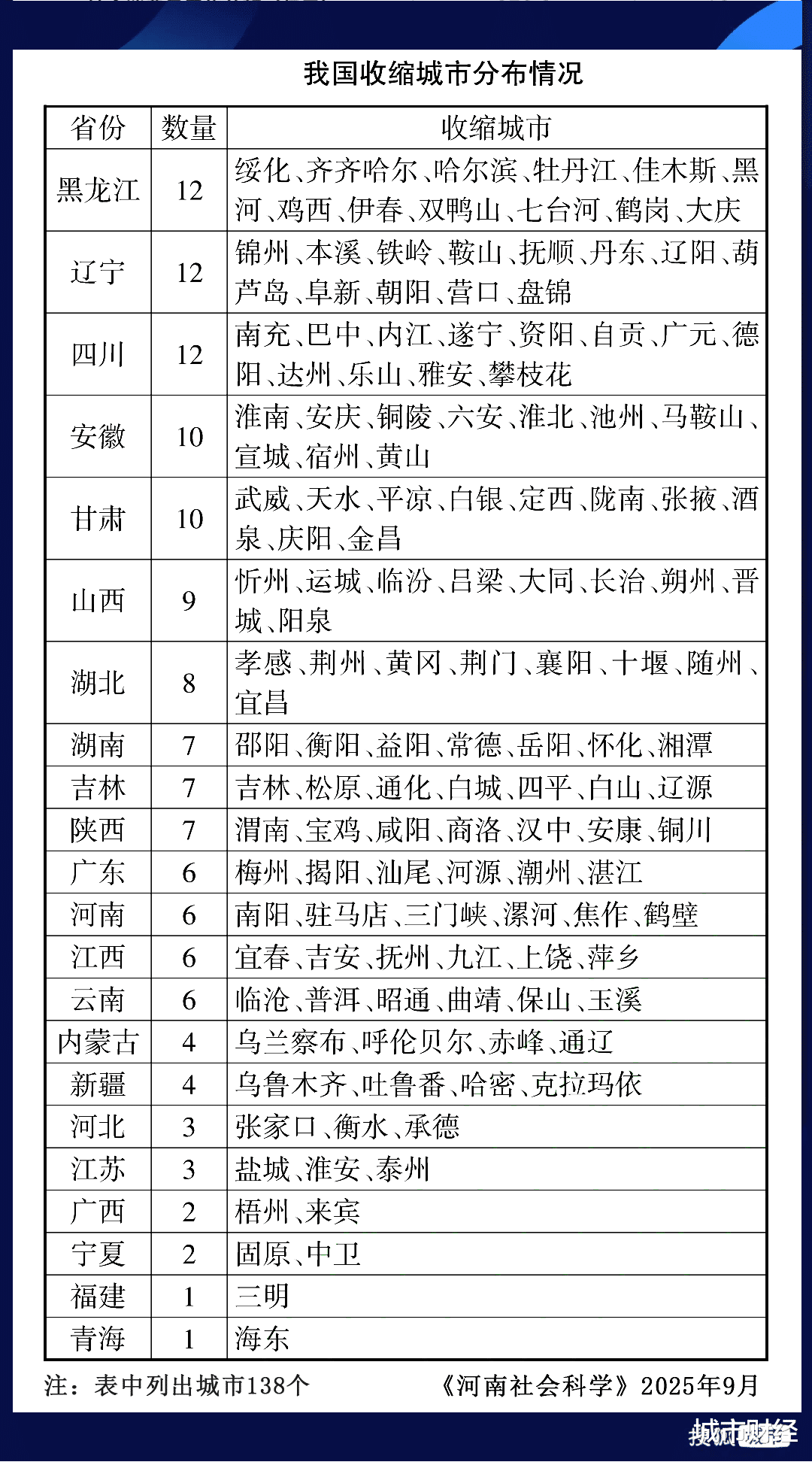
从上面的名单中可以看到,其中不乏一些核心城市,如黑龙江省会哈尔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还有一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如四川的省域副中心之一南充-达州,甘肃的省域副中心天水、酒泉,湖北的省域副中心襄阳与宜昌,山西的省域副中心长治、大同、临汾,河南的省域副中心之一南阳,云南的省域副中心曲靖。
上面的论文得出的收缩型城市的衡量标准是:
城区人口连续三年下降(注意是城区人口)。
其实,这一数据早就过时了,毕竟第七次人口普查距今已经有四五年了,当时梳理的都是2020年的人口数据。
四五年过去,收缩型城市数量早就不止138个,因为人口形势彻底改变了。
我们的人口2021年见顶,2022年开始减少,当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加速减少,减少了208万人。
2024年,继续减少139万人。
在这种背景下:
第一,2024年,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有20个地区人口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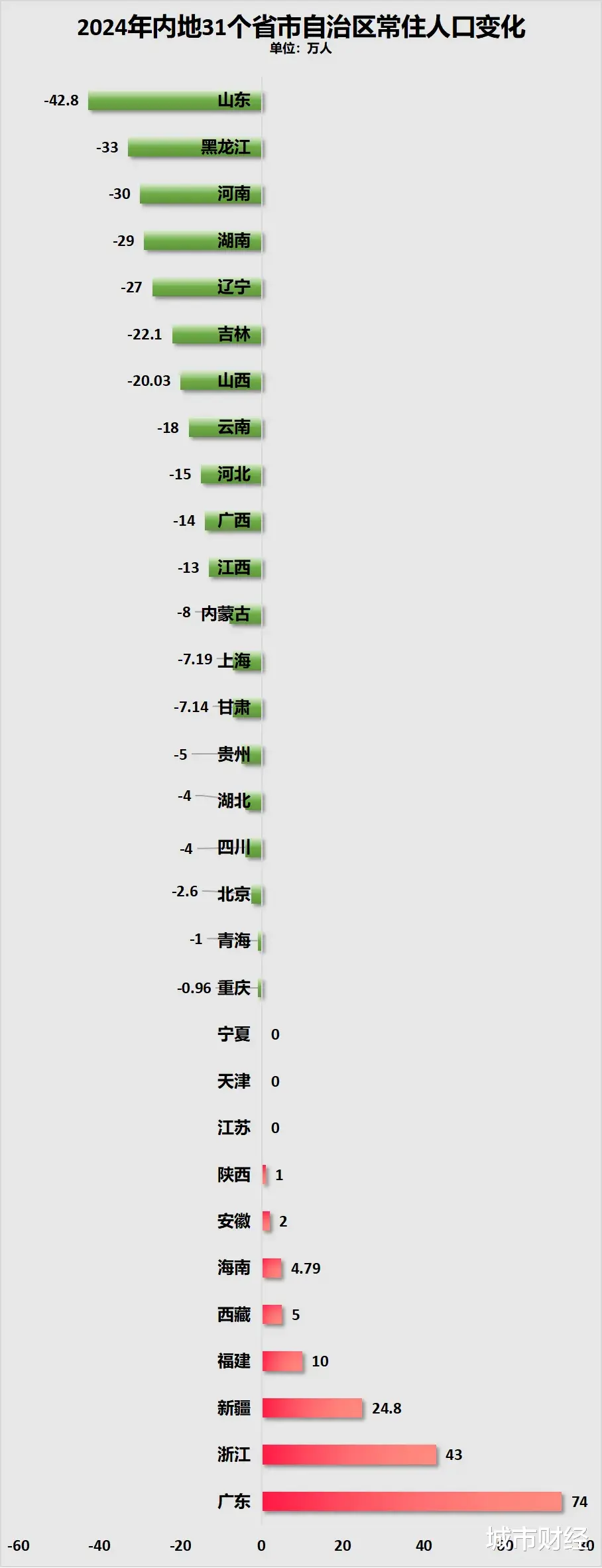
第二,河南、黑龙江、湖南、辽宁四省过去四年合计减少人数,均超百万。

第三,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去年常住人口无一增长。其中北京、上海、重庆人口减少,天津持平。
第四,2024年公布2024年常住人口数据的城市有313个,其中128个人口在增加,7个持平,177个城市人口在减少,算上哈尔滨则是178个。
哈尔滨在2021年人口跌破千万之后,过去两年不再公布常住人口数据,但大概率仍在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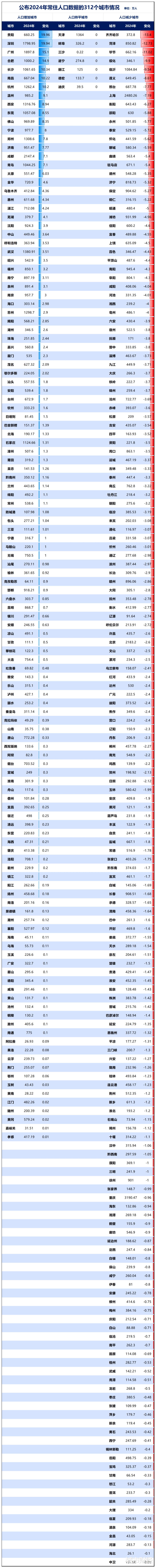
当然,以上这些并非全都是收缩型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长春等,因为收缩型城市的标准是连续三年城区人口持续减少。
上海、长春2023年与2021年人口在增加,北京2023年人口是增加的。
重庆连续连年减少,但减少的是外围区的农村人口,城区人口却在增加。有数据为证,重庆统计局披露:
2022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213.34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280.3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933.02万人。
2023年全市常住人口3191.4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2287.4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903.98万。
2024年常住人口3190.47万人,城镇常住人口2301.49万人,乡村人口888.98万人。
两相对比会发现,2022年至2024年,重庆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1.1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了44.04万人。
流失人口集中在农村。重庆乡村流失的人口,一部分进入了城区,一部分则流出了重庆。
虽然排除了一些城市,但上表中的大多数城市,符合通缩标准,且几乎都是三四线及以下城市。
原因并不复杂,有的是因为资源枯竭、经济低迷,如东北的阜新、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牡丹江等。
更多的则是当地的产业、经济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无法满足更好的就业,当地人口只能去往别的城市讨生活。
这也是顶层设计的结果。
中国的城市发展基本都依赖政策,而且过去十几二十年,好的政策都给到了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像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陕西、广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与自治区纷纷开启了强省会模式。
好的产业省会优先,优质的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资源,也是省会优先。普通的三四线城市,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在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的当下,城市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的局面会更加明显。
未来依旧是高能级城市、中心城市的天下。
今年7月份召开的时隔十年的城市会议明确提出:
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现代化城市群、都市圈是这段表述的关键词。
一句话总结,就是城市发展要告别过去的散打模式,进化为组团发展。
都市圈、城市群的本质,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其意图一方面壮大中心城市的能量场,另一方面,通过轨道上的都市圈、城市群,加快圈内、群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提升经济效益,助力圈内弱小城市的发展。
都市圈和城市圈是城市化2.0时代的载体,国家这些年之所以不断批复国家级城市群和国家级都市圈,就是要让每个圈的圈内城市之间的人、财、物等各项生产要素加快流通,产生更强大的经济效益。
城市群、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则是利好最大享受者。
此外,8月份中央发布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到:
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家批准明确的功能定位做强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主引擎。支持超大特大城市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支持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增强对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布局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提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有条件的省份培育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
所以说,无论是过去的散打模式,还是如今的组团模式,政策与资源倾斜的对象依旧没有改变,高能级城市、中心城市依旧是各个板块的最强话事人。
这就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加入收缩阵营。
03
收缩城市要被优化
随着全国人口不断收缩,一些人口减少特别严重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会被合并消失,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也是过去在做,将来我们仍要做的事情。
今年3月19日,民政部部长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到:
探索人口收缩地区行政区划优化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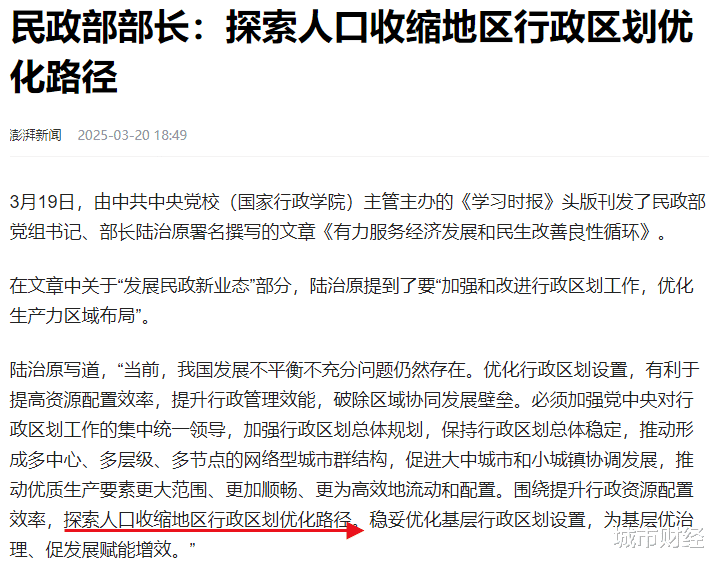
这里的优化,究竟是如何优化,民政部没有展开叙述。
不过,客观来说,可选择的路径并不多,基本都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大幅精简人口收缩严重地区的行政单位和人员。
这一点,从2023年就已开始,尤其是很多人口小县。具体可以参考前几天的文章破防!砸碎铁饭碗,力度加大了!
第二步,合并。
此外,8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也提到:
推动中小城市结合常住人口变动趋势,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按程序稳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
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也大差不差。
9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进行了独家专访在回答每日经济新闻的专访中明确说到:
从城市发展趋势来看,人口流失、资金外流、土地闲置的这一类城市,今后也会面临撤并或整合的可能。这是国际规律和经验,我们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其实,这事儿在人口已经持续减少十多年的日本,早就发生了。
2014年日本民间机构发布预测报告,将有896个市将消失。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日本的市和我们的市概念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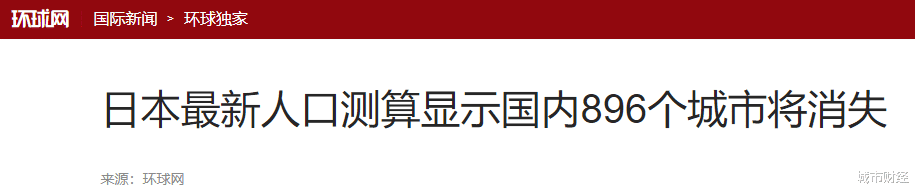
日本的市、郡、特别区相当于我国的县,而日本的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在日本县的级别比市要高,与我们正好相反。
2024年,韩国发出了两次人口警告。
第一次警报:2024年6月19日,韩国当时的总统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 ,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低出生率问题解决为止,并将成立了“人口战略企划部”。
第二次警报:韩国雇佣信息院去年6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报道,随着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因人口萎缩显现出“进入消失阶段”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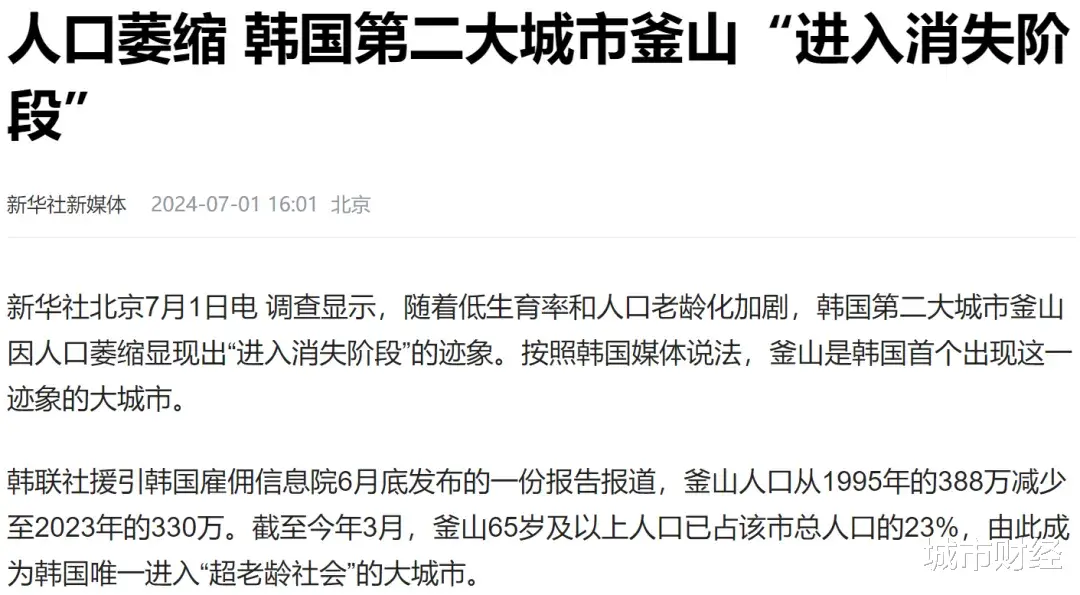
一国之总统,如此重视人口危机,可见韩国人口问题有多严重。
我们这边,乡村的消失与合并,早就在发生,第一部分介绍的人民网公布的数据便是佐证。
此外,2022年12月,黑龙江伊春市的乌翠区乌马河、锦山、向阳、曙光四个街道办事处因为人口减少因素,被撤掉街道,合并成了两个镇。
随着出生人口下降趋势难以阻挡,未来全国人口减少的幅度会继续加大,收缩型城市会越来越多,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是势在必行。
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北、西部和中部一些人口收缩较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