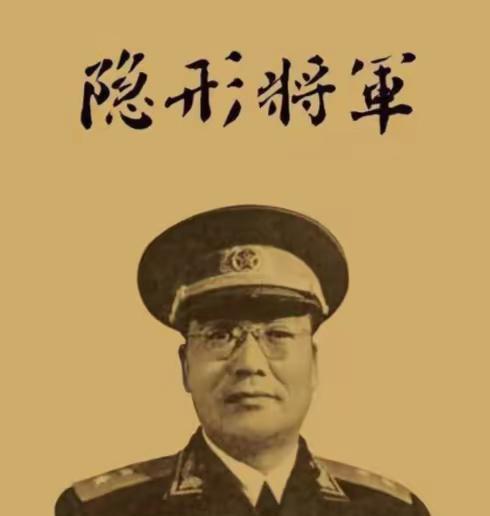1960年冬,李克农到韩练成家做客,一看到桌上的红烧狮子头,马上便说:“七嫂,你暴露了!”韩练成和妻子不由得一震。 当时,韩练成刚从甘肃省副省长任上退下来,带着妻子汪啸耘住进了北京胡同里的一处小院。 李克农是踩着薄雪来的,身上那件旧军大衣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一圈细毛边,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里面是给老战友补身子的阿胶。 汪啸耘正在厨房忙活,听见院门口的脚步声,系着蓝布围裙从门帘后探出头:“‘李经理’来啦?快进屋坐,狮子头再炖十分钟就烂乎了。” 这声“李经理”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尘封的时光——那是1942年李克农在秘密战线的代号。 那年韩练成正式加入地下工作,李克农给他起了“七哥”的代号,身为妻子的汪啸耘自然成了“七嫂”,三人接头时,便用这些名字在刀尖上传递消息。 厨房飘来的肉香越来越浓,当汪啸耘端着砂锅走进客厅,琥珀色的汤汁还在咕嘟冒泡,肥瘦相间的狮子头裹着酱汁,在白瓷盘里颤巍巍的。 李克农的目光落在盘子上,突然开口:“七嫂,你暴露了!” 韩练成正给李克农倒茶,闻言手一顿;汪啸耘刚放下砂锅,围裙上还沾着几点油星,两人同时看向李克农。 “她哪里是暴露,分明是立了大功!”韩练成放下茶壶,笑着打圆场。 李克农夹起一块狮子头,牙齿刚咬破酥软的表皮,眼睛突然亮了:“这味道,跟叶妈妈做的一模一样。” “就是叶妈妈教的。”汪啸耘接过话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寻常家事。 客厅里的三人都知道“叶妈妈”是谁——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叶秀峰的母亲,一个被汪啸耘“借”来传递情报的老太太。 1942年的南京城,韩练成在明处与国民党高层周旋,汪啸耘则在暗处织起情报网。她发现特务头子叶秀峰深居简出,却每周必回老宅给母亲请安。 叶老太太爱坐在四合院门口晒太阳,手里总拿着竹针织毛衣,见了邻居就拉家常,说的尽是儿子单位的“琐事”:今天买了什么菜,明天要去哪里出差。 汪啸耘便拎着毛线团凑过去:“叶妈妈,您看这花样新不新鲜?”一来二去,两人从织毛衣聊到做菜,叶老太太最得意的就是红烧狮子头——五花肉切粒,加荸荠碎,用黄酒煨足两小时,起锅前还要撒一把葱花。 秘方传到汪啸耘手里时,情报也跟着来了。“秀峰这几天总说电台吵,半夜还在打电话查线路。”叶老太太的抱怨,被汪啸耘连夜编成暗号传给李克农,地下电台第二天一早就转移了据点。 “秀峰明天要去上海,说是有‘大鱼’要抓。”这话让上海地下党提前三天撤离,躲过了一场围剿。 最险的一次,中统怀疑韩练成的身份,派人查他的社会关系。汪啸耘抱着刚织好的毛衣找叶老太太:“妈妈您看,有人说韩练成是共党,我一个女人家,哪经得起这种吓?” 叶老太太当即红了眼,第二天就拉着叶秀峰的手哭:“练成是好人!你敢动他,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叶秀峰虽有疑虑,却拗不过母亲,调查不了了之。 此刻,1960年的客厅里,李克农放下筷子,看着汪啸耘的眼神里,有后怕也有赞叹。要知道,叶老太太身边常年跟着便衣特务,一句错话、一个眼神不对,都可能掉脑袋。 “七嫂,你当年就不怕?”李克农忽然问,声音比刚才沉了些。 汪啸耘正给韩练成盛汤,勺子碰到碗沿叮当作响:“怕什么?我在给咱们人送消息,心里亮堂着呢。” 韩练成接过汤碗,笑着补充:“她啊,用一锅狮子头,顶得上一个情报站。” 窗外的雪不知何时停了,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桌上那盘红烧狮子头上,油光锃亮,像一枚枚浸过岁月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