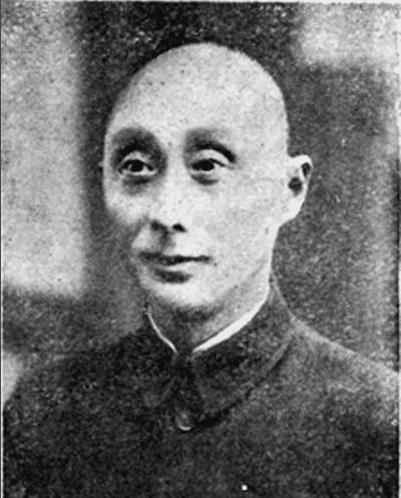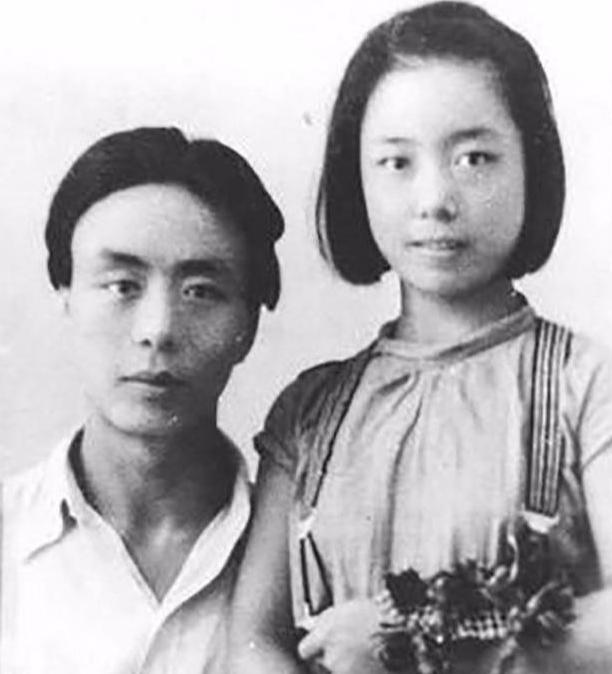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湖自尽于北京西城太平湖,在投湖自尽前,他特别舍不得自己最疼爱的孙女,在出大门前,他走到院子中间,把唯一的孙女小月叫出来,小月刚刚三岁,老舍郑重地向自己的孙女小月说:“和爷爷说再见”。 那一声“再见”落下时,院子里异常安静,丹柿小院的柿树叶纹都像凝住了。小月不懂大人世界的沉重,只觉得爷爷今天格外认真,像要出门很久似的。 老舍蹲下来,轻轻理了理她的额发,那双写遍世态的眼此刻柔得像春天化冻的水。 院门一响,他的背影掠过早晨的阳光,仿佛正从自己一生最熟悉的胡同里抽身而出。 没人知道,他前一晚在家里静坐许久。衣襟上还留着前一天带回来的灰尘,家人帮他上药时,他一句解释都没有,只说“没事”。 他懂得所有人都在担心,但他心里那道裂纹已不是药水能抹平的。他六十七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却仍习惯每天起得很早,在院中散步几圈。那天他走得慢,似乎每一步都在回望过去。 他的过去,不只是作家荣耀的堆叠,还有少年时旗人家庭的困顿、十三岁辍学的无奈、母亲洗衣度日的艰辛。他的人生一向是硬撑着走。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从未放弃写作。 从北京到伦敦,再到齐鲁大学、山东大学的讲坛,他把西方文学与市井经验揉在一起,写出《老张的哲学》,写出《骆驼祥子》,写出那些挺着脊梁、却常被命运按在尘土里的小人物。 他写人间百态,却很少真正替自己辩解过一句。 那天他走在去太平湖的路上,偶有人同他打招呼,他都轻点下头。曾经,他在重庆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在北京写下《四世同堂》,那些描写民族苦难的章节让无数读者潸然。 然而往事如烟,在他心里却始终燃着。他明白时代正在变,他更明白自己的文字在变革中会如何被理解,但他一直坚定相信:“写人,写心,写活着的人。”这种信念像灯塔,也像沉重的枷锁。 “一个人如果失去表达的力量,也就失去呼吸的勇气。”这句话后来被舒乙回忆时引用过,像为父亲一生的写作做注脚。 那天的太平湖边芦苇轻摆,风吹起来,有淡淡的水腥味。老舍站在岸边许久,身姿静得像雕刻。他并非冲动行事,而是像写一个必须落笔的、极难的句号。他的一生写尽众生,却唯独在这一刻不愿再写自己。 他闭过眼,直到那画面浮现——小月软软的声音:“爷爷,再见。”那声音像最后的牵绊,也像一种允许他放下的温柔。 入水的那一刻无人看见,但有人听说他当天穿得很整齐。整齐,是他对生活的尊重,也是他对自己最后的坚持。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湖边发现了他的遗体。自然界像什么都没发生,可北京城里再难听见那个带着幽默和苦涩的声音。家里人匆匆赶去认人,舒乙当场哭得瘫坐,母亲胡絜青握着丈夫的衣袖,久久不放。 小月那一天还在院子里玩,她问奶奶:“爷爷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人回答。 后来的资料里提到他生前住在“丹柿小院”,院里种着几棵柿树,是他亲自取的名字。他喜欢“四季分明的小生活”,喜欢写完一章后在院子里踱两圈,喜欢在胡同口同邻居闲聊几句。他的文字虽写尽人生荒凉,却总留一线温情,仿佛无论风雨如何,他仍想替普通人撑一把伞。 他的一生像极了他在《茶馆》里写的那句话:“人得活得像个人。”而他用整整六十七年,证实了自己确实做到了。 那天的告别,是一个时代的告别,也是一个作家用生命写下的最后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