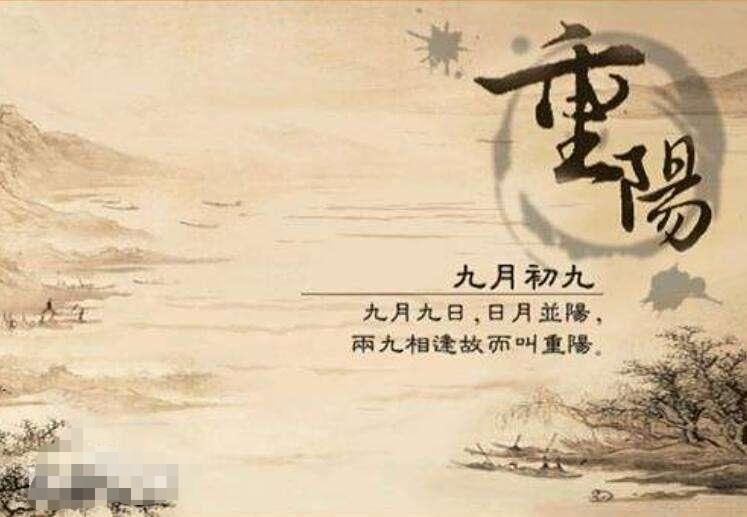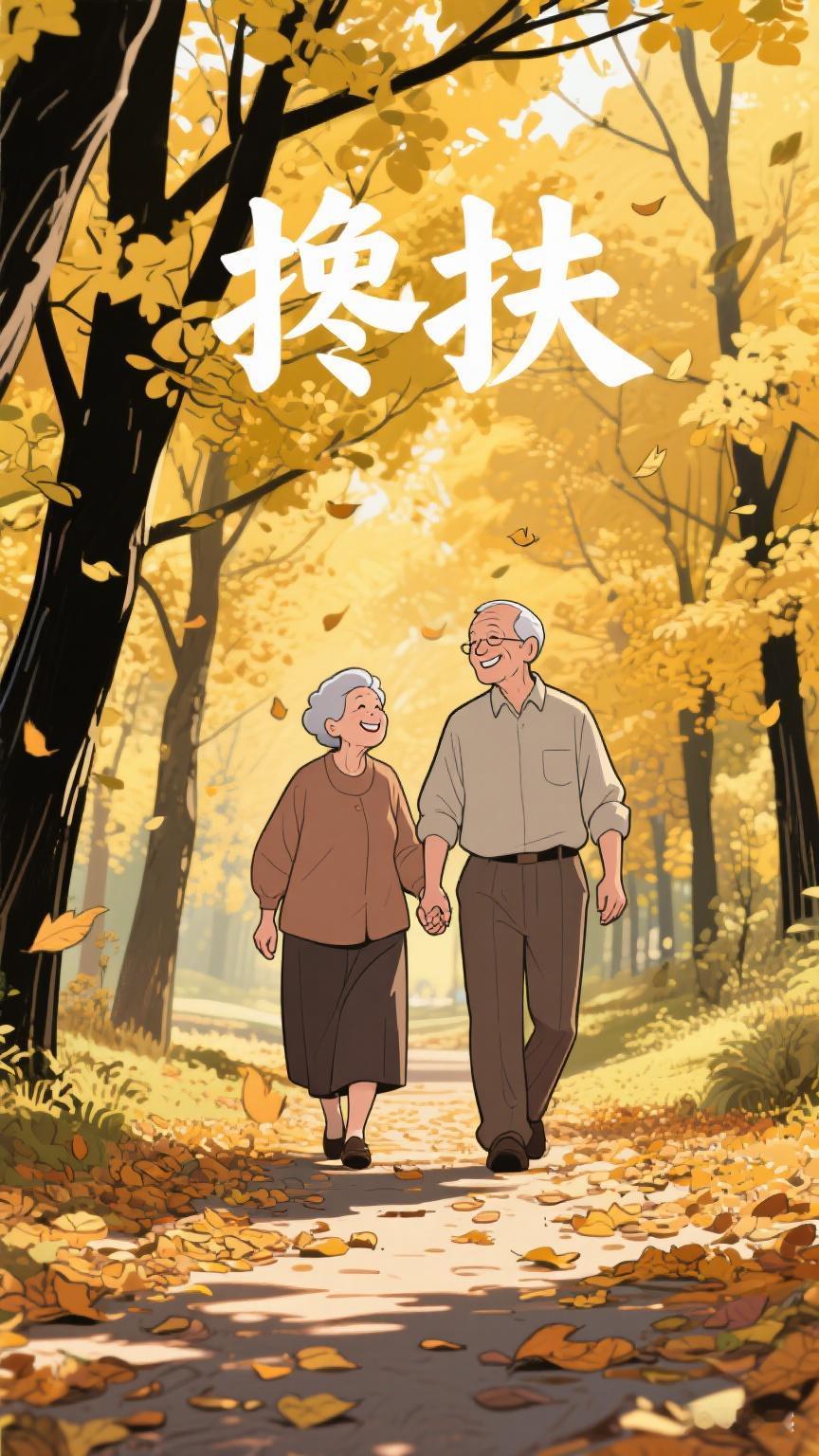又到重阳,这个古老的节日,在都市生活的节奏里,轻得像一片飘落的银杏叶,触地无声。 忽然想起小学时的重阳节。老师前一天郑重宣布:“明天带抹布,我们去敬老院。”我们欢呼——倒不是因为能敬老,纯粹是为逃半天课。第二天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走过小镇街道,老人们早已坐在院子里等着,眼神里有种期待的亮光。 我们笨拙地扫地擦窗,表演跑调的《夕阳红》。有个陈奶奶总拉着我的手说:“囡囡,好好学习啊。”她的手干瘦却温暖,絮絮地讲她当老师的故事,直到生活老师催促才放开。那时的敬老院墙上还贴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标语,空气里有消毒水和老式雪花膏混合的味道。 这些记忆突然清晰,只因意识到——这样的场景,如今几乎消失了。 现在的学校不再组织这类活动。问及原因,安全责任首当其冲——万一孩子磕碰,谁来负责?课业压力如山——半天的“耽误”要用多少习题补回?更深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变迁——从面对面的温情,转向更高效也更疏离的个体化生存。 我们曾经相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应只是书本上的句子,而应在为陌生老人捶背的动作里,在听他们讲故事时的专注目光里,真实地活过来。仪式感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形式本身,而是它为情感流动搭建的通道。当孩子们排着队为老人表演节目,当小小的手握住苍老的手,一种关于传承的密码就在无声中完成了交接。 如今通道关闭了。孩子们在作文里写“要敬老”,却很少有机会触摸老人手上的皱纹;他们背诵“遍插茱萸少一人”,却不知茱萸长什么样子。 这不仅是某个节日的式微,更是一种情感教育方式的退场。我们教会了孩子保护自己、竞争向上,却可能忘了教他们如何温柔地触摸这个世界的皱纹。 但真的无处可寻了吗? 我见过地铁上自然让座的中学生;见过社区里帮独居老人取快递的少年;也见过年轻人耐心教长辈使用智能手机。敬老的形式在变——从集体组织的仪式,化为更个体化、日常化的善意。 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不是简单地怀旧, 哀叹过去的消逝,而是为这个古老的节日找到新的锚点。在核心家庭已成主流的今天,在数字鸿沟真切存在的当下,“敬老”需要更贴近现实的表达。 它可以是家庭数字反哺——教会长辈使用一个新的手机功能;可以是一次认真的倾听——听他们讲讲我们出生前的故事;也可以是社区里的举手之劳。真正的敬老,不在声势浩大的队伍里,而在平视的目光与耐心的陪伴中。 重阳的本意是“九九”,阳极转阴,万物轮回。登高也不只为避灾,更是为了获得视角——看看我们来时的路。 那些敬老院里的老人大多已不在人世。但我想,他们给予我们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那种跨越年龄的信任,其实在童年就悄悄塑造了我们对“老去”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会因为形式的变化而失效。 我给老父亲打了视频电话。他兴致勃勃地给我看阳台上新种的花草,我们在屏幕两端笑了很久。挂断后我忽然想,或许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重阳。重要的不是以何种形式,而是那颗愿意“登高”回望的心——在个人主义的浪潮中,依然记得来处;在效率至上的时代,依然为温情留出空间。 重阳安康。愿这份祝福,能穿越屏幕,真正抵达那些苍老而孤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