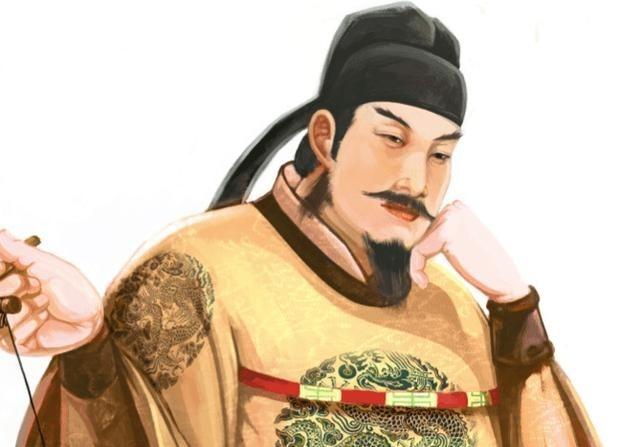清朝一考生带了36个馒头参加殿试,馒头都吃完了卷子还没交,康熙一看:头名状元就是他了! 李蟠这个人,搁在清朝康熙年间,算得上是个典型的中年寒门子弟,家里是江苏徐州丰县的书香门第,祖上从明朝末年就从丰县前四楼迁到徐州户部山那边安家。祖父李向阳是明天启年间的举人,父亲李弇则在南明弘光年间拔贡,家里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书卷气是真足,从小就熏陶着李蟠去念四书五经,奔着科举这条路走。话说回来,李蟠天生身板高大,食量也大得惊人,早年时候还爱玩鹞鹰,那玩意儿搁现在叫风筝,但古时候是真鹰,他养着放着,乐在其中。可有一次鹰从高空摔下来死了,这事儿让他转了性子,从那以后就把心思全扑在书本上,埋头苦读,不再分心那些闲事儿。家境清寒,母亲下田干活,父亲省吃俭用买纸墨,他自己借着巷口石柱的余光看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二十八岁进县学,当博士弟子,每天背书囊去堂上听课,抄笔记,父亲在家帮他改错,油灯下两人对坐,练字练到手腕发酸。这样的日子一熬就是十年,直到三十八岁那年,才在乡试中挤出去,拿到举人资格。榜单出来那天,他回家跟父亲对饮薄酒,算是小庆祝,但这点儿成绩对他来说远不够,马上又进京赶会试,成了贡生。京城租小屋,日夜啃书,窗外马蹄叫卖声不断,他揉眼睛继续写。殿试就是最后一关,母亲塞给他一袋干粮,他收拾行囊北上,尘土飞扬的官道上,马车辘辘前行。 康熙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九七年,这年殿试在紫禁城贡院办,考生们可以自带吃食,因为考一天。李蟠这家伙写文章慢,深知自己这毛病,所以一口气带了三十六个馒头,装在粗布麻袋里,圆滚滚的,麦香味儿直往外冒。进场时侍卫拦住检查,怕藏夹带,一个个掰开看,面屑掉一地,没问题才放行。考棚里光线暗,他坐下摊开卷子,题目是策论,得写对时政见解。他低头细看题目,手指摩纸沿,脑子转悠着怎么下笔。别人挥笔就写,他却边想边从袋里摸馒头撕着吃,咽下去继续琢磨。午时过了,他吃掉几个,袖子拂去屑子,提笔落墨开头。日头西斜,别人交卷走人,他还坐在那儿,抓起馒头大口咬,汁水滴下巴,擦擦嘴续写。考官巡场催了几次,他拱手求缓,笔没停。夜里烛火亮起,他吃掉第十几个,修改墨迹,刮纸重写。到半夜,棚外风吹,别人全走光,他写到准噶尔残部威胁边疆的事儿,那时候葛尔丹虽败,但准噶尔部余孽还在西北搅事儿,边防松懈,屯田戍边得加强。他接着写黄河水患,决口年年有,百姓苦哈哈,建议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别光喊口号。吏治腐败更扎心,康熙仁厚,惩贪不够严,得推行考成法,查地方官。考官又催,他加快速度,吃掉剩下的馒头,袋底空了。四更鼓响,钟声悠长,他才叠好卷子交上去。康熙亲阅卷子,看到李蟠这篇,停手细品,这些问题直戳痛处,外患水灾官场积弊,他虽是书生,提议带点理想化,但眼光准,远超别人空话套路。康熙一挥笔,头名状元给他,还授翰林院修撰。事儿传开,人家叫他“馒头状元”,这外号听着接地气,但也说明他那股子倔劲儿。 状元及第后,李蟠进翰林院,日子稳当,每天抄录典籍,批注史书,跟同僚交换卷轴,讨论经义。两年过去,康熙三十八年秋,旨意下来,他和姜宸英搭档,主考顺天府乡试。姜宸英也是前科状元,年近七旬,两人渊源深,当年殿试同榜。乡试考生多,卷子堆山,李蟠持红笔圈点,选文笔扎实、见地切的,那些上榜的多是京官子弟,他们文章严谨,论策中肯。放榜时,名单张贴,鼓声起,落榜的外地士子不服,涌到院外高举揭帖,喊着徇私卖官。谣言飞起,他们编歌谣街头传,词儿尖刻,说主考收金纳贿;檄文贴茶肆墙,墨迹斑斑,指名道姓骂舞弊。事儿闹大,传到康熙耳里,他召李蟠问话,李蟠跪陈录取凭才,不涉私情。康熙信他为人,暂压风波,冷处理。可落榜士子不罢休,国子监祭酒孔尚任以此编戏《通天榜传奇》,台上锣鼓响,演员演收红包、点头哈腰,观众看热闹,议论四起。戏文散布,士子重抄,街巷传得更凶,李蟠在家握笔手抖,无处辩白。舆论压顶,朝臣上疏,百姓情绪高,康熙没法子,下旨收监。李蟠铁链铐腕,押上囚车,颠簸入狱,蜷稻草上听雨声。康熙亲主复试,考生重考,笔墨声起,结果原样,那些官二代实学上榜。落榜者还围宫门呼,为平众怒,康熙贬李蟠流沈阳尚阳堡三年,姜宸英牢中咳嗽不止,没上路就死了。 流放路上,李蟠戴枷北上,马车雪地前行,风啸关外。到堡里,驻守砍柴煮饭,斧嵌入木,锅铲搅动,三年熬下来,人瘦一圈。期满回丰县,村口老树枝婆娑,母亲倚门,他卸袍卷袖下田,锄土教族中子弟读书。康熙南巡时想起用他,李蟠推辞,无意再仕。雍正六年四月,他七十一岁,在家病逝,从此闭门谢客,田间身影渐弯。这辈子,科举逆袭,仕途冤屈,搁谁都得叹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