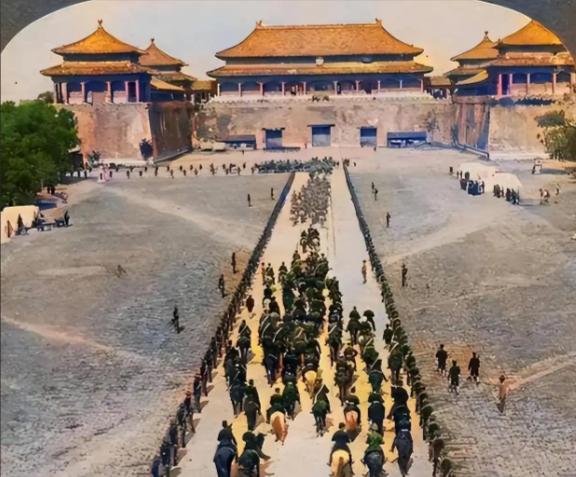1966年的下半年,八一厂彻底混乱,当时,厂里流传着一句话: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而这话形容的就是王晓棠! 王晓棠的坚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生在河南开封,祖籍南京,成长在一个并不富裕但满是墨香的家庭。 父亲是军人,爱画国画,母亲则偏爱西洋油画,两人常常切磋画技,家里到处是画具和书,这成了她艺术启蒙的底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幼的王晓棠随家人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从开封到重庆,再到云南,一路上经历了无数次空袭警报和仓皇逃命。 1943年,12岁的王晓棠在父母的建议下,拜京剧名家郎定一为师,这是她艺术生涯的正式起点,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磨砺。 每天凌晨四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熟睡时,年幼的王晓棠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压腿、吊嗓子、走台步,每一个基本功都要反复练习至完美。 她的师傅郎定一要求极其严格,一出《红鸾禧》能让她从头到尾连唱几十遍,直到每个音符、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 这段学艺经历不仅教会了她表演的基本技巧,更磨练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 就在她的戏曲之路刚刚展开之际,敬爱的师傅因病去世,戏班随之解散,这成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理想的破灭。 1949年,18岁的王晓棠原本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却得知那年学校恰好不招生,就在她感到失落之际,机会却从另一个方向来临,经著名演员黄宗英、赵丹夫妇的推荐,她进入了总政文工团。 初入文工团,她只能担任报幕员或跑龙套的小角色,但她从不抱怨,而是将每一次上台的机会都视为宝贵的实践。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神秘的旅伴》,需要一位能够饰演彝族姑娘的女演员,导演在看过王晓棠的表演后,立即决定由她出演这一角色。 为了真实呈现彝族姑娘的形象,24岁的王晓棠二话不说,独自前往云南的彝族村寨生活了整整三个月。 在那里,她学习当地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从织布到挑水,从做饭到歌舞,事无巨细地融入其中。 这种对角色的极致投入,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并不多见,当《神秘的旅伴》在1956年春节上映后,王晓棠那双灵动的眼睛和自然流畅的表演立刻征服了全国观众,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她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随后,王晓棠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时期,在那个没有特效和替身的年代,她凭借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和自然流畅的表演,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 然而,站得越高,风浪越大,1966年后,巨大的声望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审查和批斗,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林场,住进漏风的土屋,白天砍柴种地。 幸运的是,林场的人们对她还算友善,在那段最难的日子里,同为演员的丈夫言小朋始终陪在她身边,两人相互扶持。 然而,命运最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1974年的寒冬,王晓棠和丈夫唯一的儿子言群因肝炎去世,年仅16岁。 1992年,又一个噩耗传来,她的丈夫言小朋因病离世,至此,王晓棠彻底成了孤身一人。 当年龄不再允许她站在镜头前时,王晓棠选择了转型,1982年,她开始尝试导演工作,这既是对年龄现实的妥协,也是她主动求变的内在选择。 她的导演处女作《翔》,讲述了一位归国科学家的故事,深刻探讨了爱国主义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为了这部电影,她跑遍全国各地勘景,甚至不惜自掏腰包补贴剧组经费,影片在海外华人圈引发了强烈共鸣,也标志着她作为导演的成功转型。 九十年代,王晓棠出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并于199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影视界首位女将军导演。 丈夫去世后,王晓棠并未选择退休,而是继续活跃在电影界,即使年过九旬,她依然会出席各种电影活动,关注行业发展,扶持年轻人才。 在中国电影的星空中,王晓棠的光芒或许不是最耀眼的,但却是最持久的,真正的艺术不仅存在于银幕之上,更存在于如何面对生活的态度之中。

![五千年列强一笔带过,百年屈辱上下两册[6]](http://image.uczzd.cn/426565830486650900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