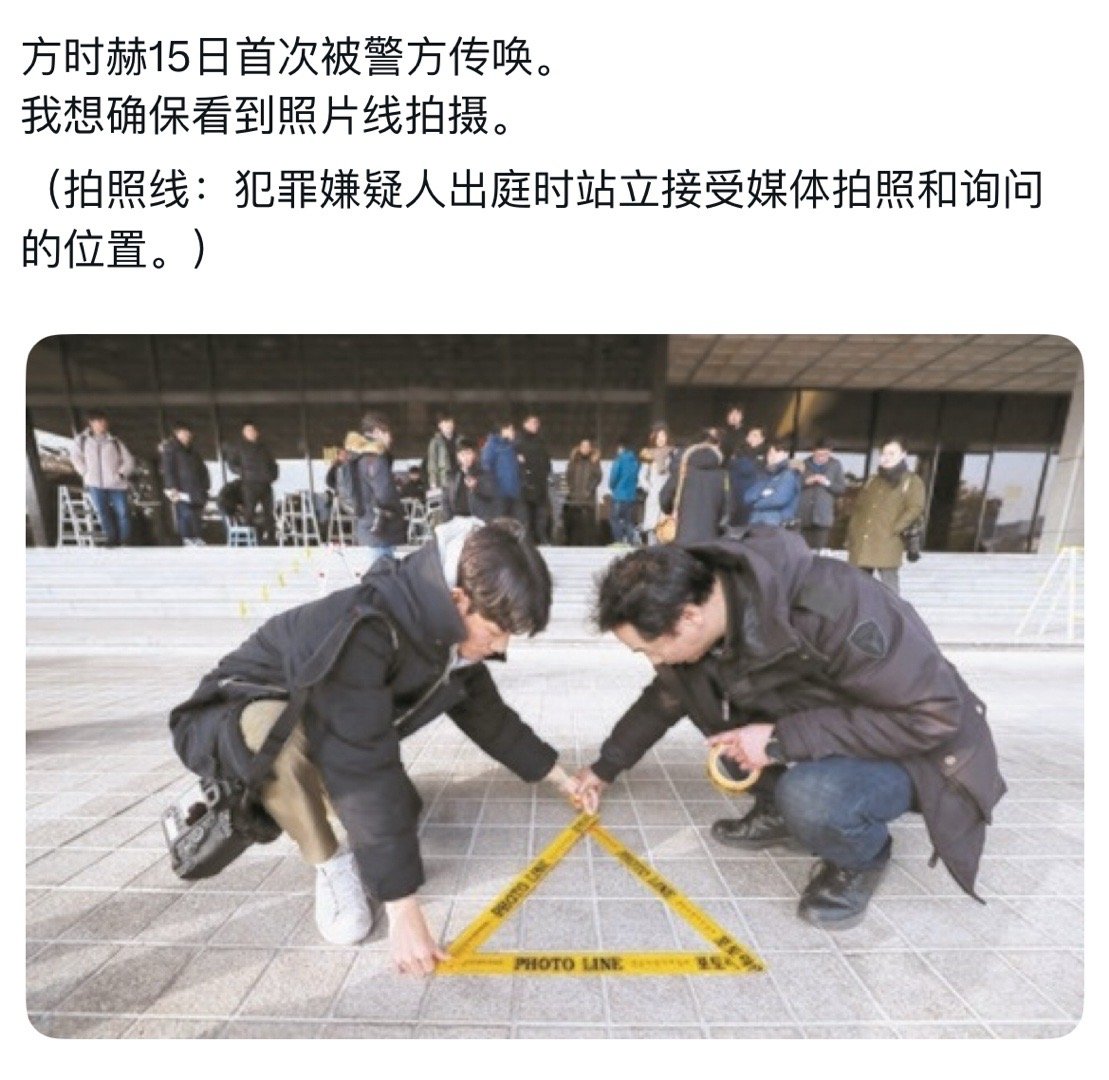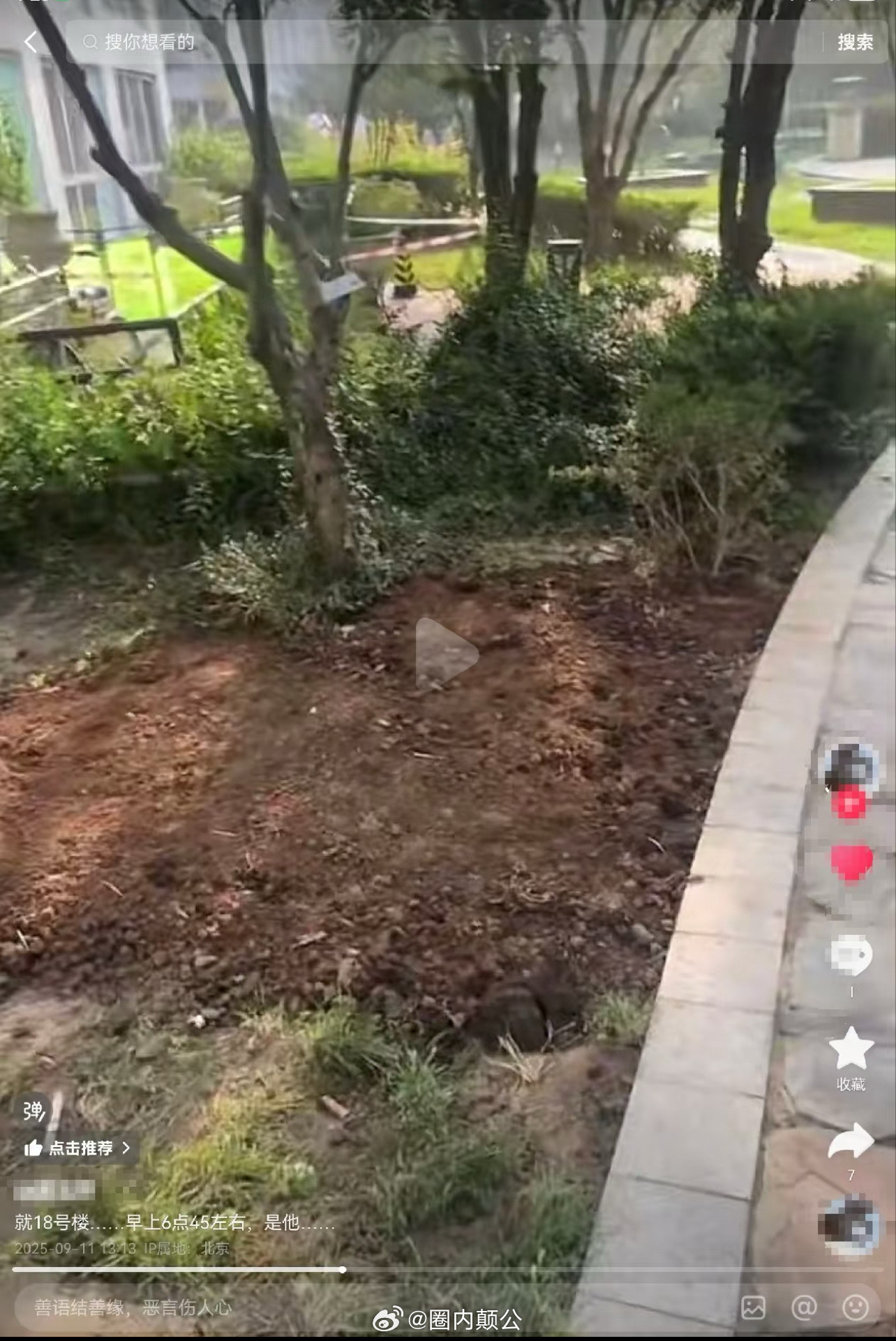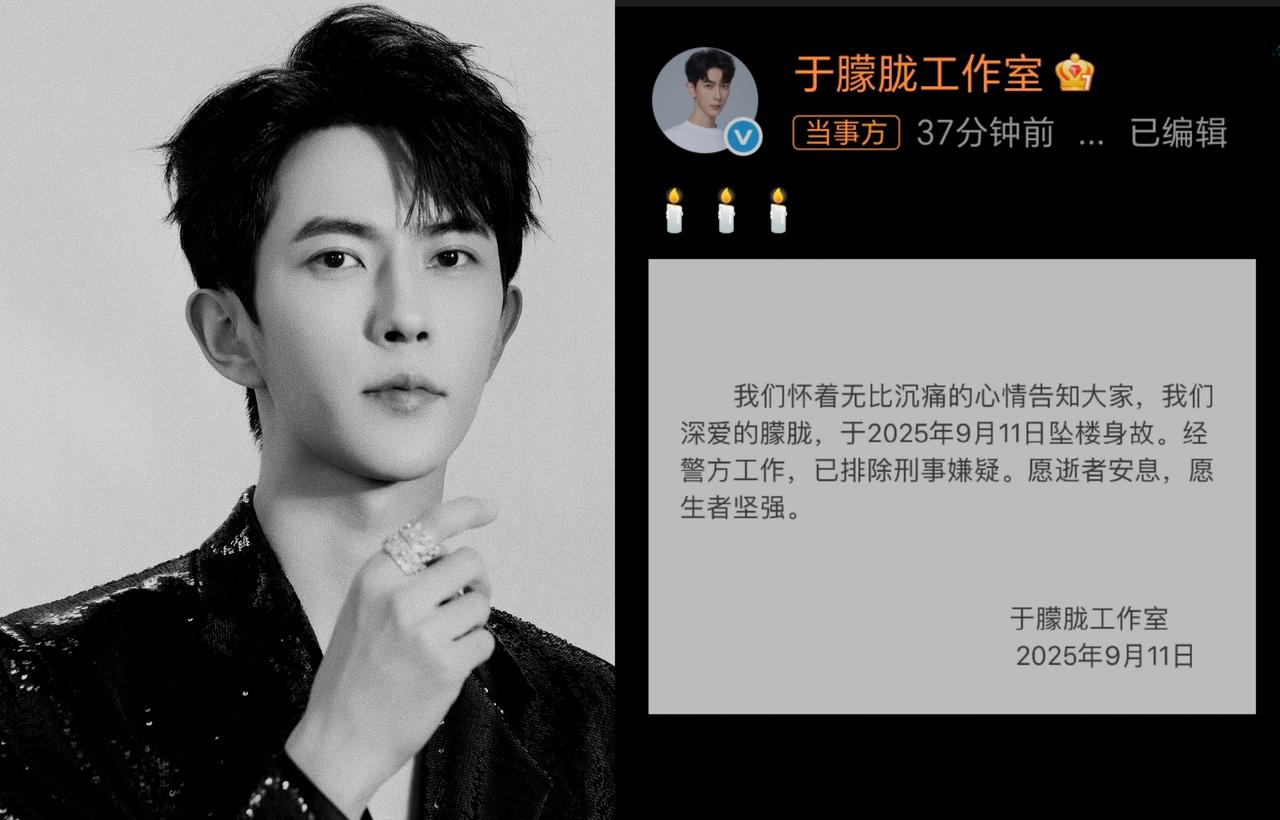一位火化工说:“当我把尸体推进焚尸炉的时候,几乎就看不到有家属特别伤心。几个男家属坐在焚尸炉前,一边抽烟一边谈笑,女家属则聚在一起说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还有几个家属背着手,到外面的园子里转悠。这一切都像等待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完成,根本就没有对焚尸炉里的死者感同身受。” “我推过那么多遗体进炉子,从没见谁真的哭晕过去。”老张掸了掸工作服上的灰,眼神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那天上午,殡仪馆大厅的门缓缓闭合,几个家属站在老张身后,等待着他按下那个启动按钮。 然而接下来几个中年男人掏出中华烟互相递着,打火机咔哒声响彻走廊。“老三去年买的股票终于解套了”“你家闺女考研结果出来没”,他们的笑声震得墙角的塑料花微微发颤。 女士们围坐在等候区的塑料椅上,交流着最近菜市场的物价,某个亲戚的婚变,还有下周广场舞比赛要穿的服装款式。 更远处,两个年轻人举着手机对比着什么,偶尔发出恍然大悟的惊叹,后来才知道是在研究附近新开的奶茶店哪家好喝。 老张的手放在控制面板上,眼睛却看着窗外:“每个厅都这样,”死亡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必须走完的流程,就像去银行办理销户手续,填完表格等待叫号的时间,人们自然要找点事打发等待。焚尸炉工作的几十分钟,成了现代人面对死亡时最真实的片段。 之前觉得大家太过冷漠,现在却品出别样的意味:正是这些烟火气的琐碎交谈,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闲聊,把人们从死亡的悬崖边拉回日常的平地上。 老张按下绿色按钮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看,真正痛彻心扉的告别早在医院病房里就完成了。能笑着聊家常的,说明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家属们用最平凡的方式完成着两个世界的交接仪式,他们不是不悲伤,而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彼此:生活还要继续。 人们总是误读悲伤的表达方式,以为眼泪是唯一的度量衡,却忽略了人类处理死亡焦虑的智慧。那些看似漠不关心的谈笑,可能是给逝者最体面的送别:你看,你走了,我们依然好好活着,就像你希望的那样。 走出殡仪馆时耳边传来家属商量去哪吃午饭的讨论声,生与死在这刻失去了清晰的边界,就像老张说的:“炉温最高能达到800度,什么都能化成灰。但活着的人总得吃饭睡觉,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或许,当代人早已习惯了把告别揉碎了拌进生活里,让悲伤散落在小事之间。这不是冷漠,而是活着的人必须学会的方式,在一次次的呼吸之间,继续向前走去。 文丨小王 编辑丨史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