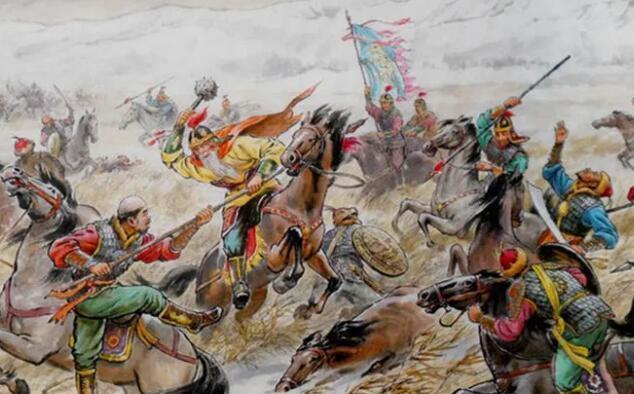1950年,67岁的清朝摄政王载沣因王府东墙被春雨泡塌,修墙缺钱,决定卖掉醇亲王府
这座曾经显赫的王府,此刻像它的主人一样,在新时代的夹缝中摇摇欲坠。
67岁的载沣望着坍塌的墙垣,手里攥着仅剩的几张当票,修墙的钱,他拿不出来了。
该王府从康熙年间赐给明珠开始,到乾隆时改建为成亲王府,再到光绪年间成为醇亲王奕譞的宅邸,已经屹立了两百多年。
它见证过纳兰性德的诗词雅集,也经历过光绪帝出生时的皇家盛况,更承载着载沣从摄政王到平民的全部记忆。
但此刻,雨水冲刷下的断壁残垣仿佛在提醒他:旧时代的辉煌早已和墙皮一起剥落殆尽。
对于此事,载沣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
1947年,他把王府一部分改成小学,想靠办学保住祖产。
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主动废除了府里的请安制度,让家人互称“同志”。
然而,伪满政权垮台后,溥仪的经济支持断了,王府里却突然多了从东北逃回的十几口家人。
仆人遣散了,字画变卖了,连饭桌上的玉米粥都越熬越稀。
国立高级工业学校的干部第三次登门时,载沣终于松口:“九十万斤小米,你们把地契拿走吧。”
在那之后,载沣把钱一分为二,一半留给八个子女平分,一半用来给自己置办新居。
奈何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四儿子溥任的理解,儿子甚至摔了当票吼道:“这是祖宗家业!”
载沣摩挲着庚子年未婚妻留下的断玉佩:“留着它,你们连玉米粥都喝不上。”
他比谁都清楚,王府早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压垮整个家族的巨石。
当时新中国的部委机关正急需办公场所,那些雕梁画栋的空屋子,与其等着被征用,不如主动换条活路。
交易完成那天,载沣独自在九思堂坐了很久,想到曾在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
1908年他在这里批阅奏折,试图挽救大清,1911年他在这里写下退位诏书。
1932年他在这里拒绝日本人拉拢,痛斥溥仪投靠伪满。
如今案几上的灰尘积了半寸厚,窗棂间漏下的阳光却比任何时候都亮。
搬家时他只带走了几箱书,连最爱的赵孟頫字帖都留给了新主人。
利溥营的新居只有两间平房,邻居是拉黄包车的工人和卖豆腐的小贩。
但载沣反而睡得踏实,再不用半夜惊醒,担心漏雨的屋顶压垮横梁。
但对于当年的决定,历史学者也曾争论载沣是懦弱还是清醒。
他28岁辞去摄政王,却在伪满时期坚拒日本利诱,他变卖祖产看似妥协,实则早看透时代更迭的必然。
九十万斤小米不仅修不起王府的墙,更补不上两百年王朝的裂缝。
但载沣却用这笔钱做了更实际的事:让子女们在新社会站稳脚跟。
小女儿韫欢拿着分到的钱,后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
溥任用分家款办起学校,真正继承了父亲“勿忘百姓疾苦”的玉佩遗训。
后来醇亲王府变成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宋庆龄故居,梧桐树下的银安殿成了小学生春游的景点。
载沣在利溥营的平房里度过最后时光,糖尿病发作时仍不肯吃药,只对着院里的瘦枣树念叨“生死有命”。
1951年冬天,68岁的他安静离世,葬礼简单得像个普通教书先生。
他曾是清朝最后的实权人物,试图挽救一个注定灭亡的王朝。
晚年却亲手卖掉了象征家族荣耀的府邸,用于建设新中国的教育事业。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醇亲王府的前世今生》 新华网历史频道《末代摄政王载沣的晚年生活》 北京市文物局官网《醇亲王府文物保护档案》